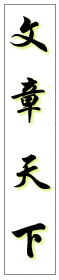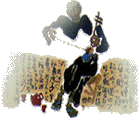|
【胡杨林社区-徒步走地球-个人文章】
于德北老师小小说专题讲座[转载]
□ 徒步走地球
2006-05-04 13:15
收藏:0
回复:9
点击:6644
(1)对话的魅力
每一个写作者都清楚地知道,心声最难以表达。心里有一朵花,到了嘴边,落到笔端,却和心里的样子大相径庭,这是最为痛苦的事情。马原在同济大学讲课的时候,赞美海明威《永别了,武器》里的对话——“你看海明威的对话真是精彩至极,海明威几乎不做任何描述,几乎用纯粹的对话,而将两个人的情绪、心思等种种细微的部分呈现无遗。”
对话当然也是小小说里人物的情绪波动、心理变化、切实感受、情感抒发的外部反映,不可等闲视之。那么,如何才能让对话精彩起来?我想无外手以下三点:一要说真话,不要单纯地为了升华主题,让主人公说假话、空话、大话;二要说“实”话,这个“实”是指不要为了完成小说,而让主人公在对话时脱离实际身份、实际环境、实际时间;三要说“情”话,这个“情”是指对话时要有动感,要有真情,不要干巴巴,像僵尸一样冷冰冰,没有弹性。
《鸟》是一篇关于死的小小说。“妈妈”是一个贩卖毒品的罪犯,她死前已经认识到这是“害众人的事”。在她之前,丈夫已经死去,显而易见,丈夫的死与此不无关联。现在,我们需要面对的残酷不仅仅是她因为内疚与悔恨,以死来寻找解脱。更残酷的是她要带走一个鲜活的、在本质上与此事毫无关系的幼小生命。这个男孩无形中成为母亲悔过的代价。
这篇小小说的语言是洗练的,不拖泥带水,通篇的对话,为阅读铺就了直达寓意的道路。这篇小小说的成功之处,就是对话,简洁而深刻,在不经意中把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尤其是孩子的语言,那么天真,那么本能,把母亲的灰暗涂抹得更加阴郁。“没得吃我们去饮茶。”“做梦吗?”“谁喂猫呢?”“妈咪什么时候让我看卡通?”……所有这些,让我们读后无法不心酸。
这篇小小说通篇以鸟为寓意,展示主人公渴望解脱、渴望心灵自由的内心焦虑与痛苦。而他们选择的死亡方式是坠楼,在大厦顶端到地面的距离,也许是他们一生中最短暂又最漫长的一次飞翔。但是这种飞翔带给我们的不是轻松与喜悦,而是深深的痛楚与惋惜。
你读完这篇小小说,感到痛楚与惋惜吗?如是,请感谢对话!
《鸟》
她对孩子说:“再吃一点儿吧!吃了这一餐就没得吃了。”
“没得吃我们去饮茶。”
“什么都没得吃了。”
“为什么呢,妈咪?”
“我们就要去死了。”
他们在楼顶上。天色正在亮起来,不高的天上有一只鸟盘旋着,像小小的鹰。她递了一张纸巾给孩子。
“妈咪,死是什么?”孩子问。
她颇费了一点思量。“死是……像睡觉一样,只是,睡觉会醒来,死不会。”
“做梦吗?”
“不做。”
楼顶上有微风,很清凉的空气。她把吃剩的东西包起来,寻思着往哪里放。
“妈咪不死可以吗?”
“不可以。爸爸已经死了。我们找爸爸去。”
“谁喂猫呢?”
没有人喂猫了,她想。人都顾不得了,还管畜牲呢?都是自己造的孽,卖白粉,害众人的事,到底不得好死。
“妈咪我们怎么死呢?”
“从这里跳下去。”
“从哪里?”
“从楼顶上跳到底下去。”她把孩子拉起来,抱他到矮墙边,指着底下说,“从这里跳下去。”
“我不跳。”她没说什么,抱着孩子在楼顶上走起来。看来会是个好天气。电车铃声从深深的地面传上来,在她心头撞了一下——是的,就要听不见那些当当的铃声了,吵人的车声也听不见了。
“妈咪什么时候让我看卡通?”
她叹了口气:“见了你爸爸再说吧!”
她从手袋里摸出一条布绳来,绑在孩子和她自己的腰间。孩子似乎不很喜欢那条绳子,用手扯着,不满地说:“妈咪绑条绳子干什么?”
“不是要去死吗?”
“死……”孩子似乎也无言了,然而还是不明白。
她把孩子背朝外面放在矮墙上,然后吃力地爬上去。孩子呆呆地望着
她。等她把他抱高了,这才望见墙外的深渊。
“我不跳。”他认真地说。 ‘
她端详着孩子,频频亲着他。孩子的小脑袋往一旁闪着,抱怨说:“你的口水……”
她抱紧了孩子,闭起了眼睛,就在她身子慢慢向外歪倒的刹那,孩子叫起来:“妈咪那边有一只……”
他们像鸟一般地飞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