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絮飞来一片红·之十二 |
45
今年的雪来的多,也下的大。
北京人怎么也想不到,这寒冷地冬天里,正孕育着一场巨大的灾难,在悄悄地降临到了所有的北京人身上。
“杀死!”“杀死!”
突然间,广播里说的,电视台放的,哪那都是可怕的“杀死”。
人民医院成了灾难的中心,医院里原先几乎全是外地人干的护理工,一下子全没了。护理工由原来的三四百元钱工资,上升到四五千元,仍然没有人来应聘。整栋整栋的楼房被武警和裹得严严实实的防疫人员隔离着,看着那些被隔离的人们在铁栏杆的窗户里挥手的情景,整个北京陷入了一片恐惧之中。
因为隐瞒预报疫情,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市长也都被撤了
一个小小的 “杀死”,把整个北京都搞乱了。
大街上稀稀拉拉没有几个行人,几十年来从没有见过。哪里还有人来坐车?张三眼睁睁地看着这从来没有过的萧条,在心里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前面有个小伙子提了一个大包过来,看样子也是要逃离北京的,张三在心里不禁骂了一声“傻屄”。
“师傅,去西客站么?”
张三用眼打量了一下那小伙子。
“去!”
那小伙子先把大包放上车,接着自己也坐了上来。
张三蹬着车朝西客站去。
车上,小伙子打着手机,不时地咳嗽一两声。
张三回头看了那小伙子一眼。这些天,电视里天天在说“杀死”的症状,张三这会儿也多了一个心眼,回头问道:“您怎么啦?”
“我有点发烧。”
“发烧?”张三在心里顿时嘀咕上了。
“莫非您得了非典么?”
“我没得,只是我哥得了,我伺候他来着。”
张三心里一惊,可没立马表现出来:“您这是要回哪?”
“回山西去。”
张三这一听,立刻将车停了下来,过来一把将那小伙子的包袱攥住,对那小伙子说道:“您得去医院,不能回山西!”那声音象是斩钉截铁。
小伙子惊恐地看着张三,“为什么?”
“您有疑似非典的症状。”一把将那小伙子手中的电话拿过来,拨打了120和110。
可是左等120不来,右等110也不来,那小伙子有些想发狠,过来要夺张三手里的行李包。
张三这回将眼一瞪,横打鼻梁竖打眼,指着那小伙子恶狠狠道:“小子!你要再和三爷我玩这个哩个啷,三爷我可对您不客气了!”说着话,将那行李包扔在地上,捋着胳膊过来将那小伙子摁倒在地。
“呜!……呜!”
随着几声警笛声,120终于来了。张三与那小伙子一块来到医院,经过滞留观察,排除了“杀死”的可能,直到晚上十多点钟,张三这才回到了家里。
看着空空旷旷的长安街,张三骑在车上就想:不如趁着眼下北京的萧条,到张北找找花儿去。
这一想,脚底竟然加着劲,急急地往家赶来。
刚到家门口,就见院里院外早已挤满了人。
自从听说苟儿胡同要搬迁了,这胡同里便没消停过,来卖房的,收购旧家具的,捡破烂想拾个大落的,这人把胡同都挤得哪那都是。
胡同口的贾二也在人群里,见着张三骑了车回来,追着张三道:“三哥,您都不玩蛐蛐了,那蛐蛐罐卖我吧!”
张三用眼瞪了贾二一眼,心说话,这贾二是想趁着“杀死”的祸乱,要来从中捞一把呢!张三从屋里掏出蛐蛐罐来,当着众人在院里,对着就要落山的太阳照了照,往地上一摔,只听的“啪!”地一声,张三用脚把地上的蛐蛐罐又踩了一脚,那蛐蛐罐在地上立马被踩得粉碎稀烂。
贾二有些丈二和尚,不知道是自己哪犯着了张三,惊愕地有些不知所措。众街坊看了,也不知道张三这火是从哪里来的,乱哄哄的院子被张三这一脚踩得立马静了下来。
半晌,只听的贾二在一旁喃喃地道:“可惜了!可惜了那值老了银子的蛐蛐罐!”
听贾二这一说,院里的众人无不啧舌。贾二知趣地不知什么时候悄悄溜了出去。
张三这才进了门,家里是收拾好了的一切。收好的,捆好的堆了一地。张三把原来准备当废纸卖的那套《十三经注疏》,重新用一个纸箱子恭恭敬敬地装了起来捆好,嘴里喃喃地道:“这书得留着让我家小三儿长大了看!”又看了看离婚状,再平平整整地和存折一块贴着自己的心口窝,放在棉衣的内口袋里。将小三用蔸布儿蔸了,背在后背,出来锁了门。
大杂院里一个人也没有,张三刚才还觉得有些空荡荡的心里头,这会儿觉得踏实多了。
父子俩出了院门,直往丽泽桥的长途汽车站去。
去张北的汽车不多,可今天这里人山人海,原来外地人都在纷纷逃离北京。
张三好不容易买到了票,在候车室里又给儿子买了两个苹果,不一会儿汽车站就在喊进站。
车站的入口处,身穿白色、头戴防化面罩的全副武装人员和防疫人员,在一旁指挥着进站的人们站在测温仪面前,广播喇叭不停地叫道:“请站立10秒钟!”原先人人向往的北京,如今所有的人,都惊恐地想要逃离出去。那个场面,就像前几年看过的电影《卡桑得拉大桥》一样恐怖。
张三心里有些后悔,不该这时去张北,可舍不得手中买的车票。张三背着孩子随着大包小包的人群,还是上了去张北的汽车。
刚与花儿结婚那会儿,花儿说想回张北,张三觉得花儿在张北没亲没故的,不去也罢。后来花儿说了,矿上的街坊们想得慌。张三便说:那天多少发了点,回去见了街坊也多少风光些,我这做老公的脸上也好看点。后来花儿怀上了孩子,又有菜摊拖着,就这样一直没去得了。这回好了,花儿没了,自己倒带着孩子来了。张三坐在又窄又小的汽车座位上,腿也伸不直,腰也展不开,比起自己的三轮车想怎么伸、怎么展那可差得太多了。好在一旁坐着的是一个出来打工回家的山里妹子,个子小,让张三父子俩多占了点地儿,凑合着坐了。张三一路想着一路看着,越往北走山越高,路越险,山上连根草毛都不生。这穷乡僻壤,心里这么一想,那路便觉得是那么难走,那么地长,那么地遥远。
孩子在张三怀里,一会儿和旁边的姑娘逗着玩,一会儿趴在车窗上看着外面的景儿,倒是一路欢快。
车终于到了张北,可去矿里没有班车。
平日里,矿山的人要出来,搭着矿里拉煤的车,出来进去倒也方便。这张三,你别看他在北京城里呼风唤雨,可在这大山里,矿山上谁也不认识。看着身边过去的几辆拉煤的空车,张三也想碰碰运气,可招了几回手,谁的车也没停下。向路边的小摊问清了路,张三决定背着孩子朝矿里走,慢慢再拦个顺便的煤车。
前面一辆空马车朝张三奔来,看样子是要回矿里去的。
张三试着向马车夫招了招手,这回马车夫倒不错,一勒缰绳,嘴里喊着:“吁……吁……”马便乖乖地停在张三面前。
看着马车夫利索的好功夫,张三心说话:“真是一把好工夫。”脸上陪着笑,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递了过去。
马车夫看了看香烟,抽了一支出来,往鼻子底下嗅了嗅,不等张三点火,便将烟夹到右耳朵的后面去了。
见了这,张三心里好笑:怎么这山里也兴这个?
张三是见过世面的人,于是赶紧又递上一支,马车夫这才将烟塞在两片嘴唇中,凑着张三点好的火,狠狠地吸了一口。
张三开口道:“大哥,能搭个便车去矿里么?”
马车夫从那眯缝的眼睛里,迅速上下扫了一遍张三,又看了看背上的孩子。
“上车吧!”
张三有些感激地:“那真谢谢您!”将包往车上一扔,背着孩子跳上了马车,并板儿与马车夫坐一块。
马车飞快地朝山里奔去。
车夫一边扬鞭,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回家呐?”
“不,找人?”
“找人?”
“找孩儿他妈。”
“孩子他妈丢啦?”
“唔。”
车夫狐疑地看了看张三。
“哪来的?”
“北京。”
“北京可是个好地方。”
张三像一下子来了劲:“可不!只要您有本事。”
马车夫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是人贩子吧?”
张三有些兴奋:“哪能啊!开车的!给老板开小车!”
马车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哦!开车可不容易!”
张三有些不屑地:“没什么,方向盘上绑个大饼子,狗也能开!”
马车夫脸上有些狐疑地:“听说北京正闹什么“非典”,您是带着孩子逃出来躲那‘点儿’的吧!”
张三满不在乎:“没您说的那么严重”。
孩子在张三背上睡着了。
马车夫眼睛不时地看一眼睡着的孩子:“这车不颠,让孩子在车上睡一会儿。”
张三:“嗯。”
说着话便将孩子从背上解下来。
马车夫从筐里掏出一件破羊皮袄上:“垫上点。”
张三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放在破羊皮袄上,孩子的小鸡鸡在马车上一颠一颠中抖的让人喜欢。
马车夫专注地看着:“是个带把的!”
张三喜滋滋地用手拨了一下小鸡鸡:“传宗接代可不就指望着他了!”
马车夫嘴里响亮地叫一声:“驾!”马车飞快地在山梁上奔跑起来。
盘山路上,左边就是山崖,右边是陡壁,张三看了有点发怵。
马车夫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突然问道:“没来过山里?”
“来过。”
“来过还害怕?”
“不……怕……有点瘆得慌。”
马车沿着盘山公路一直向上,俩人都不再吭声。
张三看着后面一层一层渐高的山路,一只手本能地护着小三,一只手不由自主地紧紧地抓住马车沿的木帮子。
孩子在车上甜甜地睡着,嘴唇不时地蠕动一下,小鸡鸡还在颠簸中一抖一抖。
突然,马车夫一回身,一脚朝张三猛地踢来。
张三一点防备没有,身子一下子被马车夫狠狠地踹下了马车,只有刚才抓着车沿帮子的手还死死地拽着。
“啪!--啪!!--啪!!!--”
马车夫连着在空中甩了几个响鞭,马车在山道上狂奔起来。
张三一只手抓住车沿帮子,整个身子悬在马车后面,两只脚被拖着在地上疯狂地胡踢乱蹬,想要站住。嘴上仍在断断续续地哀求:“大哥……大哥……”
马车夫回身过来,用马鞭凶狠地抽打张三死死把着的车沿帮的手。
张三终于被马车甩了下来,骨碌碌朝着山崖下滚去……
46
山风飕飕地顺着山梁子刮着,发出一阵阵凄厉的怪叫,细雨夹着满天的大雪,把天一下子便刮黑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张三在灌木丛中被冻得慢慢地苏醒过来,两只眼睛像有人在抽似的疼痛。张三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看了看,伸手不见五指,一股血腥味直冲鼻子。张三心里一阵悲哀:什么也看不见,我也摔成盲人了。手上能摸到的全是雪,张三顾不得想许多,甩了甩手,见手还能使上劲,知道没有伤着骨头,挪了挪身子,满身的筋骨没有一处不痛的。心里骂道:“我操你祖宗八辈!”
突然,山谷里传来一阵嗥叫,随着声音,只见远处有几点鬼火似的亮光在朝自己这边靠近。张三心里一下子明白了,眼睛没坏,这是深山沟里出来觅食的夜狼在向自己围来。心里这一明白,刚才什么劲也没有的身子,像一下子注射了强心针。张三一下子从灌木丛中爬起来,攀着树枝和荆棘,一步一步地朝山上爬来。
这一趟,张三心里可算知道了点事儿:这大山里还真不太平!包里钱不多,最担心的是儿子:“见到这老小子,我非剐了他不可。”
张三心里骂道,终于爬到了路上。见狼群朝山窝子里远去了,总算松了一口气,这才趴在马路上歇了一会儿。
远处,隐隐地又见山谷底下两只昏暗的亮光在不断地向山上蜿蜒而来。张三心里一紧:狼追来了!两只手立马在路面上的雪里摸索着,一只手抓了一块石头,就要与恶狼拼个你死我活!
亮光渐渐朝山上而来,一会儿闪一下,一会儿又不见了。亮光越来越近,一种轰鸣声夹杂着山风和扬雪吹了过来。张三终于明白了,是有一辆机动车朝山上开来。
张三拼命地站了起来,两只拿着石头的手在马路上狂舞。
车终于在张三面前不远处停了下来。
从驾驶室里下来两个人,一人手里拿着一个摇把,另一人手里拿着一把扳手,指着满脸是血双手举着石头的张三吼道:“你想怎么着?!今儿个我们可有两人,快闪开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然的话,别怪爷儿们不客气!”说着话,将手中的家伙都举了起来。
张三刚要说话,“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
那两人冲了上来抹肩拢背,又解下张三的裤腰带将张三捆了个结结实实。
张三在地上呻吟道:“救命……救命……”
那俩人这才听清楚了,问道:“救命?想劫人还是被人劫了?!”
“被人劫了!推到山凹里爬上来的,大哥救命!”
那两人对视着看了一下:“谁知是真是假,别他妈的是个苦肉计的劫托!”大点个子的对张三道:“是好是坏两条路,要么解开来重新把你推下山去!要么让我们捆着回矿上派出所,你赶紧拿主意,这深更半夜又这么大的雪,在这大山里头的。”
张三躺在地上像一条赖皮狗:“劳驾您……拉我去公安局……报案。”
张三被捆着扔到后面的车厢里,拉到矿上的派出所来了。
听说抓到打劫的,所里的干警都出来了。又听说张三是北京来的,大家捏着鼻子在那里纳了闷:北京人?昨天这刚发了通知,凡是北京来的不管三七二十一,都要隔离十五天,这个北京人倒好,大雪天跑到这大山里来劫道?待张三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说,众人赶紧给松了绑。
张三虽是花儿他爹的女婿,可是由北京来的,矿派出所除了吃好,喝好,还是将他隔离着。又请来了裹得严严实实的矿里医院的大夫,像对待个毒瘤似的,给他治着伤。好在伤得不重,等隔离完了,张三的伤也好了,只是心里惦记着孩子。
解除隔离这天,矿里让张三跟着干警们一道上了警车,警车开到了一个山凹洼里的村头停了下来。
村头拦着一杆木头,立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坚决不让非典进村!”“决不让一个北京人进门!”
几个老头堵坐在道两旁。见有人来,挥舞着手中的小旗子:“什么人?这不让过!”
警察们说明来意,村人听说张三是北京来的,死活不让进村。直到惊动了村里的大大小小干部,这才让大家伙又是量体温又是伸舌头,由着村干部在前头带路,张三和干警跟在后面,到了一间低矮的土房门前。
众人一看,那房前屋后,破旧的像个快要倒塌的猪圈,窗户用破篾席堵着。
干警们正面面相觑,屋子里却传来了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别把弟弟摔了!”
村长和治保主任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叫道:“二王叔,你出来一下!”
半天,那扇破门被打开,一个老头披着件羊皮袄出来:“啥事?”
张三一见,正是那天的马车夫,冲上前去,一把揪住马车夫,上去就是两个大嘴巴子!
马车夫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叫道:“二妞子,带着弟弟快跑哇!”
来的所有人见马车夫大喊大叫,一下子都冲进屋去。只见两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推开破篾席,抱着小三正跳窗户。其余的五、六个小姑娘,齐唰唰地拦在窗前。
破烂不堪的床上,躺着一个妇女,身边还放着一个婴儿。
干警们要冲过去揪住那两个大点的姑娘,被那四、五个小姑娘抱腿的,扯衣服的,用小拳头砸的,把干警们全围了起来。
两个抱着小三的姑娘刚从破窗户中“扑通”一声摔下去,紧跟着一声“哇--”的孩子哭声,守在窗户外面的干警冲上去,一把将两个小姑娘抓了个正着。
张三过去将儿子抱了,那两个姑娘冲上来又踢又咬:“还我弟弟,还我弟弟!”
干警将马车夫铐了。
马车夫朝张三努了努嘴:“您的包在那,我没动。”
村长和治保主任过来:“二王叔一生老实,也没犯过什么错事,望政府能宽大处理。”
派出所长在一旁埋怨道:“您也不问问,这是抢劫案!”
村长:“您这要是把二王叔抓了,这一家七八口的娘儿们,我们村里怎负担得了?”又过来埋怨二王叔道:“给政府认个错,以后别再犯傻了。”
外面那两个大点的姑娘也被干警推了进来。
村长看了,对着马车夫全家的女人跺了跺脚吼道:“还不过来给你爹求个情,请政府宽大处理!”
话音未落,床上的女人慢慢爬了起来,赤身裸体地扯过盖在身上的烂棉絮,裹住身子,往床下一跪。
那五六个小姑娘见娘跪在地上,刚才那一双双仇恨的小眼睛,转眼间变成了哀求,“扑通、扑通”齐唰唰地跪在地上:“求你们饶了我爹吧!”
女人跪在地上:“我没本事生娃,害了娃他爹,我跟你们去吧!”
小三在张三怀里,看着这齐唰唰跪在地上的人“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这一哭,地上的大大小小,一下子全都哭了起来。
张三见了,脑子里像是花儿跪在那求自己,让她去治眼睛。张三抱了小三出了屋,对派出所长道:“算了,算了,这什么狗日的,够惨的了……”
所长用眼瞪了一下张三,一把将马车夫推上了警车。
车后,是一窝大大小小女人嘶心裂肺的吼叫和啼哭……
47
张三背着孩子来到矿上花儿以前卖馄饨的地方,那地方盖了一排排的大棚。张三向那些种大棚的女人们打听花儿的事,女人们一听说是找花儿的,先说没见着,后来从矿井那边来了一队年轻的矿工,女人们便扯着嗓子喊开了:“来找花儿的……”张三背着孩子赶紧过去。
几个青年矿工过来一看,认出了张三,高兴得什么似的:“这不是张三大哥吗?”
张三也就认出了青年矿工正是那年帮花儿搬家的年轻人,后来花儿结婚了,这些年轻人还来过一次北京。
张三拉着年轻的矿工,像许久未见面的好朋友:“兄弟是您那!”青年矿工看了看张三背上的孩子:“这是你们的孩子吧。”“是”。“花儿呢?花儿怎么没一块来?”张三吱唔着:“丢了,以为回矿山来了呢!”妇女们拉着青年矿工到一旁:“他说花儿走了,花儿都丢了一年了!”
几个青年矿工开始时还在那议论,这会儿一听花儿已丢了一年了,过来问道:“花儿都丢了一年了,怎么现在才来寻?”
张三沮丧地站在一旁无语。青年们是在一旁议论了一阵,突然过来变了脸:“早就看出你小子不地道,你今儿个要是不说实话,我们哥们跟你没完。”话没说完已拉扯在一起了。
妇女们此刻也在一旁添油加醋:“怪不得前些日子有个老太婆也来找花儿,莫不是这小子嫌弃花儿是瞎子,把花儿给卖了,又到这里讨便宜来了。”
人越聚越多,听说是花儿的男人来找花儿,又听前面的人说的没头没脑的话。“卖了?!”“卖了?!”
人群里的愤怒声渐渐地越来越高,年轻的女人们已被这种议论说得跟真的似的,一双双眼睛早已冒出了火焰。那几个青年人这会儿也已按捺不住,动上手了,把张三又拉又扯,又抽了好几个嘴巴子。
孩子在张三背上,被大伙先是又掖又拽,这会儿又抽上了“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女人们见孩子哭了:“这孩子是花儿的孩子!别把孩子吓着了!”众人这才住了手。女人们又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从张三身上解下孩子。孩子“哇哇”地哭着,在女人们的手里传递着被送出了人群。
张三被人群撕扯得在地上挣扎:“那是我儿子!”
大家抱了孩子正要走,不知谁又说了一句:“这小子,早就不是个东西。”
众人被这一说,回头看了看躺在地上的张三,突然又回来一起冲上前把张三的包抢了,又将张三的衣裤扒了个干干净净,仅剩得一条裤衩遮了羞处。
张三这会儿蜷缩在地上,寒风吹过,张三想,这是到了绝路上了,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朝那山崖走去……
下面是万丈深渊,有只鹰隼在挨着山崖壁不断盘旋。
张三站在悬崖边,望着万刃陡立的绝壁,觉得自己是那样地孤独无依。
“啪!……嗒!……”天空响了一个炸雷,倾刻间大雨泼了下来。
张三像从一片茫茫的雾蒙蒙中清醒过来:那么好端端的一个家,才几年的工夫,就落得个妻离子散。这不能怪别人,是自己的心眼太狭窄了,花儿要治眼睛,自己却要去拦她,换了谁也不答应,唉……如今花儿没了,儿子没了,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张三突然又想起了娘,想起了那个抛弃了自己和娘的冯玉祥秘书台商。这一切,不都是他造的孽么?自己这一辈子,罪孽深重:不是自己娘的老娘,自己的第一个媳妇和自己的亲妹妹……这就是报应!想到这,张三将眼一闭,心想:只要这一跳,便一了百了,什么也就了结了……
张三脸上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终于,他纵身一跃……
突然,像被什么袭击,张三被人从后面拦腰抱住,狠狠地将他摔倒在泥泞的水洼地里。
张三眼也不睁,也不起来,躺在泥水里心里骂道:来张北就没碰上好事!连去死都有人捣乱!
就听见耳边抱他的人在吼道:“你他妈的要死到别的地方死去!别死在我的地盘上!”
张三用手抹了一把满脸的泥水,睁开眼一看,是矿里派出所帮自己抓马车夫的警察。
像见到了久违的亲人,张三坐在地上浑身颤抖着嚎啕大哭起来。
那警察脱了雨衣让张三穿了,对他说:“孩子在派出所里呢!”拉着他一道回到派出所。
几天水米没正经打牙的张三,见着派出所端上来的馒头和咸菜,好悬没把筷子当鸡爪子吃了一根半去。
原来,矿里先是听说来了一个北京人,这“非典”时期,矿里顿时警觉起来。后来又听说张三在矿区内先是被人抢去了儿子,接着在寻花儿时又被打了,赶紧派了一个副矿长来到家属区,将情况了解了,得知大伙又把张三的孩子抢了,这才觉得事态严重。
众人刚才一时冲动把孩子抢了,这会儿大家都冷静下来,才觉得这孩子谁养着也不合适,于是让副矿长将孩子又抱到派出所里来。派出所派了几个干警四处又去找张三,马大这才在山崖上救了张三一条命。
张三在这矿里已是第二回遭遇不测了,派出所怕夜长梦多,还会生出什么岔子来,立马派了一辆警车,将鼻青脸肿的张三连夜送回北京。
警车里,张三想着张北这一行所发生的一切,像是想明白了许多事,在车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小三看着张三,用小手摸着张三那青一块紫一块的脸:“爸……疼……”
48
又一个春天终于再次周而复始地来临了,竟管人们是在战战兢兢中迎来的又一个春天
可是经过了那场与“杀死”的较量,北京人像从病痛中苏醒过来,这个春天却让人更感觉到春天是那样地明媚。
姜大妈一早来告诉花儿:“医院说,有角膜可以移植了!”
花儿听了心里高兴,可听着姜大妈的那语气,似乎有什么不祥的事情要发生。花儿问道:“大妈您怎么啦?”
姜大妈立刻现出了高兴的样子:“我这是高兴的。”
可花儿感觉出姜大妈的高兴是装出来的,姜大妈一定有什么事瞒着自己。
姜大妈告诉自己的喜讯,花儿嘴上没说出来,心里依旧是淡淡地,没有兴奋也没有激动。花儿在琢磨:“这眼角膜,是什么样子?怎么它就能看见东西呢?”花儿想,这个消息,倒是应该告诉眼镜的。
然而,眼镜却病了。
花儿等姜大妈一走,便来到眼镜的病房,推开门,就听得眼镜叫了一声:“姐姐”便没有力气了。
花儿坐在眼镜的病床前,静静地看着眼镜。虽然花儿眼前是一片黑暗,可花儿心里知道,眼镜喜欢自己这样看着他。
花儿说:“大夫说过可能会有角膜了,我能做手术了。”
眼镜用眼睛死死地盯着花儿那双大眼睛,装着十分兴奋地:“能做手术就好了,做了手术,你就能看见东西了。”
自从姜大妈帮交了手术费的钱后,花儿就一直在等移植的角膜。花儿不知“角膜”是什么,只知道那是别人眼睛上摘下来的。
花儿问:“角膜是什么,您能告诉我吗?”
眼镜有些吃力地:“就是人的眼球。”
花儿有些吃惊:“啊!我要用别人的眼球,那谁会愿意把眼睛给我呢?”
眼镜有些惨淡地:“有人要死了,他便立下遗嘱,把自己的眼角膜捐献出来,你就能有角膜了。”
花儿脸上掠过一丝淡淡地悲戚,又像有些害怕:“死人的眼睛,不害怕么?”
眼镜笑了,笑得有些凄凉。
花儿感觉出来了:“你不舒服么?”
眼镜:“我没事。”
俩人都沉默了一会儿,花儿说:“要是你能给我做手术,我就不会害怕了,可惜你也病了。”
眼镜有些黯然:“姐姐对不起……”
花儿用手捂着眼镜的嘴,眼里的泪水就要滚出来。花儿想,要是没有眼镜在菜场给自己看眼睛,告诉自己眼睛能治;要是没有眼镜在火车站救自己;要是没有眼镜把自己安排在医院里工作;要是没有眼镜做姜大妈她们的工作;自己这治眼睛只能是幻想而已。眼镜的病是为自己累得,等他病好,自己一定要好好报答他。
花儿的手捂着眼镜嘴的这一刻,花儿心里突然起了一个念头。
对于眼镜,花儿只熟悉他的声音和他的动作,眼镜长得什么样,自己却从来不知道,花儿有些怯意地说:“你能让我在手术前摸摸你的脸吗?”
窗外,雪花正飘着,犹如一团团棉絮,“扑扑”地打在病房的玻璃上,不一会儿,又被玻璃透过去的温暖化成了一滩水,平平地流淌在窗台。
眼镜喃喃地叫了一声:“姐姐……你摸吧……”
花儿轻轻地举起双手,放在眼镜的脸上。
屋里的暖气烧得屋子里暖融融的,但是花儿的手却有些冰冷,眼镜像是打了一个冷战。
花儿将手缩了回来:“凉着你了吧?”
眼镜像是很累很累,只轻轻地叫了一声:“姐姐……”
花儿用手捂了捂自己的脸,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手怎么会那么凉。
突然,眼镜从被子里慢慢伸出双手来,把花儿的双手紧紧地抓住。眼镜的手是那么湿粘湿粘地,比自己还冷。花儿一直不知道眼镜患的是什么病。
“都开春了,你的手怎么这么凉?”
“外面还下着雪呢,该凉的。”
眼镜一边说着,一边把花儿的双手紧紧地捂在自己的脸上。
花儿纤细的十指,轻轻地颤抖着摸在眼镜的脸上,心里有些怦怦地跳。
摸男人的脸,花儿这一生只摸过三张脸,爹的脸、张三的脸和儿子的脸。爹的脸,自己是摸着长大的。以后,爹从矿里救出来,自己每天要给爹洗脸,每月要给爹剪发,直到爹死了,自己最后给爹抹上眼睛。嫁了张三,张三那宽宽的脸庞,花儿连每一个细处都曾经用心摸过。儿子的脸,那更是自己摸大的。后来在发廊,花儿给人洗头时,从来不去碰那些男人的脸。今天摸眼镜的脸,是自己摸过的第四个男人,花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欲望要摸一下眼镜,但花儿知道,是这张脸,才使她有了看到光明的希望。
花儿一点一点慢慢地摸着:“你的皮肤很光滑,很细,现在年轻人都这样么?你的颧骨很高,鼻梁也很高,只是眼窝深了些……”
眼镜自从查出自己患的病因,每天便要化疗,人也迅速瘦下来,这一切他都没让花儿知道,他怕花儿为他担心,怕花儿流泪。
花儿的泪水,对眼镜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怕花儿流泪,使眼睛越来越坏;可是他又喜欢看花儿流泪,看着花儿流泪,他心里就有一种对花儿莫名的怜悯和揪心,那种心里疼爱一个人的感觉,使自己获得了一种无限的快乐,让自己在紧张的上班后,得到了一种放松和解放,自己觉得这是自己获得幸福的一种方式。可是,自从得了癌症后,他自己也开始流泪了,从此怕看见眼泪。
看着花儿那么精心地抚摸着自己的脸庞,眼镜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姜大妈手里拿着一封信推门进来,花儿果然在眼镜这里。正要责备几句,见花儿捧着眼镜泪流满面的脸,姜大妈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嘬泣地在花儿身后叫了一声:“花儿……”
花儿摸着眼镜,平静地说:“大妈,我想做完手术后,看看他的脸是不是和现在我摸的一样。”
眼镜像是在点头:“姐姐,我……”
“我都摸出来了,你不用说,我摸出你的模样和我想像的差不多。”
花儿的脸上,充满了希望和幸福:她正在被大夫们将一层一层的纱布解下来,终于眼前是一片明媚的阳光,姜大妈、眼镜、小刘和所长,远处是张三背着孩子在慢慢地朝她走来……
眼看着就要动手术了,眼镜却病了。
想到这,花儿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眼镜放开花儿的双手,突然将手伸了过来,给花儿抹着泪道:“姐姐,手术好了帮我多看看吧。”
花儿喜极而泣:“一定的,一定要多看看,我要看看你,看姜大妈,看大家伙儿。”
眼镜眼眶里的眼泪终于刷刷地流了下来,花儿摸着的手感觉到了。
花儿有些惊诧:“你哭了!”
“姐姐,我为你就要看到东西呢。”
花儿高兴了。
姜大妈过来打岔,将那封信给了眼镜。
原来,花儿在派出所里的遭遇,眼镜听了后,在病床上给全国人大写了一封信,恰逢广东收容所里又打死了一个大学生,眼镜给人大的信,正触动了现行的收容遣送条例,但眼镜没想到,人大这么快就有回音了。人大来信说:这几日人大就要开会,讨论收容遣送条例改救助条例。眼镜在心里想,花儿虽说遭受了不少罪,可是经过了这些灾难,今后一定会好起来的。可惜,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眼镜将信看完,有些执拗地对姜大妈说:“大妈,让我和花儿单独待一会儿好吗?就一会儿。”
姜大妈看着眼镜几乎乞求的眼神,悄悄地退出了病房,将病房门轻轻地掩上了。
屋里只有花儿与眼镜,眼镜看着花儿,凝视着花儿的脸看了半天,那是一张近乎完美的脸。
“花儿……”
眼镜原来准备的话,不知怎么到了嘴边又咽回去了。眼镜躺在病床上想:自己一直想要对花儿表达的爱,花儿能接受得了么?若是接受不了,依着花儿那倔脾气,这眼睛……还怎么治?眼镜终于还是把原先想好的话收了起来,在心里暗暗地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了声:“姐姐,你能亲我一下额头吗?”
花儿愣了一下,还是在眼镜额头上亲了一下。
姜大妈终于敲门进来了:“花儿,时间不早了,我们过几天再来看他吧!”
花儿有些依依不舍:“我过几天再来……”
花儿的手术非常成功,姜大妈把花儿推出手术室时,花儿就对姜大妈说:“姜大妈我要去看眼镜。”
姜大妈一句话也没说,搀着花儿却在全身颤栗,随即呜呜咽咽地抽泣起来。
“眼镜已经死了,得的是癌症,他的眼角膜给你了,就在你的眼睛上……”姜大妈呜咽得说不下去。
花儿的心像被一种战栗紧紧地攥着,泪水被纱布盖着,眼睛里面只有泪水像是滋润着眼球,动过的手术一点感觉也没有,无棱无角,光滑一片。只有颤栗的抽搐,能让人知道花儿在哭。
姜大妈这会儿冷静下来,提了一个录音机过来,对花儿道:“这是眼镜留给你的话……”
帮着花儿打开录音机。
录音机里传出了眼睛的声音:“花儿,你听到我说话时,我已不在人世了……
花儿,我第一次见到你时,我就知道这一辈子会与你有什么牵挂……其实我在火车站见到你时,我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癌症。
看着这绚丽多彩,勃勃生机的世界,我便感受着一份锥心刺骨的痛。我已经没有了生活的勇气,可是当我看见你时,我又重新振作了起来。你看不见这个多彩的世界,可你却在黑暗中那么坦然和那么热爱。你用自己的美丽和笑声,让我们这些处在光明世界的人看到了希望。我知道,三哥爱你,三哥疼你,可当我知道三哥不让你治眼睛时,我便知道了你的心,我也决定要帮你。可是,三哥让我走了。所幸在火车站碰上了你,否则,我便会遗憾一辈子的……现在,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我终于又有了看这个世界的机会了……
录音机里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花儿,其实那天姜大妈出病房时,我就想跟你说‘我爱你!……可是我心里害怕你的拒绝,怕你离开我,也怕你听了之后,不治眼睛了……花儿,好好爱护我们俩人的眼睛,只是没想到,我的眼睛会真的给了你,花儿,你做手术后,一定要帮我多看看这个世界……”
花儿听到这,已泣不成声……
……我曾经向往着一切美好的未来,憧憬着你在治好眼睛后看我时,是不是和你抚摸的那个样,看看我是怎样地将我的一切都交给你,把我的爱,把我所能拥有的一切,都给我心爱的人。把我会的一切教给你,教你认颜色,看你满足的样子,看你在这碧蓝如洗的天空里看风筝,看小鸟……可惜,这一切都不可能了,属于我在这个世界的时间太短了;属于我在爱人身边的时间太仓促了。但是我满足了,因为我将与我一生最爱的人,一起分享我未来能享受的一切……因为我不是盲人,所以我不能像你那样想问题,可我是眼科大夫,又必然要像你那样想问题,我爱你,爱的是不管你是不是盲人,而是对生活的渴求和希望,这种憧憬,你应当永远保持下去和所有的人一样,你有权获得这一切……
……我留下一张照片,在姜大妈那儿,当你看到时,你别哭。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不是吗,现在,我还要说,花儿,你现在如果哭,打湿的可是我的眼睛……”
花儿紧紧地搂着录音机抽泣不已……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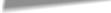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