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絮飞来一片红·之九 |
柳絮飞来一片红·之九
33
秋风“嗖嗖”地刮着,天说冷就冷下来了。
北京城的胡同里,家家户户都在贴胶条,封门窗。夏天里哪那都嫌着不透风的地儿,这会儿哪那都觉着缝太大。谁不知道,北京的冬天,冷起来那可是彻骨寒心的。
胡同里,卖蜂窝煤的、卖引火蜂窝炭的,整天在眼前晃悠,但凡看见有个扛了白铁皮烟囱的,有买了煤炉子的,那叫卖声便跟在后面没完没了。
张三自从娘死后就不点炉子了,花儿嫁过来后,这两年炉子又点起来了,花儿和娘一样喜欢炉子。每年这个时候,随着大伙儿该架炉子架炉子,该买煤时买煤。花儿摸着把那露风的,堵了个严严实实,一丝儿风也不让进。等到炉子一架起来,心里便踏实了,炉火一生,小烟囱里飘着一丝丝一缕缕的青烟,炉膛上坐了一壶水,那热气一冒,整个家里便显得暖融融,热气腾腾,屋子一暖,心里便活泛开了。冬天里的活计该干吗干吗了。要是谁家这会儿还没支炉子,准会干什么都觉得在心里没着没落。
花儿今年这时还没支炉子。
连着跟张三闹了几天,堵了几天气,昨儿个姜大妈又来劝说,花儿知道自己这治眼睛是没戏了。心里定了主意,第二天等张三一出车,花儿便背着小三来到文先生家。
文先生的宅院在胡同的中间,虽地处中段,倒也是闹中取静。
花儿背着孩子在文先生的院门前停留了一下,确信这是文先生的家门,这才抬手拍打着北京城里已不多见的门环。
“啪、啪。”
铜做的门环虽清脆好听,可花儿刚才在摸到门环那兽头时和听着这混浊的门环声时,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像是害怕,可又说不上。文先生和蔼可亲的声音,热情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一下子打消了花儿心里的那一丝怯意。
又是“啪、啪”两声,门里有个声音温和地问道:“谁呀!”好半天,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条小缝。
文先生戴着那副金边的老花镜从里面探出头来一看,见是花儿背着孩子,这才敞开一扇门:“哟!这不是花儿吗?有事吗?来来来。”将花儿让进了院子。
如今文先生的院子,在京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中已算是一景了。
四合院新近粉刷的灰墙灰瓦,房屋高朗,台砌宽平。房椽柱子用的都是大红的油漆刷得锃亮;窗户是用木头拼的各式棂格图案,用玻璃在里面隔着。北房的房檐下悬了一面“读画轩”的大匾,匾地用黑漆,字儿用的是透亮的石绿,又描红盖着两个印戳。院里搭着凉棚,地扫得一清如水。有两棵白松,怪柯撑天;左面又有几棵修竹,浓荫罩地。门廊下几十盆花卉,虽是深秋,却含蕊放葩;还有一棵石榴树,长满了火红火红的石榴;靠西头的廊檐下,还置着一个大鱼缸,有龙井,绣球,望天数十尾名贵金鱼儿,正衔尾吹沫,真是一派“天棚鱼缸石榴树”的景致,谁来都顿觉耳目为之一清。
什么是派?什么是爷?在这呢!
花儿虽看不见,可听得清、闻得倒、感觉得出:这文先生不是凡人。
一进院门,就听到有个娇声娇气的声音在叫道:“有客来了你就乐吧,你给我回来!”
说话的,是文先生新娶的小媳妇,也就是苟儿胡同东头前不久被汽车撞死的刘豁嘴的媳妇,花儿也熟悉。
话音刚落,紧跟着“呼哧、呼哧”的有个东西磨地冲着花儿蹿了出来,“嗷!嗷!”
花儿站在门口不敢进。
娇声的小媳妇女人也追了出来:“哟,是花儿,不怕的,我们家的小白不咬人。”
原来那磨地而滚嗷嗷乱叫的,是文先生小媳妇养的一只披毛京叭狮子狗。
花儿还是站在那不敢动。
小媳妇过来:“你过去吧,我蒙住它的眼睛哩,不敢咬人的。”
文先生也在厅里叫道:“花儿你客厅来吧!”
花儿循着文先生的声音来到文先生接待客人的客厅。
客厅里的文先生正在忙着,一位穿着打扮得体像是哪家的公子哥在里面,文先生拉着他的手正说道:“你来得正好,我还说要去找你呢,有一桩买卖,就要被人家抢去了,正要和你商量一个挽救的办法。”因为花儿是盲人,所以也就不忌讳。
原来文先生一直帮着一个台湾商人做买办,京城里拍卖市场上的好东西,不管是字画人物还是刻石造像家具化石,只要台湾商人看中的,便以文先生的名誉买下来,这东西不能出关,台湾商人再加一些价便出去了,人家怎么出关的,不用文先生操心。近来一桩大买卖,却有一些棘手。前几天江西一位文物贩子送来一幅八大山人的大中堂,画的是一幅双鹰松子图,先拍了大照片让台湾商人看过了,甚为满意,这回已带了原画上京城来,说好的价钱是八十八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文先生这头与台湾商人开的价是一百二十万元,两头的差价,刨去一些开支,这张画至少要赚四十万。这事不知怎么让江西贩子知道了,画是带来了,说是怎么也得卖一百万,要不然,人家这头还有一个日本人早看上这幅画了。这人还捎来话说:看你们的卖家是台湾的,好歹是中国人,也算是份爱国心哩!所以让明日一定回话,要不然这画日本人就带走了。文先生一听这话急了:“江西老俵怎么能这样?真不讲信誉,吃的喝的都是我们这支的,作了许多趟买卖了,到这关头上,还来拿捏我,这不是让咱哥儿们喝西北风吗!这样吧,你立马去把他请来,就说我今日做寿,请他来家喝杯喜酒,把他领家来。”那公子哥道:“合适吗,这许多年了,你不让领人上家来,为这一桩买卖,您破这规矩?”文先生压低了嗓门道:“把手脚作干净点,带是带来,可别让他知道在哪条胡同哪条街,到时候,让他见识见识文三爷杀狗埋头的本事。”
俩人又说了一会儿话,门外又有人在喊文先生。文先生和公子哥拱了拱手,文先生送他出门,在门口和人说了一会话就进来了。
文先生回来招呼花儿道:“花儿你坐吧!”
文先生习惯性地环顾了自己精心养护的客厅,那是刷得雪白的大墙,墙上有三五张字画,俱是法书名绘;厅前大几上一块黝黑的上水石,长着一些绿苔;东墙上还挂着一张大瑶琴,此外更无长物。厅中又摆了一个大案台,上面码放着宣纸,砚台、笔架和垫着毛毡。案台后是一张花梨木的明式圈椅。椅子后面是两个柴木做的书架,整齐地码放着许多线装书。
可惜这一切花儿都看不见,文先生好像有些失望,踱着方步款款地坐在那张垫有明黄缎子垫的椅子中。
花儿刚进门时,就感到这宽敞的空间里,有一股陈腐的怪味儿扑面而来,只是被那点燃的檀香盖了,花儿没有心思去品味。
文先生清了清嗓子:“花儿有事你说吧,我这一天到晚,前街的王小鞋家要嫁女儿,这对子还没写呢!胡同口的亿客隆又着急要让我给帮写贴子。街里街坊的,哪都不能拉下。”
花儿听了,“扑通”一声跪在文先生的面前:“花儿知道文先生是圣人,忙,可花儿的这件事,请文先生一定作主!……”
文先生听花儿说自己是圣人,这话受用,见花儿跪在那,赶紧欠起身来,“别!……别!花儿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求文先生写张离婚状……”
文先生先是一楞,眼睛一直盯着跪在地上的花儿。
文先生怎么也没想到,花儿是来求他写离婚状的。
花儿与张三结婚时院门口的对子,门里的联子都是自己写的,虽是风吹雨打发白了,可至今也还挂在那儿。老文家乐善好施,可绝不做那些损德折寿贻害子孙的事,这离婚状是不能写的……
文先生心里转而一想:你一个瞎子,能嫁张三这不挺好吗,再说啦,张三那头野驴子可不是好惹的……文先生满脸的疑惑和不解。半晌,叹了口气,拖着长声调对花儿道:“花儿,这离婚状,您找别人吧!”停了半天,叹了一声长气,对花儿道:“花儿你听我的劝,你就是不睁眼,张三还不是一样疼你?非要睁开眼干嘛么?!我们老文家是京城里积德行善承先祖遗训的文明门第,是苟儿胡同里外闻名的读书写字开后世先河之家,这种事,老文家不能做!……”
花儿跪在地上像当头挨了一棍:文先生那么知书明理,怎么也说出这种话?花儿有些绝望,跪在那里,心像被人狠狠地抽了一鞭子。楞了楞,同时一种悲哀顿时袭上心头,就像爹说的:一个在黑暗的巷道里孤独无援的人,原指望被谁搀扶一下,走出这段黑暗,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那深藏在云层之后的光明,完全被眼前这厚厚的黑暗所笼罩,自己那颗祈盼阳光的心,早已被文先生刚才的一段话,推进了这无底的泥潭。
花儿站了起来,对文先生说:“那不麻烦您。”头也不回地出了文家大院。
文先生有些不解,追着花儿出来:“没事上家来玩”。回身正要进去,却被门上自己写的那副对联所吸引,对联是那样地贴切:
积德为本续先世之风流心存继往
凌云立志振后起乃家法意在开来
横披是:
世代品行
望着渐渐远去的花儿,文先生觉得做了自己一生最值得称颂的事,刚才有如负重的感觉,一下子轻松了下来。
文先生嘴里念叨着:“如今这世界变化也太快了,您那瞎子儿媳妇也想要开眼了!老太太,我可对得住您!……”
34
花儿自文先生家出来,便将今后的事儿都想好了。姜大妈、文先生、张三,没有一个想让自己治眼睛的,自己果真要治眼睛,起码也得两万块,还不包括吃喝拉撒。孩子又小,等孩子稍微大点再说吧。
自从街坊们知道花儿要离婚,要治眼睛,张三便在街坊邻里中说:“治眼睛?我娘治了一辈子,那眼也不见好,他是嫌我老了哩!”
院子里虽说还是那样地安宁,可街坊们时不时地会有一句两句难听话钻进花儿的耳朵里来。
昨天,那种什么花也活不了的女人,理着破木箱子里往外爬的指甲花指桑骂槐道:“你也就一烂贱的指甲花儿,要你是朵名贵的百合、水仙,那还不得大发了?有个破木箱子安身就是你的造化,不错了!还一个劲地上脸往外爬!爬什么呀!真不是个知好歹的东西!”
以前连半句话也不敢招惹花儿的温州人老婆,这几天居然也时不时地要在院子里说上三,道个四:“我一字不识的睁眼瞎,伺候好了老公儿子,就什么都有了。”
将大妈更是从此除再不到张三家来,院子里连声也懒得出了。有时在院里哼哼一两声,那也只是冲着那香椿树上的老鸦骂:“该死的东西!就你会叫唤!”拿着笤帚疙瘩,狠狠地朝那乌鸦砸去。
花儿越来越感觉到,这院子里连空气都像在压迫着自己。院里以往那样融洽的街坊,像是在同一天里,都容不下自己了。
时间在整个苟儿胡同里,竟然装扮成魔鬼的模样,啮噬着花儿,也啮噬着大杂院里的每一个人。
大杂院里,花儿与张三虽然像以往一样,照样在大杂院里吃饭,睡觉、干活。可这院里再也没有往日的欢笑和快乐了。
一年过去,又熬了一年。
花儿照样出摊卖菜,张三照样出车拉活,小三也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到了两岁。
张三诨话昏话荤话和鬼话自从知道花儿想要离婚、想要治眼睛后,再也不在大杂院里胡说八道了,偶尔在外面与三轮车的哥儿们一块歇着时,虽时常还用几个精典的段子,逗逗那些还没见过大人卵的后生们和胡同里的半老娘儿们。可要来真格的,张三便不敢了。毕竟是做爹的人,毕竟有花儿在家呢。再说呢,自己已经都五十了,别让人说自己老不正经。
雪纷纷扬扬地下着,入冬以来京城里下了好几场大雪,对于多少年没这么下雪的北京人来说,真是让人痛快了好一阵子,污污嘟嘟的天空也终于让雪擦了一遍,露出碧蓝碧蓝的本来面目。可这雪对张三来说却不是好事,雪大了出不了车不算,闷在家里与花儿话不多,逗逗孩子,串串门,谁都有自己的工作。
自花儿打从文先生那儿出来,虽天天出摊收摊,可从此再也不要张三去接去送了。张三开始虽不乐意,可时间长了,倒乐得自己清闲。
窗外,大雪像鹅毛一样横斜穿插地飘着,花儿也早早地收了摊,今年买的蜂窝煤不好,屋里烧的炉子不知道怎么总是旺不起来,坐在炉子上的一壶水烧半天了也没开。
花儿在一旁喂着孩子吃饭,桌上的饭菜像是早凉了,一家人一句话也没有。
张三眼怔怔地看着窗外的飞雪,又不想出去霸踏,心里憋屈得无处可说话去,见院内香椿树上的老鸦在一阵阵“苦哇苦哇”地呱呱乱叫,仿佛它不是在号寒啼饥,却是在为有言论自由的乐趣而欢呼,有意要在这院里来骄这些街坊和在自己面前显摆。想到此,张三不禁怒发冲冠,拿了一块煤灰,正要朝那香椿树上的乌鸦砸去。
姜大妈在屋里听了乌鸦在那里鸹叫刺耳,又由屋里出来,手里抓了那把笤帚疙瘩,朝树梢狠狠地扔去:“你叫冤去吧!”
笤帚疙瘩从树上砸了下来,正好掉在张三面前。
张三看了看姜大妈,姜大妈也看了看张三,那乌鸦被刚才笤帚碰到的树枝吓了一跳,飞去了。可刚不一会儿,又飞了回来,站在树枝上伸着脖子要再叫,张三将手里刚才没扔出去的煤灰,照着那乌鸦又砸了过去。
乌鸦惊魂未定,“哇--”地一声,终于飞不见了。
太阳第二天把个银装素裹的北京城照耀得格外漂亮,满大街的人都出来扫雪。张三起了个大早,骑着三轮拉着客人欢快地走在前门大街。那金色的阳光照在张三身上,像镀了一层金箔,衬着张三古铜色的脸,张三显得有些老态了。这一路,只有张三拉着客人,张三与迎面而来的众哥儿们不断地打着招呼,脸上又显现出了一些得意。
活不好拉,钱不好挣,家里有老婆孩子,张三使出浑身解数也要多挣几个钱,晚上多少想讨花儿一些欢心。
前面有个提着生日蛋糕的女人叫道:“三轮!”张三拉着这女人,突然想起了小三过两天就是两周岁了,心里想着加快了速度,拉完活赶紧朝家来。
张三回到家,见花儿在喂孩子吃饭,张三边吃边问花儿:“再过两天就是儿子的两周岁,您看怎么过?”
花儿默默无语。
张三:“我想再请请咱们院里的街坊和哥儿们聚一聚。”
花儿仍是无语,那样子有些失神。
张三吃完饭,将碗筷收拾了洗了,又对花儿道:“您不说,那我就作主了,到时候别说我没和您商量!”抹了抹嘴,从箱子里拿了存折出去了。
张三来到胡同口的贾二家常菜,一脚跨了进来。柜台前只有一个年轻的服务员小姐在理着餐巾纸,见张三过来招呼道:“来啦您!吃点什么?”
张三往帘子遮着的后面瞅了瞅:“老板呢?”
小姐冲里面大声叫道:“老板有人找!”
贾二拍着满手的白面粉从厨房里出来,见是张三,满脸堆笑地:“三哥啊,您有何吩咐?”拉开两张椅子:“坐下说,坐下说。”
张三见贾二满手的面粉:“洗洗手好说话。”贾二知道张三有话,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完的:“哎……哎”。返身又进去洗了手出来。手中拿了一包烟,再坐在张三对面。
张三递过一支烟,贾二瞅了用手推着:“我这有,甭客气。”从兜里掏出中华烟叼了一颗就要将烟揣回去。
张三见了,心里骂了一句:“你妈屄装什么大尾巴狼。”可脸上没露出来,说道:“嗬,中华呢,您别独咪呀!”贾二装着忘了,从盒里抽出一颗出来,张三接了没抽夹在右边耳朵上,贾二有些不屑地咧了咧嘴,又抽出一颗来,给张三递上,递过自己的烟蒂让张三对了火。
张三满脸堆笑有些巴结地:“我们家小三过两周岁,想在您这大号里头来几桌,您看给个什么价?”
贾二没接张三的话茬,从怀里掏出一个葫芦罐儿来,罐身上用金丝嵌着,罐口是一块纯天然的黑色大理石镂的花,雕的一朵菊花盖,本该是乌黑乌黑的,可就是不透亮。那是一年前张三输给贾二的传家宝。贾二轻轻地拨开,一只碧绿碧绿的小脑袋伸了出来,那是蛐蛐里最上等的大青头,大青头站在罐子口,“瞿--瞿--”脆亮脆亮的叫了二声,大厅里本来就没几个人在吃东西,这一叫,左右客人不约而同地都往贾二这瞧来。那蛐蛐好像懂得主人的意思,就叫这么两声,像个将军打了得胜仗,一摇一摆地迈着方步返回罐子里去了。那贾二也像是获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慢慢地把盖子盖上又揣回了怀里。
张三心里头猛地一惊:这大青头养得可不赖,谁给教的。
张三道:“贾二!蛐蛐养的不错呀!”
贾二:“这是昨儿个花大价钱买的,不瞒您说,这蛐蛐在我这儿养几天就蔫了,三哥您的绝活,要怎么着才能教一手?”
张三听了这话,把话又拉了回来:“我那酒席怎么说?”
贾二懒懒地说道:“三哥您亲自来了,怎么也得给个八五折呀!”
张三见开了价:“八五折?不够哥儿们,兄弟不够哥儿们!”
帘子后面传来女人的叫声:“老板!”
贾二冲里面:“等会儿!”
张三:“街里街坊的,哥儿们不照顾一点?”
贾二已有些不耐烦:“三哥您知道,如今这鸡鸭鱼肉,哪一样都不便宜,实在不好弄,您这过两周岁大寿的,差了您不答应是不是?!”
张三:“那哥儿们您也被一口价呀!”
贾二:“这样吧,看在街坊的情面上,我不赚钱,赚个喜庆,给您三哥打八折,三哥您要是觉着行您就来,您要觉得不行,您再别的地方选一家?”
厨房里又在叫唤:“老板快来,王八都跑出来了!”
贾二已十分不耐烦,冲里面吼了一声:“你妈的!叫什么叫,王八出来拿刀给我剁了不就得了!”
“啪”
两手一拍,手上一只苍蝇被打得稀烂,鼓着腮帮子“呼”的一声,把烂苍蝇吹得老远,站起来,照着地上的死苍蝇用脚来回碾了碾,转身要往厨房去。
张三见贾二要走,在后面厉声地叫了一声:“贾二!!”
贾二在厨房门口站住了。
张三重新坐下,从怀里掏出存折摆在桌上,眼瞧都不瞧贾二:“还和上回那样,赌一把,若还是我输了,这折子上的钱都是你的,三哥还教您一手养蛐蛐的绝活!若我赢了,那蛐蛐罐和十桌酒钱,都你出了。敢和三爷再玩一把么?”
贾二有些犹豫:“上回玩一把,片警小刘让我去了趟派出所,就怕又有人生事儿!”
张三有些嘲讽地:“没胆量了不是?上回刘狗子也找我来着,我连尿也没尿他。你呀,不光没胆,还赢得起输不起!”
这话一说,贾二脸上有些挂不住,急了。
但凡是好赌的人,都怕人家说自己输不起,贾二把怀里的蛐蛐罐又掏了出来,放到桌子上,对着厨房吼了一声:“媳妇你来!”
贾二媳妇由厨房里出来,见是张三又在和贾二斗气,桌上放着一个红折子,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等贾二说话,早从小皮包里将存折也掏了出来,一声不吭地摆在桌上。又从包里掏出两个骰子,也摆在桌上。
张三将骰子拿了放在手心里搓了搓,放在耳边听了听,重新将它放回到桌上。
厨房里的厨子,服务的小姐,还有几个刚才吃饭的客人也都围了过来。
张三对贾二道:“上回我先,这回轮也该轮到你了!甭客气,一切照规矩办,您先来这把。”
贾二眼睛里虽然充满了血丝,但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听张三说让自己先来,也不废话,一把抓过桌上的骰子,将骰子抱在两手的拳中,“哗啦啦”行云流水一般不停地上下摇动,半天不见骰子下来。
张三在一旁冷笑道:“您玩那大花呢没用,别磨蹭,还不如早些放了呢!”
贾二不理张三那一套,照样来回地舞动着手中的骰子,脑门上早已沁出汗来了。“啪!啪!”两粒骰子终于由贾二手中的缝隙里落在了桌上。围观的人都知道这骰子一落地是什么:桌上那个精美的蛐蛐罐外带十桌酒钱。
像有鬼在那里作怪,骰子在碗里由八点转转,突然停了下来,两个骰子都在八点上定在了碗里,围观的人群都不约而同地“哟”了起来,看来张三这回又死定了。
贾二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指着桌上的骰子道:“三哥,今天您若是掷了这一样的同花,那也算是我输了!”
张三一把抓起骰子,也不摇也不晃,也不说话,从桌子上抓起骰子在空中一举随即便让骰子落了下去。只见骰子在碗里不停地翻滚。突然,骰子也像刚才那样,牢牢地定在碗里,果然和贾二的点数一样两个八点。
张三见了,突然像是从喉咙里发出了一声长啸:“哈哈!……”
贾二像有些精神恍惚,豆大的汗珠从脑门流到了脖颈。贾二指着桌上的骰子道:“你……你玩老千!”
张三用眼瞪着贾二:“怎么着!想耍赖不成?老千?!难道这骰子是我的不成!”果然抄起骰子往地上一扔,用脚死命地在地上一蹂一踩,骰子分成了两半,中间夹着一层黑心铅。张三把蹂碎的骰子捡起来拿在手上,指着贾二道:“好你个贾大老板,蒙了我的蛐蛐玩了两年,居然还敢说我玩老千!”一把薅住贾二的衣领子:“是想活还是想死!你自己选!”
贾二媳妇早过来了:“三哥!三哥!不就是十桌酒吗?您到时带着儿子客人来就是了,蛐蛐就算是我们给您白养了两年,今儿个都还给您还不行吗?”
一旁看热闹的厨子和女服务员,像是傻了,脸上一个个忿忿不平。眨眼的功夫,十桌酒就输了!不知谁说了一声:“报警去!”
贾二像突然灵醒过来,疙疙瘩瘩的脸上转身对围在一旁的大伙儿吼了一声:“敢!还不给我干活去!”指着桌上的东西道:“三哥,这都是您的,您明儿个来喝酒就是了!”
张三将钱折和蛐蛐罐都收在怀里:“就这么定了,明日中午我准时带人来吃,别误了我的大事儿!折子吃完了酒,到时还给您。”说完抹头回家去了。
35
张三要在饭馆里请大家,给儿子过两周岁的生日,在贾二家常菜定下来后,张三便挨家挨户地请客,把所有该请的都请了,最后才来到姜大妈的门前推开门站在门口:“姜大妈,小三儿过两周岁,再让花儿累着不值当,我和花儿商量了,就在胡同口的贾二家常菜摆几桌,请街坊们热闹热闹。”
姜大妈抬眼看了看张三,张三那神情不是来请客,是来哀求的,姜大妈心里不由得一阵紧抽。
这两年来,张三像是换了个人,对花儿,对孩子,对自己,张三都忍气吞声地哈着。原来脸上一天到晚挂着的那种狡黠和无赖,如今少见多了,常常是满脸的愁云和独自一人的在墙角叹息。以前,姜大妈看了张三那样,会在心里骂道:鬼张三又在琢磨什么害人的主意呢?!自从知道了张三的身世后,姜大妈一天天同情着张三:要是老太太心中没有那么深的怨恨,张三多少能读点书;要是老太太肚里没有那点私心,张三兴许爷爷都真的做了;要是老太太……咳!眼下,这花儿还要闹着离婚……姜大妈想到这些,心里便可怜着张三。没想到一天到晚依恋着老娘的张三,却是一个被娘耽误了一辈子的人!这老太太,多少也是个当娘的……这花儿,张三那样疼着她,可她还是想着要离开他,这人心哟!……姜大妈想到这些,就觉得眼前的这个张三实在是可怜。
姜大妈看了看张三,语气顿时柔和下来:“是和花儿商量的么?”
张三吱吱唔唔:“商量……过了。”
姜大妈又看了张三一眼:“那好吧!”
张三像松了一口气,回来把姜大妈也同意在胡同口请客的事说给了花儿听。
花儿仍然没有吱一声。
到了请客这一天,张三带着孩子早早来到贾二家常菜,候着前来喝喜酒的客人和哥儿们。周围的几张桌子上都摆放着“订餐”的牌子。大杂院里的老少爷们,装出一副欢欢乐乐的样,也陆陆续续地来到餐馆里找了桌子坐下,张三抱着孩子,没什么忙的,只顾给大家伙儿打哈哈作恭打揖。
姜大妈是在街坊们都到齐了最后才来的,冷冷地找了个空地坐下来。众人想找个话题活跃活跃,见姜大妈冷冷的脸孔,都不敢吱声了。人已到齐了,茶也喝够了,餐厅里腾云驾雾渐渐地热闹起来了,老板贾二过来问张三:“可以开吗?”
张三有些得意:“开!”
贾二拉长声调一声“开--喜酒!”顿时酒菜一个一个端了上来,众人趁着热气腾腾的菜肴,叉开筷子,张大嘴巴,甩开槽牙,挥着胳膊,一个一个只顾吃着每盘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菜慢慢地越聚越多,盘子压盘子,碗叠着碗,这一顿丰盛,直让大家吃了个肚歪。
“嗬!没想到这贾二家常菜,味道还真不错啊!”
“这松子鱼做得真嫩!”
街坊们天天从这贾二家常菜门前过,原以为只是个家常菜,还真没想到味道这么好。要不是张三今天请客,还真是错过了品尝的机会。人们从心底佩服起张三有眼光了,又有人觉得:人生不过如此!有儿子,有漂亮的媳妇;能吃饱穿暖足矣;想请客能请,想做寿能做;除了这些还要什么?人们对张三投来了无限的羡慕眼神。那些好听的,容易入耳的,随着菜香酒甜,飘荡在整个餐厅里面。
可花儿,死活也没见露头。
姜大妈夹在大家中间,慢慢地扶起筷子瞪着眼张三问道:“花儿怎么不来?你不是说商量过了么?!”
张三刚才已喝了几杯,满脸开始泛着紫,听着姜大妈的问话,吱吱唔唔地搪塞道:“花儿说头痛……”
姜大妈“啪”地一声将筷子放在桌上。心里顿时又涌起了一股怒气:孩子娘都不来与大家一块为儿子做寿,这酒请得还有什么意思?这个张三,实在是让人觉得可气。姜大妈的脸立时沉了下来,本想立马要起身去看看花儿,碍着这满桌子的客人,姜大妈还是坐在原地,一动没动。
张三先是见姜大妈“啪”地一声撂了筷子,冷嘴冷脸地坐在那里,心里有些害怕姜大妈在酒桌上发作,让自己下不来台,这会儿见姜大妈仍坐在那,心里便觉得没事了,举着酒杯给大伙儿敬酒:“多谢众乡亲……”
话音未落,不知怎地孩子在怀里哭了起来:“我要妈妈……”
张三端着酒杯被孩子舞动的小手一拨弄,将酒洒了一地。孩子见泼了父亲的酒,在张三怀里又哭又闹。张三这气腾地一下冒了出来,照着小三的屁股狠狠地抽了一巴掌:“你他妈的想干什么?……”
这一巴掌,清脆得让大家伙听得真真切切。本来叽叽喳喳的街坊们,一下子都静了下来,各自埋头吃着自己碗里的酒菜,餐厅里顿时只有闷声低头“叭叽叭叽”的吃噍吞咽的声音。
这顿酒,着实让街坊们吃得压抑吃得有些难受。
好好的一场喜庆酒席,吃了个不欢而散。
小三的两周岁酒席让街坊们都没喝痛快,张三心里头也闷得慌,回到家,花儿仍坐在床头,孩子早已入睡。
夜,寂静得只有张三喝酒的杯子和酒声,张三回家独自一人又喝了两小瓶二锅头,趴在桌子上醉得睡着了。
这一夜,苟儿胡同里可真是静得有些怕人,连对过洗澡堂都像没个人声。
花儿在一旁收拾东西,将结婚后张三给买的东西、衣服都整整齐齐地码在床的里边,将自己的东西打了一个包袱,照旧穿着没嫁张三之前的衣服,在儿子脸上亲了亲,抹着泪水慢慢地将门掩了,出了这座大杂院……
“花儿!……花儿!……”
张三凄厉的叫喊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街坊们穿着睡衣睡裤,纷纷来到张三家里。张三坐在屋里惨兮兮地抱着孩子哭诉道:“花儿又走了……花儿撇下我们爷俩走了……”
街坊们聚集在张三家,床上是叠得整整齐齐的缎子棉袄和崭新红灿灿的皮鞋。看了这架势,人们知道,这回花儿是真的走了。她留下了张三传宗接代的根,留下了她与张三一块度过的那些美好日子和记忆,将这两年多来张三给予的一切,这屋子里曾获得过的快乐和笑声,都留了下来。
看着这井然有序的一切,街坊们知道,自从花儿知道张三铁了心不让她治眼睛的那一刻开始,花儿便决定要离开这屋子,只是嫌儿子还小,才捱到了今天。如今,儿子两周岁了,她可以放心走了。
苟儿胡同里,从此不见了花儿的身影。
菜摊上的人在议论:说花儿在做乞丐,常在火车站那边转悠;又有人说:花儿在医院里扫厕所,要攒够了钱去治眼睛;还有人说:花儿回张北去了。
苟儿胡同从此多了两件事,一件是一致声讨那个眼科医学院的毕业生眼镜,说是他害了善良美丽的花儿,将多么幸福美好的家庭给拆散了。
“好端端的一个家,让眼镜给毁了!”
“说的是,这眼镜真可气!您治谁不好,要来治花儿。”
第二件便是赞扬胡同里的文先生,幸亏没帮着花儿写离婚状子,花儿保不准哪天回心转意便回来了呢!
文先生也常常站在张三他们家大杂院门前,像是若有所思,深沉地看着大门上还牢牢地贴着自己写的那幅对子,自言自语地念道:“这驴子,瞧我写的结婚对子还挂在门上呢!”
大杂院里的街坊们,从不去议论花儿与张三的事,只在私下里偷偷地谈论着院子里的邪乎:谁谁谁那天看见院子里的花妖出来了,有些像是张三娘;谁谁谁那天也看见了花妖在院子里转悠了两圈,见有人来,便像一股青烟似的,渐渐地消失在东屋门前种的指甲花丛里了。
大杂院里独独只有张三从此像哑了似的,连个声都没有了。
姜大妈也不再去居委会管菜市场了。
花儿的菜摊一直锁着,有多少人来盘菜摊,可姜大妈就是不松这个口。市管会新来的碍着姜大妈是老前辈,锁就锁着吧,反正都一年了。
姜大妈时常还来锁着的菜摊前照看一下,左右菜摊的菜、菜筐几乎都要把花儿原先的菜摊挤占去了,姜大妈也不管。
只要那把锁还在,那个小门脸还在就行。
这天,姜大妈又来到花儿菜摊。左右菜摊的河南婆娘和安徽女人,自从姜大妈不管市场了,这话也敢说,腰板也挺直了。每次见着姜大妈,以前怵着的那神情早没了,问这问那少不了要问问花儿的情况。
今天见了姜大妈,河南的婆娘神秘兮兮地过来道:“姜大妈,听说了么,花儿回张北矿上去了。”
姜大妈没理她,嘴角苦笑地拉了拉。
安徽女人过来接茬道:“姜大妈,花儿这菜摊可有人问老了,您到底租不租?”
姜大妈连头都没抬回答道:“不租,除了花儿回来,谁也甭想租!”
安徽的女人像是从姜大妈的语气里看到了姜大妈往日的威风,心里早不见了的怯意居然又有些回来了,怯生生地道:“都一年了,那您老也不能一直就这么空付着租金哪!”
姜大妈瞪着那双一年多来不曾瞪大的眼睛吼道:“我愿意!”
左右菜摊知道讨了没趣,看姜大妈那满身尚存的虎威,都不敢言声了。
张三自从花儿出走后,从此背着孩子每天出车拉活。拉活时孩子在自己背上,歇下来时孩子便在车里。三轮车上也多了一个装饼干袋子和背儿子的兜兜。以前锃明瓦亮的三轮,如今坐垫上总有斑痕,那是儿子小三的尿迹和吃东西留下的污渍。车子蹭坏的漆也不补了,灰尘也懒得抹,只要车能拉活,张三不再捣鼓了。张三有时独自一人发着楞,有时则逗着孩子玩,与哥儿们从此没了话,哥儿们都说:三哥这回可真见老了。
36
京城里,花儿终于又迎来了一个周而复始的春天。
当这个冬天淡淡的睡意还挂人们在眉梢,还没来得及驱散的时候,黄澄澄一簇一簇的报春花,便在还没化冻的土地上,惊艳地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人们不知道这花儿是要呼唤那远处激变的风云?还是意欲要唤醒那滚滚而来的春雷?可那花儿怎么也想不到,昨夜一宿的寒流,便将这刚刚露出的一点春光给埋住了。小小的花瓣儿,终于在寒流中掩面而泣,她不曾料到是,这场春雪,竟然是那样无情地将自己凌辱了。
花儿哪也没去,花儿还在北京。
自花儿离开大杂院的那天起,花儿就不再想让张三来养活自己,不再想让姜大妈来帮助自己,不再想让苟儿胡同里那些不让自己治眼睛的人看到自己是个盲人。
开春后,花儿便常常破衣烂衫蓬头垢面将自己满脸弄得脏兮兮地在火车站附近讨饭、讨钱;又常常学着那些买软盘的,在中关村向路人卖着盗版软盘。
买盗版软盘的多半是外地人,抱一个孩子作掩护:“要软件吗?”身上一张盘也没有。若是要,领着你七拐八拐到了一个僻静处,盘便卖了。
花儿不懂,怀里揣了几张盘,手上拿着一张,谁来问谁:“要软件吗?”
来人正是这附近派出所的便衣警察,盘没卖出一张,花儿便被逮了。
花儿被警察带到派出所,派出所里空荡荡的,花儿进门时就听的有人在扫地,见花儿被抓,问了一声:“李哥回来了,今儿个抓了漂亮的妞,也是卖光盘的么?”
警察道:“对!怎么都出去啦?”
扫地的人回道:“都出去了,就我看着大门呢!”
警察把花儿领进一间屋子,对花儿嘲笑道:“一个瞎子也卖光碟?你看的见吗?老老实实交待一共卖了多少!”
花儿听了这话,有些后悔又有些害怕,泣声道:“我刚卖!”
“刚卖?身上还藏了多少?”
“身上没有。”
“没有?”
那警察过来道:“趴在墙上,我得搜搜。”
花儿掉下泪来:“身上真的没有!”
警察道:“转过身去,还要我动电棍不是!”手里拿了个东西在那里“霹雳啪啦”地直响。
花儿想,那恐怕真的是电棍呢,一边落着泪,一边转过身去。花儿感到警察像是掐了烟,过来抓住花儿被铐的双手,让花儿脸冲墙斜趴在那里。先在自己的腰上搜摸。
花儿本能地躲着,可警察那有力的双手,早伸到了花儿前胸的衣服里,将花儿结实的奶子抓在手里。
花儿双手被铐,只有身子在不断地扭动,奋力挣扎着骂道:“流氓!”
警察开始还在花儿背后抱着花儿,这会儿花儿扭动,警察索性将花儿抱紧了,两只手加大了力气在花儿身上四处的肆虐。
花儿在狂叫:“流氓!救命!”
警察的双手拼命往花儿的腰下摸去。
院内刚才扫地的人在问:“李哥怎么啦?”
警察仍没住手:“没什么,正审案子呢!”
花儿委在墙根缩成一团,嘴里不断地在呼叫:“救命!耍流氓!”
警察放开花儿,点了一支烟回到坐位上“嘿嘿”地笑了两声。
扫地的人进来:“流氓!谁是流氓,李哥是流氓?”过来照着花儿踢了一脚:“进来的没一个不是你这样,装穷装哭装死,我们这见多了!看你那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倒卖光盘?不判你几年,你也改不了。李哥让我帮您审审?”
警察一边抽着烟,用嘴努了努桌上的烟,那意思是他抽一颗,扫地人果真从烟盒里拿了一颗烟,自己给自己点着了:“这大中华就是不一样。”
警察对花儿道:“合法搜查居然就敢喊流氓,你一个瞎子,大概还没见过流氓什么样呢!二子,你帮我搜搜她身上还有没有藏着光盘呢!女人爱把光盘放在看不到的地儿!”
那二子:“嘿嘿……好唻!”一只手把花儿死死地按在地上,一只手在花儿的奶子上身上狂摸:“哈哈……李哥!这两张软盘还真软和!”
花儿双手奋力的抵抗着。
二子一把将花儿翻过身,用膝盖顶住花儿的胸口,双手直往裤腰下面搜去。
花儿的手被铐着,胸口又被顶得喘不上气来,双脚在空中乱踢。
突然,花儿像是狠狠地踢到了二子的命处,只听二子“哎哟!”一声,双手捂着下身翻跌在地。
花儿倦缩在墙角,哭泣地哀求道:“求求你们,我第一次出来卖盘……”
二子捂了自己的下处,半天才缓过气来,举着电棍照着花儿狠狠地砸了下来:“我打死你丫子的婊子!”
花儿只觉得身上一阵剧痛和巨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花儿苏醒过来,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哪了,听得到处是女人的嘈杂声音,有个女的见花儿苏醒了,过来问话。
花儿问道:“这是哪里?”
那女的道:“这是收容所!”
听花儿的口音,是张北外地的,可再一问,感情北京市里也有人干着这违法的活。收容所见花儿是个盲人,又是初犯,可怜她也没罚她也没打她,只让家里来领人。
“找个人来保你,罚了款就放你!”又让花儿按了手印。
可花儿说:“没有家,我就在这收容所里帮扫个地,洗个衣服什么的,您就把我收容了吧!给我一口饭吃就行了。”
收容所逮来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交了罚款便脚底抹油的。唯有这盲人花儿,不肯走,还要留在收容所,这倒把收容所难住了。最后没辙,供了几餐饭,用话套着花儿,让她说出实情。
花儿想,也是!非亲非故赖在人家这也不是个事儿,可自己不愿意让苟儿胡同的人看笑话,于是哀求收容所让保着密,供诉道:“苟儿胡同的警察小刘,他能保我不?”
收容所打电话让苟儿胡同的片警小刘把花儿领了出去。
小刘来捞花儿,花儿说:“他们在派出所对我耍流氓来着。”
小刘听了这话半天没出声,见花儿在那里落泪,小刘道:“这事在外面别说了,再说恐怕连我也成流氓了呢。”
前年张三娶了花儿,小刘在家捂着被子睡了三天三宿,娘以为儿子病了,可摸着脑袋,烧没烧汗没汗。问着情况,没话!再要多说几句,儿子便跟自己急。小刘娘没辙,任由着儿子胡闹,只要一日三餐不拉下就没事儿。
有多事的老姐儿们过来悄声道:“您那宝贝儿子中邪了,是被张三媳妇那花儿妖精给迷上了!”
小刘娘这才明白过来,是花儿做了张三媳妇这事给搅得。小刘娘听到这,心里反倒高兴起来,儿子还是孩子,使两天性子便好了。果然,三天还没过呢,儿子就起来了。但看着儿子的同学娶媳妇,生孩子,还是早点帮儿子找个女人,那些妖娥子便没辙了。于是四处张罗着给儿子小刘娶媳妇,找姑娘。
不久,还真的找上了一位好姑娘,从此结婚生儿子,小刘美美满满地过着日子。
花儿出走,张三在派出所里挂了寻人启事,可一年都过去了,花儿连个人影也没有,人们渐渐地淡忘了盲人花儿。
花儿在小刘心里也渐渐地淡了下来。不曾想,今天花儿却让自己来领她。
小刘有些意外,又有些不安:张三那傻屄,要是知道这事,还不定又要干出什么事来。
小刘对花儿说:“花儿,您回家吧!三哥和孩子都等着您呢?”
花儿没有吱声。
小刘要给花儿找工作,可这满大街的工作哪样也不是花儿干的。
花儿说:“刘哥,您别为我操心了,卖软盘我干不了,我还是回张北矿上吧!”
小刘没辙,要把身上的钱都给花儿,花儿死活不肯接,末了花儿说:“别告诉张三!别告诉姜大妈!别在苟儿胡同里说花儿的事!”
花儿又消失了。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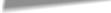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