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絮飞来一片红·之六 |
柳絮飞来一片红·之六
21
前门大栅栏,张三来回地拉着客人。
这一趟,张三车上坐着一个漂亮姑娘,到了大栅栏,姑娘下了车,转过弯往南去了。
张三在一旁用毛巾擦着汗,眼睛却一直盯着漂亮姑娘那双红灿灿的皮鞋,这可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张三在心里啧啧地称赞道。
迎面来了一个拉三轮的哥儿们,车里坐着两个大胖子,那哥儿们一边用力蹬着车,一边跟张三打着招呼:“三哥,今儿个活不赖!”
“还行!”
张三漫不经心地答道,眼睛还看着远去姑娘的那双皮鞋。
张三拉完这趟活,骑着空三轮慢慢往回地蹬,这一路,眼睛就没离过开沿街店面的玻璃橱窗。张三心里想,一定要买一双和那漂亮姑娘一样的红皮鞋,把花儿打扮打扮。踅摸着沿街的店面,可就没一家有那鞋样儿,张三心里有些懊丧。口里吹着哨,晃晃悠悠回到了老舍茶馆门前。
众多的三轮车哥儿们都在这趴活,见张三来了,打个招呼,便砍开了。
话题从南斯拉夫砍到了伊拉克,又从米卢执导的足球,说到美国飞机侵入我国领空:“美国你牛屄什么呀,要真打起来,美国鬼子还真不是咱中国人的对手!”
远处,一个哥儿们蹬着车过来:“特大新闻!有恐怖分子劫了飞机,把美国世贸大厦双子楼撞了,这回有热闹瞧了嘿!”众人的话题一下子全转到了谁是幕后主谋上来:“少不了是拉丹,说了多少回了,没动手。”“这么大的动作,估计伊拉克也脱不了干系。”
正议论着,不知谁又将话锋转了,突然问道:“三哥,咱嫂子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咋就看不见东西呢?!”
张三这会儿正想说说院里的那对小夫妇俩的事,被这话打断,没好气地说道:“看得见看不见,只要不碍吃,不碍喝,更不碍着摆摊卖菜,闭着眼睛照样给咱老张家生小三儿,就不碍事!”
另一个哥儿们过来道:“说得是!”
听着那哥儿们对自己说的话表示赞同,张三心里嘀咕道:花儿看不见那才是我的福份呢!要都看见了,你们肚子里的那些歪歪肠子,还保不准要跟我生什么事儿呢!心里这一想,肚子里反倒觉得踏实、心安了。
有客人在叫车:“三轮!”
张三与刚才过来说话的哥儿们同时应了一声:“来啦!”
张三看了看那哥儿们,要是以前,保不准张三又让了,这会儿那哥儿们也看了看张三,笑笑道:“养家糊口,如今咱三哥有家了,三哥您来!”
张三像是有些当仁不让:“那你三哥我先来一趟?!”
客人上了张三的车,张三吆喝一声:“起喽!”蹬起三轮飞快地走了起来。那车铃声顿时“叮铃铛啷”欢快地伴奏着张三嘴里的新民谣:“中国加入WTO,美国不再唱反调;三天两头敲打敲打日本小鬼子呀,台湾不久就要回家了。”民谣声引来不少路人回头观望。
这一下午,张三也没看见自己想要给花儿买的鞋样儿。
回到家来,张三心里就觉着对不住花儿,见花儿在厨房忙乎,过来道:“今儿个我来做饭吧!花儿你歇会儿!”
花儿听了,心里头高兴,把张三推出厨房,坐到床上:“您歇着吧,我一会就好!”过去拧开电视机,又给张三泡了一杯茉莉花茶。
张三爱看新闻,又爱喝茉莉花茶,张三被花儿这么宠着,乐得靠在床栏杆上,先把怀里的蛐蛐罐拿了出来。自打娶了花儿到家来,这蛐蛐罐就被冷落了,张三看了看罐里的蛐蛐,把它放在床头架上,架起腿,吞云吐雾地看着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恐怖分子劫机撞击世贸大厦的镜头,张三看着飞机撞在高高耸立的摩天大楼上,惊恐地在一旁直叫“可惜了!可惜了!”
花儿在厨房里一阵忙活,一会便把饭菜端了上来,张三给自己斟酒,又给花儿布菜。
张三看着面前忙活的花儿,心里热乎乎的,直觉得这才是有了家的感觉。
自从花儿娶进了自家的门,张三将刚想丢去的应付老娘的办法又拿了出来,什么事都依着花儿,又去买了报时钟。以前每天一个人寂寞,现在倒好,家里有了一个响,每隔一小时,便有一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花儿在张北时人给的一个偏方,用草决明、山楂两种草药泡水喝,给偏方的人说这偏方能治眼睛,矿上的姐儿们帮采了晒好,来北京看花儿时便给带些来,那草药泡的水,苦苦的酸酸的,花儿就这么一直喝着,从不喝茶叶。张三有一回偷着喝了一口,就觉得那味儿又苦有涩又酸。张三便去买了些冰糖,在花儿喝的茶里放上一点。结婚以后,张三每天由菜摊去出车,都给花儿杯子里斟满水,中间花儿自己再斟两回。
花儿一边吃这饭一边说:“三儿,我今儿个喝的水可是酸的。”
张三不解:“天天一样的水,怎么会是酸的呢?”
原来,今天暖水瓶给自己来回来去忙活时打碎了,一上午,花儿只喝了张三给沏的那杯水。见花儿一下午没喝水,河南的婆娘问道:“怎么,花儿没水啦?”
花儿答道:“暖瓶给踢了。”
安徽的女人说:“花儿,我这有水。”
花儿回道:“不啦,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安徽的女人道:“忍什么,拿杯子出来,我给沏上。”
花儿有些挤挤挨挨,最终还是将杯子拿了出来,将茶杯续满了用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便将杯子放在一旁,再也没喝,直到张三下班来接。
张三心里犯嘀咕:“外人给沏的水,怎么就会酸呢?”
张三知道娘以前的疑心重,今天花儿这一说,这除了张三觉得自己和花儿真的成了一家人外,张三也觉出来了,花儿与娘的心思一样,疑心重。
张三喝着小酒,看着电视,突然回过头来,伸出手在花儿面前隔着一二尺前晃着。
花儿把饭碗放了下来,假装嗔怒道:“你干吗呀?!”
张三以前和娘在一块生活就试过这一招,娘也是这样,一伸手娘就能感觉到。张三心里就不明白,盲眼人看不见,怎么就知道自己的手在她眼前晃呢?
花儿告诉张三:“这是感觉。有人说盲人走路数着数,哪里数得过来?这也都是感觉,到拐弯了,感觉便到了,就拐弯了!小时候,爹让我四处哪那都去,碰了壁、撞了树、下台阶摔了,心里就觉得爹特残酷,爹去世的那天拉着我的手说:‘其实,你小时候走路,爹一直跟在你的后头呢!’……”
花儿说到这,声音便哽咽起来:“若不是爹当年逼得,我哪能有今天这样啊……”
张三看着灵巧、漂亮、会体贴人的花儿,心里就想,这个世界哪怕是给她半只眼睛,这盲人也就能飞上天去了。花儿有时也撞东西,今天的暖瓶,是自己给她斟完水后没放回原处便撞了。花儿和娘以前一样,她放的东西,你给挪了,她准撞;门半开着时,也爱撞。张三从此注意着,门从不让它半开着。
几十年了,和娘天天在一起生活,虽说娘也时刻呵着自己,但是自己总觉得娘心里有什么事儿瞒着自己,娘的呵护和关怀,与花儿呵着护着给自己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看着一点也不像盲人的花儿在厨房里麻利地干活,又看着花儿那从心底里对自己疼爱的样子,张三心里直感到,花儿真是个好媳妇。
想到这,张三居然眼睛里有些湿润。
花儿虽是个盲人,可自打结婚以来,家里的里里外外,张三的一切都听花儿的。这个家,是花儿在当着!
花儿心里的感觉也和以前不一样,如今的家,是一个她和张三的家。
花儿没有想到,平时粗粗拉拉的张三,在家里对她是那样地百般呵护恩爱,花儿打心眼里觉得自己嫁了一个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花儿有时候也起急,急时会用手在案子上轻轻的敲着,那声虽轻,但却让人感到急迫。张三从此知道了,花儿的手指在桌子上轻轻地一敲,他便不吱声了。
院子里的街坊们,自打张三娶了花儿,便都觉着了张三发生的变化。每天早早地收车回了家,不是忙这便是忙那,嘴里的诨话昏话也见少了。街坊们心里寂寞,有时便打趣道:“三儿,您那装故事的篓子,怎么也跟着一块嫁给花儿了?”每当这时,张三便笑笑道:“哪天闲下来,说一段好的。”可是哪天也闲不下来。有时见花儿还没回来,便骑着车又朝着菜市场接花儿去了。
家里有了女人就是不同,更何况家里有了一个美丽娇嫩的女人。
张三和所有的男人一样,时刻都想守在这个即漂亮又会疼人的女人身边。
张三有菜没菜都爱喝两口二锅头,每天晚上这一顿必喝。娘在时,这顿酒有娘管着,有时在家喝,有时和哥儿们在一块撮,在里在外喝多喝少回来娘多少都能看着点。后来娘没了,张三有时便在胡同口的小酒馆贾二家常菜里喝。
贾二是苟儿胡同里的混混,,还好养蛐蛐,可养了几年,什么好蛐蛐到了他的手里就养死了。后来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胡同里的张三养蛐蛐是一把高手,这就借着张三来解愁,赖着张三要学本事,张三每次来,他都多给两小菜。张三嫌他吃喝嫖赌样样齐活,又琢摸着:要是把这本事传给了这小子,那这小酒也就没了,所以每回来,俩人砍的虽然都是蛐蛐的事儿,泡的却是酒的劲。几个小时眨眼就过去了,不喝痛快不回家。甭说张三叫他养蛐蛐的真本事,连张三养的蛐蛐毛都没让贾二看过。
自打结婚后,花儿知道张三的脾气,每天收了摊,晚上在家这一顿,花儿总是想着法子给张三弄点好吃的,猪头肉隔三差五的就没断过。家里那张多少年没使过的黄花梨八仙桌,姜大妈大板斧砍的洞早给张三补上了,如今也派上了用场。花儿把它抹得锃明瓦亮泛着油光,每天晚上这顿饭,便是张三和花儿这个家最幸福的时刻:桌上摆放着二锅头,一碟凉菜,一碟花生米,或者是一碟臭豆腐,还有一盘煮得黄澄澄油亮亮烂透了的猪头肉。以前这烧刀子酒是借着浇愁的,说得难听点,是浇那心头想女人欲火的。可这酒是越喝愁越深,心里头火一样的情欲半点也浇不了。如今,花儿嫁了自己,这火给花儿浇没了。每当这种时候,花儿静静地坐在一旁,一边吃着自己的饭,津津有味地听着张三“叭哒、叭哒”地咂叭叽嘴,一边听他讲着白天遇到的事,遇到的人。小屋里漾满了欢声和笑语。有时张三也会说:“花儿,你陪我喝一杯!”花儿会温顺地:“我喝不了,我不敢喝……”有时张三真想让花儿喝几口,看看花儿醉了是什么样。花儿又会说:“我喝醉了,没人侍候你……”张三便不言语了。(三十一)
张三今天软软地叫了一声:“花儿这边来。”
花儿顺从地从桌子对面坐到了张三怀里。
张三把花儿抱在腿上,手伸进花儿的胸前搓揉着,花儿痒痒地媚了张三一眼,张三觉得这一眼是那么让他消魂,一下子让他的下面那么坚挺起来,手在花儿衣服里便不自觉地加上了劲。
花儿说:“瞧您,别把酒洒了!”
张三就把手拿了出来,端杯喝了一口酒,把嘴贴在花儿脸上,蹭着花儿的脸在找花儿的嘴。花儿在张三的臂弯里,心里直漾蜜,忙将嘴唇凑了上去,张三将嘴对准了花儿,却被张三送进了一口辣辣的烈酒,呛得她咳声不止。花儿捂着嘴,叫了一声,挣脱了张三坐到自己的位置,张三却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了出来。
花儿听着张三爽朗的笑声,心里也乐,一股暖流充塞了心里,夹了一块猪头肉,直送到张三嘴里:“你那点花花肠子,连吃饭都堵不住!”
花儿告诉张三,自己觉得比谁都幸福。花儿说:“自己的一个盲人小伙伴,自去了福利厂多少年了,家里就没人来看自己。后来想家想得不行,于是独自一人摸回了村子里。到了村头,村里正敲锣打鼓,热热闹闹,是自己的亲弟弟在结婚办喜事。见盲眼的哥哥突然回来,弟弟怕女方的家人看见自己的哥哥是个瞎子,楞是把哥哥关在柴房里锁了两天,从此哥哥再也没回家去过。”
听了花儿讲的故事,张三在心里涌起了一股爱怜,把花儿抱的紧紧的,生怕要失去似的。每当这时候,花儿又会说些开心的事。有时还会说:“其实盲人挺好的,眼不见心不烦,只要心里放得下,盲人有什么不好?”说了半天,花儿说:“我如今有眼睛了,三儿你就是我的眼睛。”
张三把花儿抱得更紧了。
这顿饭,一扫张三心头没卖到皮鞋的懊恼。张三想,那双红皮鞋一定要给花儿买来。
喝完酒,吃完了晚饭,花儿把一切都收拾好了,张三也看完了新闻,花儿又与张三来到小浴室,与张三一块冲澡。
俩人进了浴池,,先还听得见里面花儿在嗔怪:“我的爷,您这是去了哪?这泥都够一盆了。”嗔怪中带着甜蜜。渐渐地,浴池里隐约流出了难以辨别的呢喃声和着戏水声,咿呀软绵的“唔……哟……”接着什么声也就没有了。
院子里静悄悄的,浴室里水蓬头的沙沙声和让人听了便起腻子的骚动响声,不断地在里面搅动着。
姜大妈由市场回来,着急着要去洗个澡,可那小浴室里早被张三两口子占了。姜大妈在外面听着浴室里的响声,直等得浑身发热,心里发紧。多年不曾有过的激动,突然像被浴室里的这声音撩拨得浑身上下都有些发紧,体内不断升腾的热气,像要把自己蒸发了。姜大妈在心里暗暗地骂了一句,干脆将衣盆放在地上,背着手在院里遛着等待,耳朵却一刻也没停下来,她甚至有些喜欢这声音了。
姜大妈像是在做着自己的白日梦,梦里是自己与死去的老头子,那声音也美妙无比,嘎吱嘎吱。丈夫把自己压在下面,自己看着丈夫的脸上泛着红云,豆大的汗珠像正浇着水蓬头似的,溅放着欢快的水花,浑身上下湿了个透。可自己却感觉到了无比地痛快和舒畅……
突然,“当啷”一声,浴池里像是被踩翻了脸盆。姜大妈从遐想中被唤了回来,浴室里的水已经是哗哗地在响。
姜大妈看看天空,天上是一层层拨也拨不开的黄云,那是沙尘暴又要来的天空。姜大妈终于耐不住了,吼了起来:“你们有完没完?这半天的!”
浴池里被姜大妈得这一嗓子,突然寂静下来。
姜大妈也开始由地上站起来,在院子里无聊地溜达着。偌大的一个四合院,自己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多好的地儿。如今城市规划,就要拆迁了,这种日子也不知道还有多久了。姜大妈把自己的思绪牵开了。
“大妈,您等着洗澡呢?”
花儿抱了衣盆由小浴池出来和姜大妈打着招呼。
姜大妈用眼瞟了一下张三,张三像是有意地在躲避着姜大妈的眼神,那眼神后面的满足和怯意,姜大妈一眼就瞅出来了。姜大妈狠狠地搂了一眼花儿,花儿的面色红润着,低着头和姜大妈说话,好像猫儿刚刚偷吃了美食,有些愧对主人似的。
花儿道:“大妈您洗去吧!里面我都冲扫干净了!”
姜大妈进了浴室,看了看四处,又用鼻子嗅了嗅,见没什么异样,这才放心地洗开了自己的澡。
这个澡洗得,姜大妈可没让自己亏着,刚才在外面听到的一切,让自己多年不曾有过的感觉像又回来了,借着水的冲劲,直把自己全身都洗软了,这才慢慢地将水关了。
擦干身子晃晃悠悠地出来,天也就见黑了。抬眼往张三家的屋子里一看,见这一对亮着灯就在屋里“叽哩噶啦”地乱响。姜大妈在院子里的骂声便起来了:“洗澡也要俩人一块儿!真没见过!这会儿灯也不关!”
花儿刚才上上下下给张三抹香皂时心里便有些冲动,待给张三前前后后地将泥儿搓完,心里便急匆匆的有些难耐了。
张三也一样,见了花儿就猴急,像只没碰过母猪的骚公猪种。
俩人刚起了一会儿腻子,花儿就听见院里有声音,轻轻在张三耳边妮道:“外面有人听墙根呢!”将张三的手给挽了回去,张三这才慢慢地罢了手。等回到屋里,这俩人再也耐不住了,三下两下,便拥着倒在床上,裹着被单,连灯也没关了……
姜大妈的骂声传进来,花儿正躺在张三的怀抱里,瞪着那双什么也看不见的大眼睛,轻轻地吁了一声,等姜大妈的骂声过去,俩人这才慢慢地穿了衣服起来,轻轻地将灯“啪!”的一声关了……
22
自从花儿嫁了张三,花儿便觉得张三是自己的依靠。
清晨,俩人感受着希望的阳光出去挣钱;晚上,俩人把落日的余辉捆在一天的收获里,回到家来享受。每天晚上俩人最大的乐趣,便是张三讲花儿听,张三那没完没了的新鲜事和白天向往的欲望,在晚上都得到了满足。
花儿十九岁的时候学过一年多的盲文,要说识字,花儿认识的字可比张三多,花儿嫁过来的时候,什么也没带,就带了几本盲文书,花儿说:“如今盲文都改了几回了,自己有些字儿已不认识了,若不经常看一看,以后就丢了!”花儿说起在盲校学习的情景,就觉得打开了话匣子:那年是爹带她来同仁医院看眼睛的最后一次,看完了眼睛,爹便带着她来到五棵松的一所盲校。她从音标认起,很快就认识了好些字。张三看着凹凸不平的盲文,用手学着花儿的样模着问花儿:“这字儿怎么认呀!”
花儿道:“盲文比明文好认,我告诉你吧,盲文字和词没有区别,它和句子紧紧地连在一起,只有读了后面,她才知道前面的字是什么!”
张三听了这么说,还是不懂。
花儿举例道:“笨死你!我这么跟你说吧,比如前面有个‘大’字,后面有个‘小’字,这字便是大小的‘大’。如果后面是个‘架’字,那这字便是打架的‘打’字,如果前面是‘到’字,这个字便是‘达’字,如果前面是个‘问’字,这个字便是‘答’字,明白了吧!”
张三早给绕进去了,什么也没明白。可在花儿面前,他还是装作懂了的样子答道:“原来是这样。”
花儿一遍一遍地抚摸着张三那肌健发达的胸脯,捋着由脖子上直到肚脐下茸茸的胸毛,那感觉,真让人觉着舒服。花儿独自幸福地享受着这世界上最棒最好的男人。可有的时候,花儿心里也会掠过一丝细细的担心:有时自己正在兴头上,张三便泄了,这时的花儿心里,便有些莫明的痛恨和怨情。那种幽怨,说不清是恨张三还是恨自己,有时恨张三不争气,恨完之后,有时便会问自己,是不是自己要得太多了?所以每次要那个,花儿都要与张三起一会腻子,相互爱慰、温存一番。先把张三的猴急压一压,让自己脸发烫身子发紧,熬得自己心里实在忍受不住了,这才任由张三在自己身上疯狂施为。今天,张三像是吃了虎鞭,一直硬梆梆地来回蹭在自己最敏感的地方。花儿在张三怀里已有些像是神志不清,臆语也随之出来了。张三知道:这是花儿最需要自己的时候。张三把花儿该伸直的地儿摆直了,该垫高的地儿,用枕头垫了起来。张三终于竭尽全力,疯狂得像那高山上狂泻的瀑布,飞流直下的银练湍流。
远望楼里传来一声歇斯底里粗犷的歌喉:“妹妹你坐船头哟!……”
张三果然像个篙工,又像那湍流险滩上的勇士,在急流涌进之中,一杆子直插下去。毫无顾忌奔腾咆哮的湍流,用自己的身体,不顾一切地撞击在那溪流中坚硬无比的岩石上。竹蒿每一次插下去,都是那样地有力,拔出来时又是那样地酣畅淋漓。稳稳地杵下去,缓缓地拔出来;杵下去,拔出来!激流中的小船,载着俩个没有丝毫牵挂的忘情人,在汗水和醉意中,突然像由万丈高空一下子抛进了谷底;酣畅淋漓,朦朦胧胧地终于到达了彼岸。
张三翻倒在床上,掏出烟来,满足地深吸了一口。倚着床头尽情地回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花儿却像一只没有张开的倦猫,静静地趴在一旁,品味着刚才无限幸福中的时光。
张三抽着烟,一个接一个地吐着烟圈,静静地看着花儿那娇媚的面庞和白玉一样剔透温润的躯体;幽暗的灯光下,花儿脸上呈现出享受了男人滋润后的无限满足,粉红的潮色还俏然在脸上残留,没有退尽;少女般的青春,依然荡漾着纯真和洁净;这一切,吸引得张三要过去吻花儿那微微气喘的红唇。朦胧种,滚烫的嘴唇烧得花儿一把将张三的脖子再次勾住:“三儿,真好!”
花儿软软地偎在张三的怀里,轻轻地蠕动着光滑丰腴的躯体,像只在母亲怀里拱奶的小鹿,右手不断地抚摸着张三的脸。张三用眼睛盯着那张美丽如花的花儿,欣赏着独自占有的美丽在自己怀里慢慢地睡着了。
张三像抱孩子似的将花儿搂着抱到她自己的位置。
花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醒了,两臂圈住了张三的脖颈,喃喃地从嘴里发出蜜一般粘糊的噫语。张三搂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这一切又逗得心旌摇动,不能自持。
张三再次俯下身子吻着花儿,越吻越狂乱,越吻越没有了张法,越吻越无法自制,那双有力的大胳膊突然又像铁钳似地,忘情地再次将花儿紧紧地箍在怀里。
花儿被张三紧紧地抱住不能动弹,直到憋得喘不上气,脸上一阵紫,一阵白,生痛得只感到一种晕乎乎的快感。花儿要再次享受刚才的一切,她让张三那坚硬宽阔的胸膛,牢牢地贴在她的胸口。
花儿看不见张三的表情,但她听到了张三那“咚咚”的心跳,她只觉得温暖紧紧地裹着自己的肌肤,全身的骨架也瘫软了,遍体发麻。花儿什么也顾不得,两只手深深地插入张三的两肋,她用力地帮着张三,迫切地要尽快让他进到自己的身体里。
张三的激情被花儿再次调动起来,看着花儿无比妩媚的神态,听着花儿鼻子里呼出了粗重的呼吸声,张三这回虽觉得下腹有些挺胀,仍然将花儿的身子飞快托到床沿,激情再次喷发,地动天摇山崩海裂,张三绷紧的肌肉和花儿激情的呼唤,终于在一阵急促的喘息声中松弛下来。
花儿蠕动着身躯,再次感受着无比幸福的爱和快感,婉转呻吟的表达方式,足以让这对出了灵魂的躯壳升到天界,使他们没有任何遗憾地忘记这个尘世的忧烦……
23
秋去冬来,花儿的肚子,衣服再也遮掩不住,渐渐地隆了起来。
花儿怀孩子与别人不一样,这也让左右菜摊的婆娘和女人心生嫉妒。
别的女人随着渐渐隆起的肚子,脸上也随之变黄,变着花样出雀斑,现麻点。花儿不,肚子虽隆,可不像人家那样隆得可怕,圆圆的像有什么东西托着,不往下坠。花儿有时摸着不大的肚子,自己也曾暗想:莫不是营养跟不上?可转而一想,自打怀上孩子,鸡、鸭、鱼、肉、张三没少买,有时连他那口猪头肉,张三都想让花儿多吃几口。安徽的女人和河南的婆娘时常在花儿的背后看花儿走路,说能看出是生小子还是生闺女,争来争去,俩人谁也没说服谁。有时候花儿肚子里的孩子翻身踢了花儿一脚,花儿“哎哟”一声,俩个女人又议论开了:“是小子!调皮着呢!”“谁说的,闺女在肚子里才踢呢,你没瞧见,小子有几个踢妈的?”每当这时,花儿只报以笑笑,随她们议论去。花儿说,只要肚子里有了孩子,自己便已经是娘了,于是将张三准备让自己做娘时才穿的一件缎子面的棉袄,悄悄地穿了起来。那缎子亮闪闪用手摸着滑溜溜的让心里舒坦,说是穿了新衣,其实也就每天在去菜场的路上,收摊回家的路上,那新衣服才露了出来。在菜摊上,花儿虽穿着新衣服,可舍不得蹭脏了,弄坏了,于是在前面围了一个大围裙,由衣领下,一直盖到新棉袄的下摆,又将两只袖筒戴了遮到大胳膊。只有菜摊闲下来,买菜的人渐渐稀少下来,花儿才会掸掸前身的土,拍拍背后的尘,把围裙和袖筒脱了,让新棉袄在左右菜摊面前露一下。那前后掸灰的动作,像是一种喜悦,也像是一种自豪,引起了左右菜摊的注意力,便都注意到花儿的身上了,身上哪有什么尘土哟!
左右菜摊见了花儿崭新的棉袄,羡慕得“啧啧”直叫唤:“哟!围着围裙没瞧出来,花儿今儿个又穿上新缎子棉袄了。”
花儿心里美,可不敢太露在脸上,只用手在光滑得直溜手的棉袄上来回摩挲了几下,仍然是那个未出阁的闺女,仍然是那样软绵绵的声调:“是我们家三儿入秋时就买下的。”一边说着,脸上白皙的皮肤里面,慢慢地就泛出了一层嫩红:“一百八十多块钱呢!”(三十二)
一阵铃铛声刚传了过来,花儿的精神又兴奋起来,对左右菜摊说:“是我们家三儿回来了!”
河南的婆娘道:“花儿真是好耳朵,三哥的车还没露头呢,就听出来了,难怪什么都给花儿买,那么贵的缎子棉袄也舍得。”
安徽的女人接口道:“这个张三,都半辈子入土了,捡了个这么大的落儿,让花儿这么疼着,真是嫉妒死人了!”
花儿听着这一左一右的议论,心里那个高兴,可嘴上却说:“瞧你们说的!……”
张三骑着车过来,满脸喜兴地与花儿一块利索地将菜摊收了。
花儿从菜摊底下拿出一个塑料袋来交给张三,又从纸盒里掏出一个生猪头来:“我让他们从乡下带来的,比城里的便宜多了。”
张三一一接了,喜滋滋地搀着花儿上了三轮车,看着花儿隆起的肚子,张三在一旁自己贫着自己:“好儿子哎,和你妈一块上车啵!”在众人羡慕的眼光相送下,小俩口欢欢喜喜哼着曲,骑着那辆满身响着铃铛的三轮“叮铃铛啷”,一路欢声一路歌,朝家奔去……
张三以前也常拉着娘出来转转,娘在车上从来是一言不吭,张三也就没什么话说。如今车上是自己的媳妇,花儿可与娘不一样,不时地会问。那天晚上张三骑着车拉着花儿出去上大街,一路上花儿问声不断:“前面是什么?左边是什么?”
张三用自己的眼光和理解给花儿解释:“快到后门桥了!这里是烟袋斜街。”
三轮的轱辘,辗着地上堆的一堆沙子,只听得“沙——啦”一声,花儿便问道:“这‘沙啦’是什么东西?”
张三道:“辗着沙子了呢!”
花儿心里美滋滋地不吱声了,满足了。
过胡同了,路面不太好走,车有些颠,花儿道:“这路好的坏的差多少?”张三答非所问:“我骑车的都不怕,你坐在车上怕什么?”
花儿佯怒道:“我下次不跟你出来了!”张三不敢言语了。
下回花儿想出来兜兜风,照样还坐着三轮出来溜达。
花儿的肚子果然不负张三重望,生了一个男孩。
“好一个带把的小子!”
“张三真是好福气!”
大杂院里自从大家伙搬进来,就没见着生儿子的,如今张三头一个生了把尿壶,满院的街坊都在祝福。
姜大妈更是乐坏了,看着小三的鸡鸡,那心里头的疼就甭提了,真是抱在怀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巴不得就要用嘴去嘬那个逗人心醉的小尿壶。
张三更是乐了,自从生了儿子,张三心里更加疼花儿。是花儿给老张家传了后,续了种,接了香火!
刚满月,花儿便背着孩子在菜市场卖菜约菜。
转眼间,孩子又快一百天了。(三十三)
这天,张三从菜市场接了母子二人回家,路上,花儿在车上抱着怀里的儿子逗着,怀里的孩子不时地发出一两声“嘎嘎”的笑声。
张三回过头来看一眼。
小三儿百日大喜,张三抱着儿子,拉着花儿,又让姜大妈先去登记处把登记员说好了,送上喜糖,张三又递上一个小红包,这才让来登记。
姜大妈坐在一旁喜滋滋地看着这一家三口。
张三把一年前都准备好的婚检表递了上来,张三在一旁道:“您看我们都有孩子了。”
姜大妈在一旁骂道:“你还不赶紧谢人家,废什么话!”张三又谢了。
那登记员将证明体检表推过一边看也不看,从抽屉里拿出两张结婚证,把张三和花儿的照片贴了,盖了印交给张三和花儿:“行啦!好好过日子吧,别生事就行!”
路上,花儿在车里拿着结婚证说:“我们家小三儿过两天就满一百天了,三儿,咱们也给儿子做做寿,庆祝庆祝吧!”
张三一听乐了:“是该请大伙来乐一乐。”
车很快就到家了,张三支着车,花儿抱了孩子来到姜大妈家,姜大妈把孩子接过来不停地逗着孩子。
花儿喜滋滋地说:“过两天就是小三的百日寿,三儿说要请街坊和大伙过来热闹热闹。”
姜大妈抱着孩子连头都没抬:“烧包啦!挣足啦,你请得过来吗?我生了八个孩子,也没有一个做百日的!”
花儿仍在旁边喜滋滋地沉默着,看着姜大妈在逗怀里的孩子,花儿又轻轻地说:“今天又领了结婚证……”
姜大妈抬眼看了看花儿,将孩子交到花儿手里,又用手逗了逗小三的小脸蛋:“那就请吧!乐得我有顿饭吃。”
花儿高兴地抱着小三回来对张三道:“姜大妈说行!”
24
张三要给儿子做大寿、过百日,与花儿把该商量的都商量好了。
第二天一大早出车,张三顺着道来到一家酒店,要打听每桌酒的价钱,可一问价,没有一家不让啧舌的。想砍个价,人家上下打量他,末了,家家都像卖刀的。张三心里明白了:这酒店只重衣冠不重人,不是不够意思,是狗眼看人低。这一整天,张三拉活都没劲,脑子里一直在琢磨,儿子的百日喜酒在哪摆体面又省钱。直到傍晚收工回来,见着胡同口的贾二家常菜,张三这才想起来,不如明日去他那试试,那离家近,又是街坊,兴许老板贾二那小子还卖点咱三爷的面子,不会贵到哪去。想到这,张三将压在心头的乌云驱散了,哼着小曲儿把花儿和儿子接回了家。
第二天,张三按着自己想好的招儿,要去贾二家常菜定酒。
张三将两个山核桃和蛐蛐葫芦罐揣在怀里,来到贾二家常菜。虽说以前常在这里蹭酒喝与贾二的交道不少,可毕竟只是酒肉朋友,更加上贾二这小子一说到钱便翻脸。要说呢,贾二钱也挣够了,可就是财迷心窍,把那钱都扳在肋条上拴着,动一动肝就疼,真的要他让点利拽下一个铜板来,能带血带筋儿!张三心里想:自己这一招要是不行,那就没辙了。张三心里有些犹豫:可又一想,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小子黑,还不至于黑到胡同里的街坊吧?更何况这街面上多少还知道点三爷的名声。想到这,张三心里多少又有了些自信,迈步进了贾二家常菜馆。
张三手里转动着两个油光锃亮的山核桃,发出“嘎嘎”的响声。一进门,见满屋子的人都在用餐,贾二和媳妇趴在柜台里,点着进出的菜单,眼睛却在四处转着大厅里的客人。
张三看准了一张没人坐的桌子,往那一坐。冲着柜台里面的贾二叫了声“贾二!”
贾二这几年在胡同口开饭馆,人人都是“老板!老板!”地叫着,这贾二的大号,都快没人敢喊了。今天突然有人直呼其名,贾二反到吃了一惊,探出头来一看,见是胡同里的张三,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答道:“来啦,是三哥您哪,给三哥上壶茶!”
张三坐在那不再理贾二,将手上的核桃往桌子上一放,四周的食客有懂行的一看,知道这架势是说明这位爷在京城里有身份、有地位。说的不好听,是这附近的一霸!来这准是要找碴的。顿时大厅里的喧哗声静了下来,有怕事的,赶紧吃了几口饭,起身出了大厅;有不懂事的,见张三那架势,好奇地往这边瞧,要看后面的好戏。
贾二在胡同口开餐馆,也有些年头了,胡同里张家长李家短也都大概齐的清楚。别看张三只是个拉三轮的,可您去四方邻里打听打听,这苟儿胡同西半城,乃至整个北京九外七皇城四,谁不知晓张三是个人物?自己开着酒店,也常和客人犯浑,可那得分什么人。俗话说:光脚不怕穿鞋的,自己多少这是个酒店,他张三有什么?看他今天来店里拔份儿的这个架势,准是店里有什么得罪了这位三爷。贾二心里有些忐忐忑忑,亲自端了泡好的茶满脸堆笑地过来。
张三从怀里掏出那个腰子形的葫芦罐子,往桌子上一摆,那贾二眼睛便直了,贾二这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好的蛐蛐罐。
张三那罐子周身用金丝嵌着人物山水,罐子面上早被张三摸得油光锃亮,金丝的图案,一阵一阵地闪着光亮直耀人眼;罐口是用一块纯天然的黑色大理石搂的花,雕的一朵菊花盖,鸟黑乌黑越发显着透亮。张三将罐子慢慢地打开,用一只眼往里面瞅了瞅,一只碧绿碧绿的大青头蛐蛐,大摇大摆地走到罐子口,张三将罐子扶倒了,蛐蛐将二只前爪子伸出罐口踩在桌子上,抬了抬头“瞿--瞿--”两声嘹亮的鸣叫,满大厅里的人顿时静了下来,连个吃东西的嚼响都没了。
贾二端了茶,恭恭敬敬站在一旁,又把自己这一辈子也没见过的硕大的大青头看了。刚要凑过来再仔细瞅瞅,那大蛐蛐已返身像个得胜利的将军,朝罐子里面进去。
贾二心里有些懊丧,才照个面就回去了。但贾二是个明白人,一看这架式,张三不是来捣乱,是有求自己来的,这一想,那胆便壮了。
贾二把茶放在张三面前,自己也在对面坐下道:“三哥您这大青头可来劲嘿,让它出来多走走,让兄弟再镂一眼。”
“再看一眼就拔不出来了!”
“别介。”
张三没理他,将盖子盖了,慢慢地又将罐子揣进怀里:“三哥今天给你瞧蛐蛐是有事求您,我们家三儿过百日,想在您这大号里来两桌怎么样?”
贾二一听是这事,把悬在嗓子眼的心,一下子给咽回了肚里。脸上也立刻有了光泽:“三哥您尽管来,兄弟一定让您满意!”
“多少钱一桌?”
“您都给兄弟看蛐蛐了,咱哥儿们还用谈价吗?”
张三有些得意:“那怎么着?哥我可不是白吃猴儿。”
贾二有些诡诘地笑了笑:“哥啊,您不就是两桌吗?把您怀里的这只大青头给我们家那只小绿配个种,您再教我一招这养蛐蛐的小绝活不就结了么?三哥您看怎么样?”
一听这话,张三顿时将细小眼睛翻了起来:“什么?!你那臭绿虫能配我这大青头!别恶心我了。”张三心里想,这小子打我养大青头绝活的主意呢。指着贾二道:“你小子没安着好心哪,原来惦记着我的大青头。”说着话已站了起来。
贾二一直赔着笑脸:“三哥您别走哇,咱哥俩慢慢再聊。”
张三横了贾二一眼:“好小子,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怕你啦。”说着话,人已出了贾二家常菜,骂了一句:“好小子够意思!”
那些要看热闹的,见这二位没打起来,也都怏怏地要散了。
张三刚想迈出大门,可又倏地返身回来,从怀里重新将蛐蛐罐掏了出来,“啪”地一声,重重地摆在贾二还愣坐的那张桌子上面。
贾二今天是头一回见着这么好的蛐蛐,又见张三没给自己多看一眼,心里正坐在那懊恼,这会儿见张三踅了回来,坐在那里用眼不解地看着张三。
张三冲着贾二道:“敢和三爷玩一把啵?!”
贾二听了,脸上立马堆满了笑容,“嘿嘿”地看着张三笑了一声,立刻像打了一针吗啡,冲着柜台里吼了一声:“给我拿骰子过来!”
柜台上的娘儿们,从一副麻将牌里拿了两个骰子送过来,交到贾二面前。
贾二用手朝张三努了努嘴:“三哥想玩两把?”
张三接过骰子拿在手里搓了两搓,骰子在张三手中咯咯吱吱直响。张三用眼瞪着贾二道:“三爷今儿个与你玩两把,赌的就是这罐和罐里的蛐蛐!”
贾二有些兴奋:“您要怎样赌?!”
张三道:“赢了!不想要你小子的多,只要我儿子的十桌酒席。输了,这便是您的!”
贾二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哪能被张三这两下气势给镇住,慢慢地他从嘴里吐出几个字来:“那就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三哥您不怕亏了?”
张三道:“什么话!你三爷是掉地上噶吧脆响的那种。不过空口无凭,你得先拿了十桌酒的现钱搁这,省得麻烦。”
贾二一听,对着柜台立马叫道:“把今天的钱都给我拿来!”
柜台里贾二的媳妇嘟嘟囔囔地把钱抽屉端了过来,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你今天又在哪喝高了不是?”
张三见了抽屉里的钱用嘴撇了撇:“贾二你小子敢耍我?!就这点钱想哄我的金丝罐和蛐蛐,胡同里打听打听去,三爷我敢把你活剥了生吃,你信不信!”
贾二冲着媳妇瞪眼道:“把存折给我!”
贾二媳妇从手包里掏出一个存折,摔在桌子上。贾二看也不看,把他拿起来扔在钱抽屉里,直接蒋抽屉一块就推给了过来。张三把存折拿在手里看了,有些喜滋滋地念道:“三万五,十桌酒在这也就是它了!”
张三与贾二论赌的这会儿,厨房里的厨子,刚才欲走未走的客人,这会儿全都重又围了过来,要看这场难得地大买卖。
张三的蛐蛐罐放在桌子上,金丝线嵌的猫蝶图,是那样地惹眼,人们心里在不断地琢磨:就这一个不起眼的东西,就能值了好几万?可看张三立在那,像对那堆钱不屑似的,眼睛都快要看到天上去了。
贾二脸上有些不动声色:张三还在等什么?贾二有些不耐烦了:“三哥,要玩就麻利点早动手,这人越来越多,一会儿刘子来了,不定还说我在这聚众赌博呢,别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张三把眼一横:“刘子?他敢!有三爷在这,还没他说话的地儿!”
正说着,文先生在人群里探出一个脑袋来,要看这在干什么。这一探让张三看见了,过来拨开人群道:“文先生来得正好,做个中间人,免得到时双方不好!”
文先生用手捋着三绺胡须,有些得意:“二位都是苟儿胡同响当当的人物,我今儿个既碰上了,也就讨口酒喝,来!击掌为凭,速战速决!这人多口杂,别让人家给搅了。”
张三道:“有文先生作保,那咱们就开始。”俩人说好一把定输赢。
贾二这会儿一支接着一支地在抽着烟,眼睛盯着那桌子上的骰子,像狼见了血似的。
张三道:“谁先来?”
贾二抽着烟,咬着腮帮子:“在我店里,当然是三哥先来!”
张三像那桌子上的钱已经归了自己一样,脸上早已憋得有些像是拉不出屎来,抄起桌上喝茶的水碗,一仰脖把里面的水都喝了,又将桌子上的骰子一把抓了放在碗里头,用另一只手摁住碗口,摇了起来。就听得碗里“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张三将骰子摇了半天,突然“啪”地一声,将碗扣在桌上。
贾二铁青着脸,额头上像沁出了一些汗珠。
张三一把掀开碗,只见里面两个骰子一个四点,一个六点。早有人在一旁叫道:“老板,把手搓红了,稳住点!”
张三瞪了那人一眼,那人吓得直往人后躲。
轮到贾二,贾二双手捂着骰子,也在空中摇了几摇,再把手举得高高的,“嘀……嗒”两声,将骰子滴落在碗里。
张三眼睛都快要掉碗里了。只见碗中滴溜转了一下,两个骰子稳稳地停在碗心,一个是八点,另一个还是个八点。
文先生站了起来:“一把定!没得说的,三儿,你还呆在这儿干什么?”
张三听文先生这一说,头也不抬,连蛐蛐罐都不看一眼,拨开人群就走了。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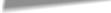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