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絮飞来一片红·之一 |
1
春天来了,花儿又开了!
这北京城,多少年多少代也都这样:雪还没化呢,便先见着了一枝枝火红火红的腊梅花儿;接着是一丛丛、一簇簇、黄澄澄的报春花儿;再下来,百花都竞相开了,人们也准备脱了厚厚的冬装,要去看百花吐艳竞相争春的时候,天上便纷纷扬扬地下起了一片片白色的柳絮花儿。
柳絮花儿不似别的花,她既不能看,也不能赏,可它却像雪花儿一样,满天飞舞地飘着,能把整个北京城给罩住啰。
女人们拿出去年收起来的纱巾,将漂亮的脸蛋裹的严严实实。男人们却没有女人这般幸运,那讨厌的柳絮花儿,时时刻刻往鼻子底下钻,让你不得不用手来回来去地搓着鼻子。
这缠人恼人挠人的柳絮花儿……
在京西,有一条东西向、哪那都是柳树的胡同,每年这个时候,满天飘洒的柳絮迎面而来,胡同的犄角旮旯里、墙角中、瓦楞沟上、大杂院当间、哪都是一团团旋转的絮状,避不开,躲不了,扫不净。不知是柳絮花儿的原因还是别的,这胡同里从此便没了别的花儿,谁家种花儿也不活,人们都说:这是柳絮花儿闹的。
家家户户都不养花的胡同,虽不像别的胡同那样,侍候这个花儿,侍候那个花儿,隔三岔五地培养出一二个稀奇的品种来,让世人羡慕不已。可生活在这个胡同柳絮花儿堆里的人们,却把人伺候得一个个地水灵。胡同里,三年五年,不时地冒出一个二个令人羡慕的名人来。
这胡同,便是苟儿胡同。
苟儿胡同,原先叫狗儿府村,经过上千年的演变,才有了这个雅驯的名字。要说胡同名字的来源,胡同西头的文先生可有得说法。
文先生是胡同里最有学问的人,这几年名声更是在外。据文先生说:唐太宗征高丽时,路经河北三河县姜福山甘泉寺,借兵于寺僧,和尚闻听打仗杀人,僧众顿时哗然,多不相从。太宗东征回军,要泄这口窝囊气,遂将寺庙围困。
甘泉寺前,有两只护寺看庙的石狗,见兵丁凶猛,故而狂吠不已。太宗夜闻狗吠,挽弓射矢,一发没镞。第二日前来视察,见寺前一石狗身中箭瘢,血泪潸然,太宗惊骇,遂罢兵领军回朝。后来该寺历经千年,镞虽早已消亡,但镞的铁锈处却宛然可验。不知又过了多少年,寺前那只中箭的石狗,逃遁的不知了去向。直到前几十年,北京西城狗儿府村的农民在刨地时,偶然刨见地中有一狗首,与甘泉寺前那只看庙的狗头相似,村民闻知,尽来挖掘。可那狗身埋在土中,随土随挖而下,始终只露一首于土上。村人害怕,知道石狗不愿出此尘世,复将土埋了,狗儿府村自此名播京城。以后,村民在此建屋起灶形成胡同,村人嫌这村名不雅,遂改狗儿府村为苟儿胡同了。
如今的苟儿胡同,当年埋狗头的地方早已不知在哪个方位了,可苟儿胡同的名气却日渐里长,越来越大。那些挨着苟儿胡同的胡同,也像沾了这胡同里的灵气,一天一天地跟着冒出些名人来。您瞧!苟儿胡同西面的,有棵大枣树的后泥洼,出过沈从文;北边的狗尾巴花儿胡同,如今叫高义薄的,几十年前,身边围着花季般少女许广平的鲁迅,带着不合时宜的朱安和老娘,在那个胡同里出了大名。如今,那所他们住了好几年的大宅子,都供着人们瞻仰呢!再往北一点的八道湾,虽然周作人的故居,早被街坊们堆着的破脸盆、破尿盆、破瓦罐什么的大小杂物,可那灵气儿,至今没散得了,还在呐!要不然,哪来那么多好事的文人墨客,一路过这儿的时候,总免不了要指指点点:“这是八道湾,周作人与鲁迅兄弟俩闹翻后便住在这里……”
挨着苟儿胡同的一条斜街,原先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四合院,如今,四合院被拆得没了踪没了影,可一提起来,人们还不免挑起大拇指:“嗨!那是大画家王雪涛的故居!那是……
只可惜了!没了!
如今的苟儿胡同,扬着名的,是胡同东头大杂院里远近东西城尽皆知道的三轮车工人张三和他八十四岁天天攥着两个拳头把蚕豆咬得嘎叭脆响的盲人老娘。
2
张三娘八十四又是个盲人,可那张到老了还有模有样的老脸上,让谁看了谁不说?这胡同里的花儿,自打张三娘年轻时那会儿起,就把这胡同里的花儿羞死了!人们都说:张三娘是苟儿胡同里的老妖怪,花精哩!
张三23岁那年结过一次婚,新媳妇是前泥洼做老头鞋老王家的闺女玉凤。
老王家的闺女玉凤,俊的和花朵儿一样没得说的,不多话,不惹事,对爹娘又孝顺,爹娘也把她看得跟个宝贝似的。可玉凤姑娘长得不像爹不像娘,倒与张三长得如同兄妹。
街坊邻居们说:“都说夫妻同相,那人家是老夫老妻,这倒好,才结婚呢,怎么就一个模样?”
前街后坊又都说了,这是张三天生的缘分。
唯有胡同西头拐角处的杨家大宅院里的杨老太太,把老王头找来问了:“你那闺女叫玉凤?是和平解放北京那年抱养的吧?”老王头不知这杨老太太也知道这事,正要细问,只见杨老太太听后直叫唤:“造孽!造孽!”
苟儿胡同西头拐弯处的这座杨家大宅院,是胡同里最大的一所四合院。高高的灰院墙,两扇朱漆大门中开着一扇小门,旁边一个小车库;院子里有两棵大槐树,还竖着一根又细又高戴着一顶小尖帽的烟囱;里面静悄悄的,从来没听见过有人声传出来。杨家的儿子是个大干部,自打杨老太太搬在这住,就从不与胡同里的街坊来往;唯有小汽车回来,见着一个二个人影时,那也是脸无笑容,不和胡同里的人打招呼;苟儿胡同也就没把他们当街坊看。
老王头不知是积了哪辈子的德,居然被召到了里面,见着了尊贵的杨老太太。可杨老太太说的话,老王头听了却不乐意:自己的女儿结婚大喜,杨老太太却说这样晦气不吉利的话。欲问原委,杨老太太再也不言语了。碍着杨老太太儿子的虎威,老王头把心里的怒火压了又压,没敢发出来,回去了。
结婚那天晚上,张三终于送走了来贺喜的客人,娘不等收拾完,就推着张三进洞房:“好儿子,照娘说的,陪媳妇玉凤去吧!”
火红的蜡烛,早烧得张三心里的欲火跟那蜡油似的直往下淌,就等着娘的这句话。进到洞房,新媳妇玉凤端坐在床沿,看那样子像有些在微微的颤栗,头上盖着大红的盖头,随着微微的抖动,像要融入整个洞房的红颜色。
张三早已耐不住,一把将盖头揭了,疯了似的把新娘玉凤抱上床,摁住了,就几下功夫,张三便把自己弄泄了。迷迷糊糊就要睡去,这才记起了老娘教的生儿子办法,懊恼了半天,起来想吹了蜡烛再去相拥而眠,可床上的新媳妇玉凤半天没动静,将新娘玉凤扳过身来,没想,老王家的闺女玉凤躺那儿早没气了。
这一惊,张三不觉恐惧地尖叫道:“娘呀!……”
娘听见了张三的惊叫,过来安慰道:“玉凤她没挺住,那是她没这福分!如今女人尝过了,安心拉车吧!”
可就这一嗓子,整个苟儿胡同都知道了。
街坊里有人说了:张三他娘命硬!娶过来的俊媳妇玉凤要与老太太比俊呢!可她没比过盲眼的张三娘,能不死吗?有的则说:是张三那玩意儿太长太大,小媳妇玉凤是给他肏死的!好端端的一朵花儿,楞给张三糟践了!
尽管同院的姜大妈在一旁骂道:“别胡说八道,信那些封建迷信。”可谁的嘴也没堵住。
派出所把张三叫去问了:“你媳妇脖子上有两道用手勒的红印,你怎么就把新媳妇卡死了呢?”
张三有些迷惑不解:“我娘教的,女人要摁住脖子的,卡了脖子憋住气,那才能痛快!”
派出所里又问了:“那你家伙上又放什么来着?”
“没放什么!我娘教我顶着别泄了,准生儿子,可我没绷住。”说着话,就要脱裤子让派出所的民警看家伙。
派出所里没话说了,把验尸结果给了居委会,也告诉了街坊邻里大家伙,说是典型的新婚猝死症。
街坊们私下里议论的话,从此一传十,十传百,远近京城里,没有谁不知道,苟儿胡同里有个肏死了媳妇的张三。
老王头痛罢女儿就是不明白:自己造了什么孽?女儿玉凤才嫁过去一天就死了?想起杨老太太的诅咒,老王头找到杨家大宅院要去问那杨老太太,可门口的警卫从此一见了老王头,便给挡了回去,赶的远远的。
以后张三娘几次托人给张三再介绍,可谁家的姑娘也没有胆量敢嫁张三了。张三从此与老娘相依为命,拉三轮养活自己,也养活着盲眼的老娘。
张三脾气越来越爆躁,浑浊闷愣,又爱打抱不平,除了经常与人犯楞吵架耍横打架外,还常常在外惹骚事。
那年电视演员牛比大走红,京城里火火的。前门大街的老舍茶馆前,是个拉活的好地方,坐车的人手头也阔绰。这天中午,张三与几位拉三轮车的哥儿们正在树荫下歇着,一边候着活,一边扯淡吃着中午饭。各人各自掏出带来的馍、大饼和用大可乐瓶装的凉白开,吃着喝着话便侃到了那些不三不四没油没盐的骚话和浪话上来。
中午的太阳骄阳似火,大街上没几个人,吃完喝完侃完,张三前后看看,自言自语道:“歇会儿呗!”将肩上的毛巾擦了擦汗,自顾自地躺到车里去了。架着二郎腿,用毛巾盖着半拉脑袋,眯缝着眼睛,像似在睡,却不时地又在窥察着四周,别错过了叫车的。
远处,新近走红的演员牛比大与两位花枝招展的明星姑娘,从喷着凉气的轿车里勾肩搭背地出来,正好经过张三的车前。
两个漂亮姑娘,一位穿着一双又红又亮的皮鞋,一位穿着一双又白又灿的靴子,两双嫩白丰满匀称富有弹性的肉腿,迈着轻盈的步子,像是两对依偎在一起不断游弋嬉戏的鸳鸯。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地在牛比大身边闪着。
就这么一眼,张三的心里呼地一下立刻就热血沸腾,翻搅着一股无名的冲动。张三眯缝着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在搭着的毛巾后面一下子直奔牛比大扫过去。
“牛比大!”
牛比大回过头来,见身后并无熟人,有些茫然地顾盼了左右,嘴里嘟囔着,与姑娘们直奔茶馆而去。
张三见状,又大吼一声。
“牛比大!”
牛比大再次回过头来。
张三坐在车里挺了挺腰,梗着脖子用手指勾着牛比大:“叫您呢!”
牛比大这才看清是张三在叫自己。
牛比大恭谦地弓着身子过来与张三打招呼:“师傅,是您叫我?”
张三:“不叫您,叫谁?”
牛比大有些丈二和尚:“我以为您叫别人呢?”
张三没好气地:“这世上能有几个可以挽着女人在大街上横行的牛比大?”说着话,又用眼剜了牛比大身旁两个姑娘一眼。
牛比大见张三那直勾勾的眼神并没看着自己,而是盯着身旁姑娘的那两双细腿,于是道:“咱们认识?您还有何指教?”
张三这会儿回过神来,像有些泄了气:“演员要谦虚点,以后别摆那个架式!”
牛比大看了看左右两姑娘,有些自嘲地:“不敢,您还有何吩咐?”
这会儿张三真像个塌拉下来的皮球,一头倒在车里,两手将毛巾把半个脑袋一盖,丢下一句话来:“没事啦!还能睡一觉!”
三轮车的哥儿们在一旁看着这一出,捏了烟头过来要逗乐子,张三却蒙头大睡,只觉得心里头一股腥骚味直往鼻子里钻,整个下身没了力气。
张三心里明白,自己的老毛病又犯了。
张三扒豁子,给自己惹麻烦,可在一块蹬三轮的哥儿们却总是在犯难的时候,有张三援手。出力、出钱时张三连眼皮都不带眨一下。前年,一块拉车的刘四被一地赖讹上了,张三决定要为刘四打抱不平,出口气。
这天,那地赖摆着一副特狠的架势又来找刘四,往刘四的车里一坐,抬着胳膊一努一努地欣赏着上面刺的纹身。
张三过来一看,见那胳膊上刺着一对凶猛的二龙戏珠纹身图样,心里这气便不打一处来,过来一把薅住那地赖的脖子,按在地上一顿暴揍,打得那地赖跪在地上直求饶。张三住了手,指着地赖胳膊上的二龙戏珠问道。
“这叫什么?!”
地赖答道:“二龙戏珠。”
张三一听,接着还打,直打得那地赖在地上又哭又嚎喊爹喊妈。
张三指着胳臂上的二龙戏珠再问:“这是什么?”
地赖这回学乖了:“两个皮皮虾玩一球。”
听到这,张三自己倒忍不住笑了起来,住了手,放了地赖。以后,那地赖再也不敢来讹刘四了。
众哥儿们一致说:张三就是够哥儿们。
3
张三家住的这个院子,原是一个坐北朝南,四方蹬正的四合院,相传当年冯玉祥的一个秘书买下来后,在里面养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妾。后来解放了,这秘书家败落了,人也自此不知去向。从此搬来了街坊邻里大伙儿,再后来,你一家,我一家的生儿育女,院子里的那点空地儿,便渐渐地被各家占去,见方见角的四合院,从此没了形,没了样,成了一个大杂院。
张三家碍着几十年来人丁不旺,又是院里最赤贫的劳动人民,虽没去占块地、建个棚什么的,可这娘俩住的却是政府分给的院内最好的冬暖夏凉的北屋。
张三自打会认人开始,便不知道爹是什么样,看着到老了还有模有样,皮肤白皙皙的老娘,张三经常问自己:爹到底长什么样,是干嘛的?怎么就我生得这般难看。几十岁的人了,要说脸面上五官的搭配,除了秃眉毛外倒也不缺啥,可一单一双的眼皮下面,却包着一双细细的灰眼珠儿,像是一对小母狗眼。两眼角还不定哪边永远有着一块黄呼呼的眼屎;惟鼻子生得挺拔丰满,是相书上说的“悬胆”那种,可偏偏鼻孔朝天翻着,露着两撮鼻子毛,在鼻梁正中还长着一颗不大不小的黑痣,像粒没扒拉掉的鼻衄,甚是碍眼;两片想要吃四方又厚又阔的大嘴唇,不说话没事儿,说起话来下嘴唇便直往上翻,说着说着,两边嘴角便结着一层白沫,像个小尿盆似的;脸上的皮肤紫黑紫黑,夹杂着一些坑坑洼洼,总让人感到,这张三,昨儿夜里干什么去了没洗干净?身材长得倒也算匀称,可走起路来爱扛着肩膀东张西望。剃着一个板寸,半睡半醒半醉的样子,把个脑袋卷缩在脏兮兮的衣领里面,不熟悉张三的人见了,总以为那是个贼胚子。
看着胡同里一个个有模有样,张三常常暗自埋怨:都说这胡同里有灵气,人人都水灵,怎就一点没给我?
还没改革开放那阵子,张三一年四季穿的是一套旧军装。这些年,北京一年一个样,变化大了,张三也随着大伙儿,改穿了袖口扎着商家标签的时兴西服,唯有那绑腿和那双薄片儿蛤蜊张的老头鞋,还透着满身的皇城根大爷劲儿,掺和着那永远散不尽的劣质烟油子味儿,一直没改得了。
张三常常觉得自己投错了胎,对自己不明不白的身世,有时站在院当中,面对诺大的四合院宅子浮想联翩:老爷子或许也是个什么王爷的小王爷?或者是大清朝的什么大臣什么阿哥?要么干脆就是那个冯玉祥的秘书?年轻的时候,张三也赖着问过娘,可娘什么也没说,像是对以往失去了记忆。娘有个守得紧紧的纸胎漆皮小红箱子,张三自小就想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可到如今,张三都快五十了,老娘也没让自己打开过,这更让张三幻想不断。
张三脾气坏是坏,可有一样好,那便是吵架不记仇。大杂院里虽然和谁家都干过仗,可一转身见了面,还照样是哥长姐短的。更加上张三成天在外转悠,见了石头都有三句话,又常将外边三轮车哥儿们的笑话,带到了院子里,再将院子里的家长里短,带到了三轮车哥儿们那边,倒也在里在外是个人见人爱的人物。只是那些笑话经张三口这一传,话里话外,从此添加了赤裸到裤腰带以下的话去了:“男人不坏,有点变态;男人不骚,是个草包;男人不花心,绝对有神经;男人不流氓,发育不正常。”
大杂院里,但凡是有人聚在一起,不像是人家院里下棋看球什么的,准是张三在那将外面的荤话诨话昏话鬼话瞎话和时下的民谣倒腾着带了回来,在给街坊邻里们这一番素说。
院子里漂亮的娘儿们、姐儿们、大妈们、大婶们,一边听着,一边骂着:“好个没羞没耻的张三大流氓!”一边骂着一边笑着,可一边还忘不了耸起耳朵来听着,生怕漏了哪一句关键的词儿。
有时候在胡同里,张三也照样吼着那大嗓门,逮着谁叫谁:“娘儿们,姐儿们你真美,让我亲亲你的嘴;大妈大婶你真骚,让我揉揉你的腰;媳妇儿小姐你真坏,干吗解我裤腰带?……”喊得路过的左右街坊们,常常是脸红心跳,可胡同就那么宽,想绕都绕不开。
“娘儿们、姐儿们、媳妇们,不生孩子不合被,都到我这儿来问问。”
对面来的是一群水灵灵的小媳妇,不知谁说了一句什么没油没盐的话,逗得大伙儿顿时笑岔了气,弯着腰按着肚子在那儿喘着。
张三手中扬着一根满是倒钩刺的“虎鞭”,对着迎面而来一字排开的娘儿们和姐儿们道:“今儿个劲松潘家园贩古董的客人给我一根虎鞭,要不要捎回去给大哥、大爷壮一壮啊嗨!哥你昨天枪太软,枪太软;独自一人自摸实在可怜。到天亮,匆匆让我干一回,实在太简单。我没到高潮心里太难耐,哥你身体不行怎叫我宝贝心肝!姐儿们!要我这虎鞭么?”
苟儿胡同的娘儿们姐儿们,虽说什么样大风大浪的世面都炼过,张三念的这些时下都市民谣,如今哪那都在唱,本来早已不稀奇,可经他张三这一改造,便觉得有些新鲜了。更稀奇的是,张三手里晃动着的大山里的老虎鸡巴,您还甭说,谁也没真见过到底是什么样。以前常听人说:“驴屌黑、马屌紫,老虎屌上带倒刺。”莫非就是这东西么?
看着举得高高的满是倒钩刺的虎鞭,女人们心里活泛了:饭馆柜台上,常见大玻璃瓶里泡着一些这鞭那鞭的三鞭酒,带刺的那个,可和眼面前张三手里的这玩意儿一摸一样。那些色迷迷的男人成天嚷嚷着要喝这鞭酒喝那鞭酒,敢情诱惑他们的是老虎那股子骚猛劲儿!
张三手里的虎鞭还在那里使劲地摇着,看着又长又粗富有弹性满是倒钩刺的虎鞭,这玩意儿要是让自己的男人吃了,或许真能壮一壮,猛一猛……
正遐想间,突然有人醒悟似地骂道:“你张三拉一趟活多少钱,坐趟三轮就能给你一条那么贵重的大虎鞭?那也太让你占便宜了!”
娘儿们姐儿们媳妇们带着脸上还未消退的红云,就骂开了:“好个大光棍张三,敢在咱姐儿们面前耍流氓!”哄地一下子散开,追着赶着假装着要撕烂张三那张无遮无栏的骚臭嘴,与张三没完。
也有平时文文静静不言不语羞羞涩涩的小老娘儿们,这会儿倒没羞没耻地调侃开了:“那么一条又粗又大的虎鞭,你张三先自个儿壮一壮呗。”说到这,竟自顾自“嘿嘿……”的笑起来:“壮起来你张三搁哪蹭去呀?”一边说着,又是一阵“哧哧哧哧哧……”的嗤笑:“我家那条母狗倒挺乖挺懂事儿,就怕你那大虎鞭忒大了挺不过来哩!……”
说到这,漂亮的脸蛋灿烂得像一朵朵花儿,红云是退了,可笑声却银铃般的更加清脆。
张三听到这,心里像是被什么狠狠地戳了一下痛处,脸上有些少见的不自在,举着虎鞭,蹬着满身铃铛响的三轮车回家了。
可娘儿们、姐儿们的心里,早给张三手中的虎鞭和那些没黑没白的浪话,撩拨得三分情骚惹起了七分肉痒,巴不得真要从哪去寻条又粗又健带倒刺的虎鞭来,让自己的爷儿们好好地壮一壮,给自己猛一猛。想到这,下面便不由得一阵发紧。
女人们互相看一眼,心照不宣地“嘿嘿嘿嘿”像一群无忧无虑的麻雀散了窝,在张三的背影和笑声中各自回家了。
白天有荤话诨话好打发,可夜里闲下来和侍候完老娘后,张三有时便觉得有些无聊,常常在被窝里手淫完后就想:是该有个女人呐!可一想到自己的名声和健在的盲人老娘“唉……”转而一想:真是可以养条母狗嗬,但又一想,老娘八十四,又是个盲人,自己成天在外拉车,谁侍候狗啊,那狗要是饿急了,还不把老娘给吃了?
想到这,自个自地躲在被窝里“嘿嘿”傻笑一声,翻个身,呼噜噜地睡去了。
4
张三家院里住的几户人家,东屋是一对小年轻夫妇,结婚几年了,想生个孩子都想疯了,可那女的连个响屁也没一个。小公母俩四处寻医问药,直闹得男的越来越瘦,女的却越来越胖。那男的本来就瘦高瘦高跟螳螂差不多有一米九,这几年吃药下来,人就像是个病秧子。在自家的屋里,那女的没一天不埋怨:真是一头多长了条又长又大后腿的笨驴。可街坊们在院子里侃大山,那女的偏要在人前显摆,说自己的男人有多高有多壮。
张三有回听急了,半调半侃地打断那女人的话说:“操,杆子长!就是不开花儿,不结果!”
女人被噎得不说话了,回屋里哭了半天。
那女的除了四处寻找吃了能生孩子的药外,什么爱好也没有,在娘家时就爱养花。刚嫁过来的那会儿,见胡同里家家户户不养花觉着奇怪,于是在门前用两个破木箱子盛了土,想种点喇叭花、爬墙虎什么的,一来花儿好看,二来叶也好遮挡西晒的太阳。可是种了几年,那花怎么也不活。后来想种些黄瓜、丝瓜烂贱的瓜果也不行。唯有一种叫“死不了”的指甲花,不知是从哪里飘来的种子,在荒了的木箱子里,时不时地冒出一两朵小花儿来,这就算是她的绝活了。
那女的从此倒省了买指甲油的钱,成天用这指甲花儿的汁,天天地抹着永远抹不完的指甲,与那倔强的指甲花儿,比着谁的色艳色好看。
街坊们私下里议论:“花妖在这院里呢?您那花儿能旺?”
大杂院像应了胡同里人们的传说,院里各家的小娘们和老娘们,一个个赛花妖,谁见了谁觉得这院子里邪乎!
西屋里住的是一对温州来北京做运动鞋买卖的,男的有点矬,矮巴溜丢是个小矮个,别看他人模样不怎地,娶个媳妇却格外靓丽,可惜这漂亮女人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专在家里给老公和儿子烧饭洗衣做家务。忙定了,便穿着漂亮的衣服在胡同里瞎转悠,明里说是要看街坊养的花,暗地里却是想让街坊们看她的漂亮衣服、听人们在后面议论她家如何有钱和评论她那张靓丽的脸蛋。儿子寄读在附近的小学,光一年的寄读费就好几万。可温州人会挣钱,小俩口也不在乎,每日吃得好,穿得好,潇潇洒洒地隔三岔五不是龙虾就是甲鱼大王八,吃的满胡同里都溢着王八味儿。
胡同里有看着不顺气的,便时而传来了一些小声大骂:“中央二台可又曝光啦,温州的鞋贩子用纸壳做皮鞋,穿一回,就开口了,坑人真不浅,国家怎么就不逮他呢?这种人,就像皇城根下的一泡屎,把世界都臭翻了,非得逮了遣送回原籍,他就不敢神气,老实了!”可骂归骂,做归做,人家温州客一家三口,除了片警小刘来查户口时哈着以外,腰板挺得比苟儿胡同里谁都直,睁眼瞎的媳妇照样在胡同里显摆她的漂亮脸蛋。
南屋住着两户,靠东边的一户,是保洁公司推销洗衣粉的,男的成天在外卖洗衣粉,长年不着家。这些年推销洗衣粉发了点小财,让谈恋爱的儿子带着女朋友在外面买了一套楼房住着,儿子很少回家。漂亮的女主人在家寂寞,便像养孩子似的养着一条狗,“儿子!儿子!”地叫着。京叭小狗听了,摇头摆尾地过来直往那女人的怀里钻,伸着大舌头,在那女人漂亮的脸上来回来去的舔着。
狗初来的那会儿,张三看着也有几分可爱,时不时地还伸出手来逗一逗,可时间长了,那狗常在张三修车时身前身后转着舔着碍事儿,张三没了耐性,飞起一脚,直踢得小狗在地上滚了好几个滚,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夹着尾巴呜呜咽咽地躲回自家屋里去了。从此见了张三,绕着躲着远远地离他八尺地“嗷!嗷!”地吠吼两声,躲在主人的门后面,连正眼都不敢瞧张三,再也不到张三面前来晃了。
靠西面的两间屋子里,住着东城袜厂的退休工人姜大妈。
姜大妈他爸早先在京城里是有名的木匠,按京城里的说法,是个有“玩艺儿”的人。练就的一手木匠绝活,雕只老鹰能飞,刻个螃蟹会爬,建房做屋,梁上的花有花儿的香味,兽有兽的威风,趴在门柱上的螭吻能看家护院。可惜老爷子只生了姜大妈一个独女儿,没奈何,那人见人爱的木工活,只给传了个大概给姜大妈,从此姜大妈抡着大斧子在袜厂做着袜楦。后来袜厂改制了,倒闭了,姜大妈提前退休了。
姜大妈只传了老爷子一半的手艺,可老爷子生女儿的本事却给她包了圆儿。
姜大妈年轻结婚时就想生个小子,偏偏肚子不争气,一直生到四十多岁,一连养了八个女儿,个个水灵漂亮赛过花朵儿,就是没一个带把的。人们都说:胡同里的花妖就在这个大杂院里,没错!
如今,花儿一般的女儿们,都从这院子里飘着嫁出去了,老头子也先走了,就剩自己一人了。(一)
姜大妈好管闲事,什么事都爱掺和。苟儿胡同里的人当面喊着“姜大妈”,背地里却都叫她“胡同串子”。居委会相中了姜大妈的那副热心肠,让她管着胡同西头最难管的菜市场。从此,菜市场里转悠着一个满身肥嘟嘟肉膘子,有点簸箕脚的老女人,左手戴着一个红袖标,右手常拿一把笤帚的,那便是姜大妈了。
张三说诨话不管不顾的海天海地,可这整条胡同里,唯有一些忌讳的,只有姜大妈。
以前,张三说诨话昏话在姜大妈面前也是不管不顾的,甚至有时还拍着姜大妈那肉滚滚的大肥腚,不紧不慢地道:“哪天劳您拾掇拾掇您那大热炕,也让我三爷暖一回。”
姜大妈那会儿也跟没事似的,有时还会围着张三像不认识似的瞅一圈,见张三仍不知天高地厚地咧着嘴,姜大妈知道他不定还要放出什么厥词来,于是在张三的肩膀上拍了拍揶揄道:“馋坏了吧张三儿,臭拉三轮烂光棍,您那,哪凉快哪待着去吧!”一边说着笑着:“哪天是得让老娘帮你把那家什撸下来。”说着笑着居然真的要过来薅张三那小肚子下的家什。
张三疯笑着躲着:“别!……别!……留着它还有点用处,儿子就指着他呢!”
姜大妈这才颠着那身肉膘进了屋。
后来有一档子骚事儿,彻底地让张三在姜大妈面前趴下了,矮了半截了。从此,张三在姜大妈面前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那是张三死了媳妇后有好几个年头的一个夏天,守着盲人老娘便没别的女人的张三,这天收工回来,听着隔壁公共小浴室里洗澡的哗哗水声,便耸起两只耳朵开始浮想联翩,心里头像有一团乱麻,堵得自己越来越难受。
伴着“哗哗”的水响和自己无边无际的遐想,张三躲在自己的屋子里狠命地打了一通手铳,等到“唔唔”的声音终于发出来,身子像软瘪了的柿子一样瘫倒在床上,张三这才跟拔了气门芯的车带,算是发泄完,松了那口憋在心里的鸟气。
耳朵倍儿灵的老娘在外屋喝粥,早听见了里屋的动静,嚷嚷道:“三儿,哪儿不舒服,过来让娘摸摸。”
张三用手提了大裤衩:“没不舒服,您吃您的,我挺好!”出了屋,端了盛小米粥的大海碗,拿了大馍夹着咸菜,蹲到院里的台阶上,不断转动着大海碗,喝一口粥,啃一两口馒头,那眼睛却时不时地看一下通往浴室的地方。
姜大妈穿着宽大的汗衫从浴室里出来,提了一个塑料桶,头上用毛巾裹着,一只手在头上来回擦着水,趿着一双花木屐,肉嘟嘟地从张三身旁走过。见张三蹲在院里喝粥,打着招呼道:“按根呐!”张三随口“唔”了一声,只见姜大妈那肥大的汗衫袖口中,露出抖动着的两只耷拉下来猪尿泡似的大奶子,一时间,裤底下便硬梆梆地挺得难受。
小米粥里的沙子碜了牙,张三在一旁直“呸!呸!”可心里却骂道:“她娘的老妖精!骚货!”
张三在心里恶狠狠地骂着,眼睛可没离开那撅着的大屁股。
第二天,张三早收了一会儿工,回到家,小浴室里姜大妈正在洗澡。
张三三下五除二支好了自己的车,蹑手蹑脚来到自家的里屋。
昏暗的里屋,张三轻轻地掏出自己塞在墙洞里的小棍儿,墙上立刻透着一个萤火虫大的亮点。张三紧张地扒在墙缝上,大气也不敢出,弓着身子用眼朝墙缝的小洞中往里瞅。
蒙蒙胧胧的浴室里,两只粗短的赤脚趿着那双艳丽的花木屐,什么也没瞧见!张三心里正待要骂出来,将身子往下哈了哈,视线往上抬了抬。这回,终于让他看到了想看的东西:老妖精赤条条叉开双腿,仰着脸在冲水呢。
水从头上一直流到脚底,浑身上下,虽是隔着一层流动的薄水,可还是能看清白是白,黑是黑。那白的,水流到那,便被隔着分向两边流去了;那黑的,在水的冲击和水的压力下,倾刻间被熨得妥妥贴贴;又见凸是凸,凸的真是个地方,直让你想上去咬一口;凹是凹,凹得让人要挺进去探个究竟。水在凸处,缓缓地如屋漏痕,悠悠哉哉,像个闲逛的顽童,不愿离去;水在凹处,匆匆地像崖边瀑,急急忙忙,“吱溜”一下,钻得不见了。
水顺着身体不断地往下滴着淌着,在昏暗的光线映照下,依然有些晃眼。
张三口干舌燥,一边拼命地咽着口水,狠不能自己钻进那个小洞里去,耳边也开始在“嘭嘭”作响,一颗心跳得跟布鼓雷门般。
浴室里,姜大妈劳累了一天下来,头上的柳絮花儿,身上的土,都在赤身裸体尽情享受的水蓬头淋浴中,一冲而净。沐浴带来的痛快,让姜大妈嘴里哼哼叽叽那听不清分不明,不知是京剧还是评剧的曲调,一直就没停下来。
好半天,姜大妈终于磨磨叽叽地擦着身子,翻着口袋似的大奶子上下左右地抹着。这会儿,正扶着墙擦脚呢。
突然,姜大妈发现墙缝中有一双鼠眼在里面滴溜乱转,那眼睛正盯着自己瞧呢!姜大妈先是吓了一跳,随之便明白过来。
倾刻间,浴室里跟见了鬼似地惊叫开了。
姜大妈连衣服也没来得及穿,披着大浴巾光着身子,扛着那两个猪尿泡似的大奶子,冲进了张三家,揪住张三照着头脸便打:“打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张三流着哈啦子正津津有味地看着浴室里出神,姜大妈的一声惊叫,把他从云雾霄霄里拉了回来,还没等把哈拉子抹干净完全反应明白,姜大妈暴风骤雨似的大肉巴掌,已落在了头上脸上肩上背上,架都架不开,只有抱头鼠窜往屋外奔逃的份了。
见张三跑了,姜大妈竟然站回屋拿了那把锈迹斑斑的斧子,一手叉着腰,一手挥舞着大斧子,指着张三鼠窜的身影大骂道:“看老娘的身子!你等着!看我那天不将你那段臭肠子剁成三截!省得再害人去!”
老太太什么也看不见,开始听见姜大妈冲进门来,坐在那跟没事似的问道:“三儿,你又害你婶什么来着。”后来又听着他们都冲出了门,这才杵着拐杖走到了自家的门前问道:“他大婶,三儿又怎么啦?”
姜大妈这会儿缓过神来,被老太太一问,反倒不知怎么回答了。于是答道:“没什么,老太太,您歇您的,我走了。”披着浴巾,提着那把大斧子,回自家屋去了。
这一晚,姜大妈怎么也睡不着,在床上辗转反侧,竟然不是恼张三,而是一直在想着自己年轻时候与自己那死去的老头在床上的好戏。直到迷迷糊糊地听见了胡同里的狗吠声,张三娘却杵着拐杖来对自己说:三儿他可怜,四方托媒,也说不上一个媳妇,看来张家是要断香火了……
张三在外面直躲到三更半夜,才悄悄地溜回了家,躺在床要睡,可白天浴室里姜大妈那雪白肥胖的身子,像放电影一样,在自己的脑子里一遍一遍地放着,张三在床上像贴饼子似的睡不着。手也不自觉地向下摸去,直等到自我满足、全身放松了,这才呼噜呼噜地睡死过去。
从此张三见了姜大妈,像狗见了扁担,顺着脖子流着汗,捋着尾巴骨直奔大腿下去,灌了一鞋坑儿,矮了半截头。有时在院里荤话骚话的兴头上,见姜大妈从外面进来,张三便会对大伙说:“散了散了,明儿再来!”众人也就知趣地散了。
姜大妈自打那次张三犯骚后,并没把这事儿往心里去,肚子里揣着的那副热心肠子,早把那骚事给融化掉了。只从此不再参与张三的荤话和鬼话,每天在市场照样是管了东家管西家,成天红袖标不离手在菜市场里转悠;街里街坊的照样串着门子,邻里邻居照样帮着照看张三那八十四岁的盲人老娘;时不时还将市场上买到的便宜白菜萝卜,给张三娘拿过些来。
可张三还是怯着三分姜大妈,整条胡同里,就只怕着姜大妈一人。
|
|
被文坛.浮 世 收录 原创[文.爱的传说] 收 藏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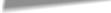 |
|
回帖 |
 |
|
| 回复人: |
zimalian |
Re:柳絮飞来一片红·之一 |
回复时间: |
2006.02.27 19:05 |
|
又是一篇绝好的影视素材!别只在这里放着,可惜了儿的,改成剧本呀!
|
|
|
| 回复人: |
多喝了三五斤 |
Re:柳絮飞来一片红·之一 |
回复时间: |
2006.02.28 11:26 |
|
呵呵,希望看到的是一幅历史长卷!
|
|
|
| 回复人: |
真龙女 |
Re:柳絮飞来一片红·之一 |
回复时间: |
2006.04.05 19:24 |
|
哈哈,我晕了.
|
|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