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你就是要伤害你 37-38 |
(37)
她走后,我在家门前的石阶上坐了很久。雨已停。黑夜在四周游荡。我想着她刚才的那些话语以及那个灿然的微笑,这些究竟代表什么含义?她在向我暗示什么?我恍惚感觉那笑意里埋藏着一层隐隐的凄凉,伴随着某种孤独。我的心不知为何突然间漾起几许悲伤,淡淡的悲伤,无色无味,在失落与怅然中徘徊。
我久久地闭目沉思,力图让情绪得到控制,使之平静。我知道,这是她的话语自然而然地渗入自己心中的结果。为什么呢?其实那不过是一种假定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中蕴含的锐力却是致命的,势如秋风横扫落叶。她那灿然的一笑里,包含着深刻的内省和暗喻的回声,将我心中长久以来渐渐形成的某种定式一举粉碎。尽管那定式尚属混沌之初的雏形,但毕竟给了我清晰的存在感和平衡感,而现在这一切犹如梨花纷纷,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的目光落到了院子里那只蓝色花盆上。花盆里种着秋海棠。多年来第一次看见那枝海棠似乎有些枯燥。我全身微微一怔,再次闭上眼睛:仿佛一扇看不见的门悄然打开,阵阵穿墙的冷风从另一世界嗖嗖吹进安静的院子。我觉得一瞬间有一种东西完结了,微妙地、决定性地完结了。我感到一次死亡,我的心百感交集,我开始思念起那个一直暗恋我的女人,那个对我而言没有裸体,却充满激情的女人,犹如远方的音乐里横着一堵爬满了长春藤的石墙。我心里涌起一股无可排遣的孤独与悲伤。
有人这时柔柔地握住我的手。滑腻的手指与玲珑的掌心握住了我的手,握了相当久长的时间。
我被那只手温暖着,但又感觉似乎有些不现实,这感触不过是往日记忆的再现,逝去的日子重温于心。是的,是记忆的重温,温煦的记忆的重温。那掌心有股热量源源不断流入我的心田,如阳光普照冰凉一夜的大地,寒冷倐然间消褪,悲伤和孤独般的寒冷倐然间消褪。是谁啊,竟然有如此的魅力,可以瞬间化解我心中的忧郁。
我睁开双眼,夜依然黑暗,我看不见那个人。我对着周遭仔细搜寻,空气这时骤然发亮,泛起一圈细微的波纹,波纹似涟漪般一圈圈放大,院子的景致与周围的建筑在涟漪中渐渐弯曲,随着波纹一起在荡漾中远离。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般的幽暗,有点像演唱会的前奏。不久眼前空间豁然明亮,如周日的晨光透过百叶窗射进房间,同样的光照,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布景,同样的色调。我对这一切了如指掌,甚至可以呼吸其中的空气--星月之下躺着那片熟悉的海,此刻涛声阵阵,有风自海面吹来,夹裹着浓郁的略带腥气的海草味。
我深深呼吸着海风,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直握住我的那只手上。是她,那个蒙面女孩,她坐在我身边,衣衫贴近。她仍然蒙面,甚至连双眼也被遮蔽其间。尽管如此,我依然感觉出她的美丽,那是一种绝世的美丽,带着清纯与高雅。此刻我与她心灵对接--有某种信息在悄然传递--她不是陌生的,就细节而言,她是我熟悉的某个单体,但又极其模糊,从整体来看又甚为遥远,似有似无,像重力和暗物质--两者都是明显存在的客观形态,但却无法用数据加以证实,使执着的人常常露出空茫的无奈。然而我对那只手还是有着清晰的记忆,只要今后的现实中它再次触碰我,一定能唤醒沉睡的感悟,让我知道她是谁。
海面方向吹来的风这时突然停滞,海草味消失。我反手抓住蒙面女孩的手。空气微微一颤,传来她的笑声。笑声亦是如此熟悉。我来不及细想,她已开口说话。“为何要抓住我的手?”她问。
“怕你消失。”我望着她说。
“这次不会那么快了。”再次传来她的笑声。
“那就好。”我盘住腿,望着她说,“见你一次真不容易,而每次的时间又太短。”
“海底相遇那次为何急着走了?”
“因为时间到了。”我应道,“此前刚刚答应过一个人,不再做任何使她担惊受怕的事。”
“你是对的。我很高兴,为此。”她说。
“能告诉我你是谁吗?”我问,“总感觉你平日就在我身边。”
“常有这样的感觉?”
“没错。而且越来越强烈,那感觉。”
“你是对的。但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我是谁,至少目前。”她摇摇头。
“我总在暗暗观察,谁有跺右脚的习惯,可是仍然一无所获。为什么?”
“刻意的隐藏。”她说,“知道你在找我,时机不到,只能如此。别介意。”
她身上着一件月白色的连衣裙,质地很好,剪裁细腻,做工精巧。里面夹带一些光滑的线条,在星月下闪闪发亮,但我说不清楚那是什么材料。她脸上的白色面纱也比我记忆中的要精致得多,好像是用极好的手工缝制,似乎透过面纱看外面的世界一目了然,然而从外面看她,那面纱却是严严实实给人一种滴水不漏的感觉。她一头齐肩的黑发,看上去英姿飒爽,千娇百媚。我觉得不长的时间里,她的气韵形态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身体苗条且渐感丰满。
她突然一声长叹,叹声奇妙动听,如兰花吐露,夜莺柳鸣。
“你怎么看我和邓岚?”良久,我问蒙面女孩。
“这是你为之烦恼的现实中的问题,”她应道,“尽管我也是作为现实的形体和你在一起,但在眼前这片天地里,我不能回答你。因为这里是唯一忘我而纯洁的一隅--它既不在虚幻里也不在现实中。”
“那么,这片天地究竟存在于何处?”
“在另外一个你的心里,”她应道,“他在历史烛光的另一端,镜像世界里,与你相对而立;你们心心相连,连接之后的心才是一个整体,在你们内心最深处的地方,有一座没有门窗的房子,这世界就在那房子里。”
“那房子我知道。”我说,“但里边是什么,真是陌生得很。”
“你们偶尔也换位,但次数并不频繁。”她继续说,“你们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着的。但在现实中的形态,有时是你有时是他--内在结构上可以如此划分,但极不准确,因为毕竟都是你自己。”
“现实中,”我说,“综合的感觉,邓岚离我最近。可对?”
“那是错觉。”她说,“那是悬浮于你心里的一种廉价的感情,属于沉沦的爱情。”
我望着她,惊讶得睁大眼睛。“愿闻其详。”
月光下,她隔着面纱一直望着我,片刻之后幽幽叹了口气。“你处在一个充满欺骗、贪婪和冷漠的现实里,只要你甘愿将一切纯洁、神圣和梦想扔进垃圾筒,那么你想找寻一份普通而廉价的感情并非难事。如你和邓岚,一夜之间就完成了升华。之后呢,便是空虚和茫然,否则你也不会问她‘今后该怎么办?’这样愚蠢的问题。表面看,这些只是思考方式的不同,现实中也确实存在不同的思考方式,但归根结底,仍是江河归海的问题。”
“我从没想过要使自己的爱情变的世俗化。”我说。
“这点我清楚。”她轻轻一笑,“我经常进入你的心灵,你的所想亦是我的所想的一部分,所以一切一目了然。你所经历或是即将经历的爱情可归纳为四类:沉沦的爱,悲惨的爱,失落的爱和圣洁的爱。至于你与哪些人之间发生哪一种爱,恕我不能对号入座,因为我所知道的也就是这些。我只能看清你是事件的主角,亦能看清事件本身,但有关事件的另外一些角色,基于同性相斥的原理,她们离我极其遥远,以致我的目力无发达及。所以我无法看清。但我已经听到有人在哭泣了,不止一人在为你哭泣。”她停顿片刻,望着我,“我感觉你在颤抖。”
我点点头:“是的,我在颤抖,那是来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条件反射。你对爱的诠释,除了圣洁的爱之外,其余都是令人痛苦的过程。这些是如何发生的,能够避免吗?它们之间有何关联,是必然的客观存在,还是单个的、突发性的偶然性事件--就像某些进化媒介消失后在时间的烛光中茫然四顾的独生物种?我想知道,我真得很想知道。”
她一直望着我,尔后用平静的口吻说道:“这些我也不知道,我和你一样不清楚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我只能说这些事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因为我已经看见了它们,我清楚发生的过程,每一个细节以及结尾。除此而外我一无所知。当然,对这些事件的出现,不能归咎于某一个人,任何人都无法负责,任何人对此都束手无策。包括你和我,都只能静观事态的发展,尤其是你,作为与所有事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进入结构性流程的逻辑内。”
我有些绝望,沉默不语。
“该说的都已经说了。”良久,她叹了口气,“若说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话,想来想去,也就剩下最后一点了--这些发生在你身上的诸多爱情,形象点说,就如同汉字里的那个‘卐’字,其上端是你圣洁的爱,也可以说是‘垂直的爱’,如你夜望星空那样;左端是你失落的爱,右端是你悲惨的爱--这两者亦可称其为‘平行的爱’;下端就是沉沦的爱了,它是由本属于平行的爱因遭遇偶然性蹦塌所造成的。但这些存在的形式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某种条件下,它们的性质和位置是可以发生转换的。具体的转换过程我也不清楚,我仅知道,假若时间和空间在结构上误入歧途而无法自我纠错时,转换就会发生,从而造成逻辑的倾斜、变形和混乱。直接的后果导致在现实中以何种形态出现,我一时难以说清楚。也许永远都说不清楚。我真得无能为力。”
我叹口气。“有个问题。”
她点点头。
“你在这个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思索着说,“我觉得自己在以往的人生中苦苦寻求的似乎就是你,似乎你曾以各种形态出现在我赖以存在的现实里、梦里或是虚幻的意像里。你的身影朦胧得简直令我神往,同时又亲切熟悉得无可挑剔。现在回头想想,似乎我们之间曾有过一个约定,一个没有具体时间概念量度的约定,它可以无限久地停留在历史长河中的某一阶段--以等待有缘人的相遇。当然,这仅是纯粹的逻辑内想像,是我刚刚突然意识到的。但我坚信无疑。”
她再次凝望我,这次时间较长。“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她说,“你可以等候,比如三年,到时你自会清楚我是谁。理论上讲,我们会有一次奇遇,命运的偶然排列组合中有此一环,仅此而已。现实中它不具有任何指导意义或实际价值。目前我的位置是在你的头顶,你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再次正告你,这一切并非固态,现在也只是相对的现在,若时间和空间结构发生变异,一切又将陷入困境或是转换。所以‘三年’只是暗示性的,不代表什么,也无法保证或承诺什么。只是一个模糊的方向,不一定完全正确,不属于绝对的概念。无论在虚幻或是在现实,无论在两者之间或是别的世界里,一切均呈现相对性。所以这期间你仍有追求和向往其他境界的自由。”
我默不作声地想了很久,随后说道:“如果从现在起,我不再离开你,和你在一起,就在这片天地里生活三年。所有的困惑该会迎刃而解吧。”
她摇摇头:“这里赖以存在的结构和那边的现实不同。这里是极其封闭的世界。时间在这里发生了弯曲,因此它流失得很慢。即使我们在这里生活一天一夜,在外边的现实中也只是过了几秒钟而已。另外这里没有阳光,没有重力,也没有水和食物,你和我都无法生存。所以你和我都必须回到各自的现实中去。有一点你或许比我幸运:即使你回到现实中,这里发生的事你会记起,而我就不行,我会遗忘的干干净净。我只有来到这里,才会心如明镜,洞察物事。好了,我只能向你说这么多,其余的我很难再用语言向你解释了。刚才我也说了,有些事情的详情我并不清楚,而我清楚的那部分又不便向你解释。”
我望着她,有些垂头丧气:“我就是不想再回去了,怎么办呢?那边太冷,且又潮湿、黑暗,道路布满石头,搬起来很累人;又窄又滑的路走起来亦很辛苦。那边有阳光又能怎样呢?它依然无法直达心底,它能力有限,死角太多,很多情况下无奈又无助。况且我对光明已经失去信心,我不再喜欢它。你让我回去,那也只是虚度光阴,磨损生命,让我肩负起一个走头无路的年华。”
“回去吧。”她沉思片刻,尔后轻易地脱开了我的手,站起身。“阴影不只是你一人才会有。只要在现实中,每个人都有。我也有。但别无选择。去找寻,去把握你心中的那份希冀。属于你的圣洁的爱,假以时日自会到来,但若你无法很好把握,同样也会失去。这机遇并非人人都有。这是造化。还有,别再犯今天下午那样的傻事,如若你的现实形态被毁,这里的一切作为载体将永久关闭,永远不再存在,而处在镜像空间里的那个你也将彻底幻灭。因此你责任重大,不能不慎重从事。”
说罢,她悄然而去,体态轻盈如洛神凌波微步,不久消失在月华中。
天空逐渐阴暗,星月无辉。空气变得稀薄。时空混乱。我在黑暗中迈步,刚一抬脚,耳中听到远方火车驶来的隆隆声音,倏然间又立刻消失。
我屏息静等那声音的再次到来。
我一直沉默。不知过了多久。海潮退走,天空隐匿。时间在混乱中摇摆。我的影子在黑暗中延长、凝缩--腿变得很长很长,全身比例失调。空间正在发生畸变,我本身也随之变形,就像动漫影视中的那些丑角。
但我毫不惊慌,只觉得有些汗流浃背。我闭上双眼,汽笛声立刻迎面而来,伴着火车汽车的形象,骤然驻足在我身旁。然后是大块大块的宁静和蝉鸣。再次睁开眼睛,雨已停了。我仍然坐在家门的台阶上,前面放着那盆秋海棠,在夜色里散出淡淡的幽香。
回到房间,我脱光衣服,去卫生间洗澡,冲洗掉身上的臭汗。随后躺在床上,一边喝酒一边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老实说,我的思绪很乱,这并不仅仅因为我从蒙面女孩身上发现一个以和谐、完美为特点的迷人形象。重要的是她那一句“等我三年”的奇言妙语,如醒世恒言,深深触动了我对一连串往事的怀想。我想到那些如歌如曲的风声,以及在那些落满枯叶的小溪间觅得的一片七角的枫叶。我想,也许感念的实质,是以自觉观察存在主体的特殊规律为标志的;处在这类命运的庇荫下,我或许终将得见未尝的夙愿。然而,相形之下忧伤的情绪又暗然飘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脑袋迟钝了,一些被遗忘的细节模糊了,我得像擦洗旧画像的肮脏玻璃镜框一样费力地回忆。现在似乎已没了那种痛苦的直接感受,只是回忆着从前曾经存在过的痛苦。同时我又无法把握,这些往事存在的确定性。除了在虚幻里挣扎的记忆,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来。
倘若我愿意,也许我可以等待三年,什么也不想的等她三年。之后我们会有甜蜜的爱情,高尚的理解,共同的兴趣,从此一生她都将留在我的视野中。。。。。。可是,我已经不再相信自己了。不相信在花岗岩脑袋的统领下,自己能安全地不受任何干扰地平安度过三个春秋。我想任何一件现实的偶然因素,都会瞬间化作带死结的绳索,将我窒息在等待的途中。
我不知道,那些被她分门别类的爱情都是些什么内容,何时到来,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但我愿意承认,这些未知的故事一定与站在我周遭的那些女孩之间有着某种无法割舍的联系。此时,困惑又开始在脑海中编织着朦朦胧胧的花纹,使我心乱如麻。不知为何,我倐然间思念起那个蒙面女孩来,怀着极其渴望的心情思念着她。然而她在哪里呢?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她知道我在现实中所保持的形态吗?我现在马上就想见到她,现实中的会见,我要向她倾吐自己的心声。可是,在现实中她是失忆的,因而一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她又变得陌生起来。
我独自行走在庸俗、自卑、犹豫的路上,我是否因为过多的忧郁而错失过什么?比如蒙面女孩在过去的日子里是否曾经为我畅开过大门?我是否曾经听到过一种充实的声音、真实的语调,但我却疑虑重重地因大脑发生固有的混乱而自绝于那扇大门之外?有过这种情况吗,到底有过没有呢?
我想不明白,也回想不起来。可我还是隐约记得今晚最先开始思念的是猪猪。我什么时候变得有点花心了?我到底该思念谁?到底谁才是我的圣洁之爱呢?
哦,想不明白就想不明白吧,反正这种情况又不是第一次发生。
现在我的脑袋就像一团浆糊一片混乱,瞬间堆满了杂乱无章的东西。用手敲敲,居然又发出石头的声音。那些形同僵死的意识,呆滞的反应,迟钝的灵感再次占据整个大脑。
今后的事还是今后慢慢再想吧。除了小心翼翼应对之外,剩下的也唯有听天由命了--最后,我自言自语说了一句。
这时,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按下电话机上的免提键--活佛的声音在房间荡开:
“嗨,回来几天也不吭一声!真是!”
(38)
“嗨,回来几天也不吭一身!真是!”活佛说道。一副既显得懒洋洋又让人感觉无所谓的口气,声音不高不低,听不出是高兴还是生气,总之平平淡淡,如一池秋水。
“走之前电话里不是说好的吗?”她嗔怪道。
“没错,是说定的事。”我低声说,“回来后太忙。忘了。真对不起!”
她口中发出一种既像鼻哼又像嗯哈之类的浑浊不清的音调。
我手握话筒,听到这声音,半天想不起一句合适的词语,脑袋乱哄哄的。该说些什么好呢?
“嘿!你怎么了?喂喂!”良久,见我不吭声,她呼唤道。
“好端端地站在这里嘛!” 我笑。
“声音怎么让人感觉有点怪怪的啊?”
“紧张。”我解释说,“有些不知所措。小时候做了错事,都会语塞,口吃和紧张。特别在电话里,放松不下来。”
她沉默片刻。“马上过来!我在会所咖啡厅。”说完“咔”的挂了电话。我拿着话筒愣了半天:过来就过来嘛,干吗那么用力挂电话呢。
我下了床,走到衣帽间,换了身衣服,对着穿衣镜整理了一下头发。然后去了会所。
她坐在角落里,戴着耳机,一边口含着饮料吸管,一边摇头晃脑。头顶天花上的镭射灯光在铺着白布的桌面上勾勒出一幅柔和的图案。
我在她对面坐下,望着她。
“萧洒。”她扫了我一眼,嘴里蹦出这么一句。
“谢谢!”我微笑。
“有点像影视歌星。”她面无表情,带点挪揄地说,“都是绯闻惹的祸。”
“哪里有绯闻呀。”
“那你在忙什么?”她拔掉耳机,拿眼睛瞪着我。“给个合理的解释。”
我叹口气。“不想再旧事重提,但事情纷至沓来,阴霾不散。”
她望着我一言不发。
“邓岚那盘录像带,有人想偷走它。”我解释说,“小偷半夜三更进了我家,被我发现。这小偷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司机。看来是对手老早就安插进来的卧底。感觉一切都是有预谋的,而且蓄谋已久。”
“头疼。不提也罢。”她摇摇手说,“原谅你了,事出有因哦。”随后又望了我一眼,“你运气不错,总能被我原谅。不知下一次能否这么走运。”
我笑笑:“多谢理解!但愿不要有下一次.”随后身心轻松下来。
“饿了?”她说,“刚才路过你家,看见你坐在石阶上像睡着似的。那情形不像是吃过饭的样子。我有没说错?”
“没错。因为没胃口嘛。”
“好了,我已为你点了份新西兰黑椒牛排。”她说,“我也没吃晚饭呢,就算陪陪我。”
“理当如此。”我笑。
“还挺客气。”
“我的意思是,”我清了清嗓子,“每天到一定时间肚子都会饿,有没胃口,乐不乐意,反正总得要吃点东西,给不争气的身体补充点营养。只要你方便,我有的是时间陪你吃饭。理当如此。”
东西端上来后,彼此边吃边聊,她不时抬头看我。牛排味道不错,就是不太对我的口味,只有六成熟,而我一向喜欢八成熟。她更历害,只吃五成熟的,一刀切下去,雪白色的盘底立刻渗出鲜红的血丝,有点恐怖--尤其是一个只有15岁的小姑娘。
我抬头看看周围,琳琳琅琅坐着不少清一色衣着入时的客人,只有我们两人一身冬季休闲的着装。活佛看上去更为秀美洒脱,十足的众星捧月。有些客人不时抬头,目光在她脸上身上闪闪烁烁。但也只是略作停留,几秒钟而已。大概觉得看久了有失礼节或是绅士风度吧。这世界真是蛮复杂的。
“瘦了点。”她低着头说,继续吃牛排。
“或许。”我摸了摸脸颊,“都是被警察给气的。”
“不就一夜吗?”她说,“问你什么了,到底?”
“一夜过得跟一年似的。”我说,“净问一些毫无意义浪费生命的废话,即便如此也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几十页纸。那情景跟我的人生似的,无聊又无奈。”
她抬起头看我,那眼光就像看情人节聚会上被人砸在脸上碎掉的奶油蛋糕。
“你也不赖哦,”半晌,她说,“当着警察的面也能在电话里对着我谈笑风生的。酷毙了。”
“那是否极泰来。”我笑,“实属无奈的举止。希望当时没有气昏你。”
“瞧你,傻里傻气的样子,谁会生气?”她满不在乎地说。
我默然。专心致志地听起背景音乐来。
她吃完牛排又要了一份甜品,继续吃。“这首歌从没听过,”她指着天花板上的那些圆型小音泡,“你可知是谁唱的?”她问。
我低头沉思片刻。“蓦然记起来了,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我皱着眉头,“但究竟是在哪里呢?依稀以为记得了,怎么又无从记起呢?我这破脑袋。”说着我拍拍脑门。
“不急,再想想。”她说。
“噢,对了,想起来了。”我说,“唱歌人叫anouk,属于dutch歌手。”
“从没听说过这家伙。”她边吃边说,“感觉风格上有点土气。”
“荷兰牛仔。”我说,“是个有实力的家伙。”
“没想到北殴歌坛和国内差不多,一个字:土。”她翘着嘴唇说,“你这人。。。。。。”她想了想,一挥手,“算了。”
我笑笑说:“荷兰当然没法和美国比,甚至也没法和香港比。”
她望了我一会,随后低下头继续吃她的甜品。
两个人酒足饭饱后,买完单走出会所。
“你。”她用手指在我的胸口戳了一下,“去把我的行李拿到我家来。放了那么久,有些衣物可能都发馊了。”
当我提着行李走进她的家门时,便感觉有些不对劲,我嗅到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气氛。似乎有什么不妙的事件即将发生或是已经发生了。进到客厅,果不其然,只见活佛捂住腹部横躺在沙发上,双目紧闭,额头有汗冒出。
“莫不是刚才饭菜有问题,吃坏了肚子?”我问道。
她不答。只是对我摆摆手。意思是与饭菜无关。我说那就去医院吧。她摇摇头。
“没有用的。”她有气无力地说,“这就是我以前对你说过的那个病。吃什么药都没用,只有忍着,过一会就好了。”
我扶她斜靠在沙发上,给她背部塞了一个靠垫,又把脚凳搬过来,把她的双脚放在上面,使其疼痛尽量减轻点。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有效,不过电影电视里都是这般处理的。
房间里有点闷,我走到阳台,推开一扇窗户,让室内空气流通。雨又悄然下起来。雨滴很细,细得几乎看不清楚,只是有风吹来时,方才感觉脸颊和头发被涂上淡淡的湿润。天空阴暗,几乎没有可称之为星光的星光,雨下得很安静。我把一只手伸到阳台之外,手心凉凉的略感雨丝的浸袭。
“回来!”她低声叫我,表情依然很痛苦。“给我倒杯热水。”
我点点头,不久把一杯热水端给她。她抿了一小口就放下了。看来还是不行。
“用热水袋是否有点作用?”我问。
她点头:“厨房有,自己找。”
我进了厨房,略微搜索便找到了。随即灌好热水递给她。她放在小腹处。
我坐在她身边。“吃点止痛药之类的不行吗?”
她有气无力的摇摇头。看来不行,我想。这是什么病呢?上次她倒是对我提起过,但我似乎没听懂。
又是一阵疼痛,我拿毛巾为她擦去冷汗。她的头自然而然地歪倒我身上,整个身体也靠在我怀里,脖颈僵硬,脸上粘着几根汗湿的头发。她双手抱着热水袋,紧紧压在腹部,如此久久地纹丝不动,只有胸部随着呼吸而有规则地起伏,但看上去也是微乎其微。总之疼痛使她的呼吸变得极其轻微,感觉她只是稍稍吸进,略略呼出。仿佛吸一口大气就能夺走生命似的。我心想,这孩子为什么如此楚楚可怜呢?每每有需要时,亲人都不在身边。更小的时候她都是怎么过来的?莫非这也是她的命运不成?我尽管总感到生活对自己不够公正,但现在看来,处于同样境地的并非我一人。于是我伸展双臂轻轻抱住她,心中泛起一股要呵护她的感觉。
如此过了半个小时。她微微张开嘴唇。“口渴了。”她小声说道,依旧紧闭双眼,吞了口唾液,“在杯里加点热水端给我,不要太烫。”
水杯和热水壶都在茶几上,伸手可及。这次我自己先试过冷热后,再慢慢喂她,她缓缓地抿了几口。那情形着实令人怜悯。喝完水,我又为她擦去额头冷汗。她舒适地躺在我的怀里。
两人便久久处于这样的姿势:我坐着她躺着--像小鸟依人那样躺在我的怀抱中。也许这是人的天性使然,我自己对此深有体会:每当心灵或身体遭遇痛苦时,总有一种隐隐约约求助的欲望,总想有一个温柔的怀抱能让自己安睡其中,使痛苦借以减轻。因为那个怀抱自己的人同时也在心灵的层次为自己分担着痛苦。活佛或许较之于我稍稍幸运一些:今夜有我为她分忧。可是他日若我遇此境况,届时又有谁为我分担苦痛呢。外面的雨依然很细,但势头似乎比刚下时急了些。天空有很低的云团飘过,被霓虹灯照映得五彩缤纷。此刻,她僵硬的身体稍稍松弛,头软绵绵地靠在我胸口,我什么话也没说。
她闭着眼睛,眉头微微舒展,呼吸依然轻微恬静,仿佛熟睡一般。汗湿的头发紧贴在鬓角额头,鼻腔随着呼吸微微颤动。脸色的黧黑似乎褪掉许多--被海南冬日的阳光晒成的黧黑。我继续用毛巾擦拭她脸上的汗和湿了的头发。偌大空旷的房间异常安静,偶尔能听到断断续续的雨声。
良久,她睁开眼睛,头依然靠在我的怀里,她把模糊的眼光转向我--身体某处依然疼痛的眼光。我身体不动,伸出一只手端起调试好热度的水杯放在她的唇边,这次她轻轻摇了摇头。用手指着热水袋。
“再加点热水。”她低声说。
我轻轻放开她,进了厨房将水袋里的水倒掉,重新加满热水。回到客厅后先将她抱起平放在沙发上,头下放了一个软垫。我将热水袋递给她。随后又拿过一件外衣给她盖上。
“去楼上第三间房,拿床毛毯来。”她说。
我上楼拿来毛毯,严严实实地将她裹起来。随后搬过脚凳,坐在她身旁,眯缝起眼睛看着她的脸。她脸色显得十分疲惫,那模样活像被病魔折磨得濒临绝境之人。这时,疼痛再次袭来,她全身立时一阵抽缩,冷汗又从额头涌出,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地忍着。
我再次坐上沙发,让她躺在怀中,不停地为她擦拭冷汗。感觉她的衣襟已经湿透,汗渍斑斑。过了很长一阵,痛楚渐渐减轻。终于听到她轻微的鼾声,低头看她,已经熟睡过去。
凌晨二点,大概雨停了很久以后,月亮从云端里露出了脸,乌云渐渐散尽,月明星稀。寒流在肆虐数天后,终于游走他方。
活佛随后醒来,脑袋在我胸口微微移动,长长的睫毛眨了眨,轻轻伸一下懒腰。刚才她熟睡时,我一直呈坐势,连动都不敢动,生怕弄醒了她。
“还疼吗?”我问。
“嗯,好多了。”
“那还是疼。”
她点点头。“与刚才相比,这不算什么了。”
“刚才好恐怖。”
“吓到你没有?”她问。
我说没有。只不过比较焦虑,看见她疼痛成那模样,自己在一旁却毫无办法。束手无策的。那一刻恨不得自己变成医生。
“是医生也没用,”她低声说,“那一刻也毫无办法。无非是打止痛针,即便打了也还是疼。不信你变医生试试。”
我笑:“变不了,说说而已。只是凸显当时的心情罢了。”
她靠在我怀里沉默片刻。“有时感觉你像空气。”她说,“无处不在,却又看不见摸不着。”
“唔。”
“假若你变成空气,也许就没那么多烦恼了。”她说,“你这人太多的伤感。可对?”
我笑:“变成空气就没有烦恼和伤感了,你怎么知道?”
“嗯,有道理。”她想了想,“也许空气亦有烦恼和伤感也说不定。只是我们人类不知道而已。”
“对极了。”我应道,“空气也有伤心的时候,比如酸雨--那是工业污染的结果;比如沙尘暴--那是环境遭破坏的结果。这个世上,不仅仅是人,所有的客观事物都会有伤心烦恼的时候。只是表现特征不同罢了。”
“假定空气不会有烦恼的话,”她一字一板地说,“你还是变成空气的好。”
“为什么?”
“我可以把你装进一个大玻璃罐里。”她孩子气地说,“放在窗台上晒太阳。”
我笑:“那不等于被关进深牢大狱?本来像云一样的自由自在也没了,而且每天看着你起床吃饭睡觉,自己又一筹莫展,头发还不早早白了。到以后你嫁人的那天,总不能搬个玻璃罐当你的证婚人吧?你在玻璃罐上贴个‘证婚人’的红色字条,向出席婚礼的嘉宾宣布玻璃罐里的空气就是你的证婚人,还不把大家笑翻。”
“不会啊。”她说,“打开玻璃罐的盖子,你一出来就恢复人形不就是了。”
“那要惹出大麻烦。”
“怎么讲?”
“你想想啊,”我笑,“我一出来又变回人,高高大大,英俊萧洒,你的新郎还不气得跳楼。”
“为什么要跳楼?”
“还不明白?”我笑,“新郎对你说,噢,你就和这个人在一间房里朝朝暮暮生活了那么多年。我还是跳楼吧,只听‘噗嗵’一声,婚礼变丧礼。你说悲哀不悲哀?”
“嗯,只要你不再返回玻璃罐里就行。”她说。
“唔。”
“抓你来顶替啊。”她笑。
我说,自从我们认识以来,很少见你笑过。你对我要么冷言冷语,要么毫无表情。有时我真有些怀疑你天生就是一个没表情的小姑娘。
听我如此说,她说我这人要么傻里傻气,要么经常惹她生气,所以很少对我笑。不过除我以外,包括她父母在内的任何人,她自始至终从没有对他们笑过。也许就因为我的傻里傻气、形为举止不同于常人,才使我因祸得福见过她不多的几次笑呢。我说不晓得自己哪里不正常,但我知道自己肯定不正常,假若有一天我要是变得正常了,那世上人人都是疯子了。
她听了嘻嘻一笑说:“喜欢和你在一起。”
“为什么?”
“和你在一起玩没有任何压力,”她说,“又能放松自己。似乎一切藩篱倐然间消失,唯一剩下的是对自我的尽情挥洒,就像漫山遍野的雪花,无忧无虑地任意飘飞。”
我想了想说:“有同感。对你说的深有同感。不敢对别人说的话,却敢对你说;压抑在内心很久的情绪时常无意间对你流露出来。有时我对此感到非常奇怪,你不过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如何能够承载这一切?但你还是承载了,而且做得很出色。我对此常常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我还不够成熟,许多事情还想不明白。我的人生不够健全也不够完善。”
“是有时候,”她强调,而后停顿了一下,“对你的某些想法有时理解得非常透彻,有时又似是而非、糊里糊涂的。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大概是你的问题。”她继续说道,“我的意识常常为你的情绪化的东西所左右,也就是你说的‘诗意的’东西。这对我来说很有意思,随意识而意识,随情绪而情绪。”
“唔。”
“反过来讲,你也受我的影响,受我的左右。这点早看出来了。”她说,“只是恍惚觉得你的内心彻彻底底还是个孩子,需要我来呵护--简直就像是发生在月亮上面的童话故事。”
“这故事不坏……”
“我说,别仅仅把它当作故事好不好,”她纠正我的话,“这不仅是故事那么简单,借用你的话--它有深刻的暗喻,亦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其实,我这样说都是为了你好,除了我,可有人一心一意地为你设想过?嗯?”
“好像没有。”我思索片刻,然有肯定地说:“是的,一个也没有。”
她的头依然靠在我胸前,呆呆地望着外面的月光。我用手悄悄替她掖好毛毯。
“和你在一起玩的感觉就是奇妙。”她说,“要是能一起去月亮上面玩或许更开心!”
“去月亮上面玩些什么?”
“在那里飑车啊,”她抬手指了指月亮说,“那感觉一定酷毙了。”
“月亮上面根本没有空气,”我指出,“汽车引擎离开氧气就无法燃烧,也就无法发动,如何飑车……”
“就要飑车嘛,”她细声细语地说。也许她对我的话没听进去,或者是根本没听。但其声音之柔软却让我心情悄然紧张。至于什么原因倒不清楚,总之那里面含有一种令我紧张的东西。“是有时飑车无需空气嘛。”她继续说,“而且我觉得在没有空气的地方我和你依然能够相处,我有这感觉,也是这样认为的。”
“比如说?”
“海底。”
“我们背着氧气瓶,”我说,“那不能算。”
“海底有氧气吗?”
“是有一点,在分子结构里只占很少一点比重。”我说,“靠肺功能呼吸的动物无法生存。”
“我就指这个。”她说,“有那感觉,一直模模糊糊的感觉,像你一样,说不明白。但就是好玩!”
“总想着玩也不是办法。”我说,“你总要长大,上学,成材。”
“我对自己还是蛮了解的,”她说,“不骗你。我这样说,是要向你表明,在往后的任何时间里都不会忘记你。”
“是哲学意义上的说辞吧?”
“不,”她说,“实际意义上也是如此。”
“可你不是18岁或者更大一些。”我说,“你还小,你不懂时间为何物。时间能将一切记忆磨损掉,包括刻骨铭心的记忆也会淡化。”
她摇摇头,望着月亮:“我不会。即使长大,上学,工作,我都不会。就像月亮,无论你走到哪里看她,她都是那么圆那么亮。”
我默然。她这些话尽管很美很动听,但毕竟透着浓郁的孩子气。我想不出合适的词汇与之对答。
“要不你飞到月亮上去。”她指着月亮说,“这样我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看到你,看见你在那棵桂花树下乘凉。每当这时我就会想:嗯,他还在那里等我。我得快点长大。”
我笑:“那里可是冰火两重天噢。对着太阳的一面热到摄氏几百度;背对太阳的那面冷到零下几百度。”
“你是说月亮上面会这样子?”
“对呀,我要是去了,分分钟就翘辫子了。”我说,“那你天天看到桂花树下的不是我的生部,而是我的白骨骷髅噢。”
于是她赶紧把指向月亮的那只手放下来,放在我的手上,指尖冰凉。
“就是喜欢和你一起玩嘛!”过了一会,她说,“希望玩的时候,时间突然断裂,我不再长大,你呢,也一直都停留在25岁零6个月。然后大家一直开开心心玩下去。此时的世界,天既不会荒,地也不会老。多么奇妙啊!”
我微微苦笑,本想对她说点什么,却终未顺利出口。她那么漂亮,人又单纯得像一绢白绸。我当然对她怀有好感。和她在一起的时间也过得十分惬意,她如一片超逸脱俗的风景,使我陶醉其中,从而忘了世间的所有烦恼。我喜欢看她无忧无虑的样子,喜欢看她带着耳机摇头晃脑听音乐的样子,喜欢看她在大海中翱游的身姿,甚至喜欢静静欣赏她的一颦一笑以及对世上的一切漫不经心、满不在乎的神态--这一切里透着很阳光的朝气、洒脱与活泼。这是我曾经拥有而现在已经失去的东西。因此和她在一起,既享受了诸多快乐同时又找回了失去的过去。何乐而不为呢?但是。。。。。。
但是怎么说好呢?
最后我还是什么也未出口,因为根本就想不起确切的词来。同时感到她在为我的沉默而暗自忧伤。她虽然一直出神的望着月亮,但我还是感觉到了来自其内心深处的那一丝失望。她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一切正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只是她自己对此并无觉察。这一刻,我即便想起什么来,也无法对她出口--我不忍让她伤心。现在我只能这么想。
这时,月亮从豁然敞开的几片薄云间探出脸来。我坐姿未改,她依然靠在我的胸前。我们静静地、一声不吭地望着月亮。良久,有几只夜鸟飞过天空,发出一阵嘹亮的鸣叫。它们在呼唤什么呢?我想。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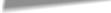 |
|
回帖 |
 |
|
| 回复人: |
鸽子飞翔在梦中 |
Re:爱你就是要伤害你 |
回复时间: |
2005.06.05 23:01 |
|
|
|
|
| 回复人: |
海蓝宝石 |
Re:爱你就是要伤害你 |
回复时间: |
2005.06.05 23:44 |
|
继续吧~~有始有终嘛~~林子里肯定有人一篇一篇的在看呢~~~
林子没法和搜狐比呀~~每天来逛的也就200多~~:)
|
|
|
| 回复人: |
鸽子飞翔在梦中 |
Re:爱你就是要伤害你 |
回复时间: |
2005.06.05 23:46 |
|
遵命!
|
|
|
| 回复人: |
梦飞舞 |
Re:爱你就是要伤害你 |
回复时间: |
2005.06.06 00:08 |
|
呵呵,还是我好吧!关键时刻总会来给你捧捧场。谁叫你今天把人拉到这儿,明天又把人拉到那儿的。
关键是你有到处留情的习惯,我们可没有啊!!!嘻嘻~~
|
|
|
| 回复人: |
阳光下的蒲公英 |
Re:爱你就是要伤害你 |
回复时间: |
2005.06.06 07:36 |
|
被人狠狠损了一顿吧~
|
|
|
| 回复人: |
左手华彩 |
Re:爱你就是要伤害你 |
回复时间: |
2005.06.06 14:06 |
|
林子每天就200来人在线
这又不是秘密
又没人骗你林子每天有10000人来玩
你自己愿意来 不是吗 不是吗 不是吗 不是吗?
|
|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