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你就是要伤害你 36 |
(36)
第二天一早,我尚未起床,她打来电话。
“昨夜几点走的?”
“凌晨一点左右。”
“碰我了没有?”她迟疑了一下。
“你说呢?”
“我说你没碰。”她想了想。
“怎么知道我没碰?”
“感觉。”她笑。
“是吗?”
“不是吗”
我嘿嘿笑道:“是没碰你,因为你醉了。但从性质方面理解,这事并非不可能。”
“但你终究还是没碰。”
“这要水到渠成,两情相悦吧。”我说,“不可力致,不能投机取巧,更不能趁人之危或是趁人醉酒。否则既不道德也无乐趣,与禽兽倭寇无疑。”
“算你是个君子。”
“不过,我反对!”
“噢?--”她声音拖得很长。
“刚才我强调的只是一面之词,”我说,“那是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只是从虚假出发到达虚伪目的的一种自我解说。其实,这件事单纯得很。昨夜碰了你,我们之间就会出现天翻地覆的新气象,两人感情更上一层楼,从此高举高打以致九天揽月。虽然我的大脑,意识乃至生活一直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估计还将继续混乱下去。但有些事不言而喻,确是命里早就注定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一直处于自我意象与外在意象之间的虚幻中,这种日子过的很是奇妙,一切呈现反向特征,时间颤抖,意识变形,智力扭曲,逻辑摇摆,但这毕竟是属于我的世界,是属于我的非任何科学特质能改变的世界,它在现实与梦幻之间保持均速移动,两极部分如铜墙铁壁,将之紧箍其间。我就生活在这里,我栖身在其中,听到铁壁外面遥远世界的回声,听到那里有人哭泣,为我哭泣,为我不能为之哭泣的存在而哭泣。每当这种时刻来临,思绪就会像水一样从墙壁的缝隙间汨汨流入,冒着热气,天赋中仅存的那份好奇便受到激发。但我同时亦无法忘记自身所处的现实形态,它终究会有弃我而去的那一天。仅此而已。”
她默然。大概在思考我的话。
“瞧我笨嘴笨舌的,”我清了清嗓子,笑:“解释得一塌糊涂。”
“不,你描绘得很出色。”她很认真地说,“你讲的我隐约明白,但全部理解尚需要时间。”
“不妨静等暗示性以具体的形式出现吧。”
“无非是要耐心等待了。”她淡淡地说,“做到恰如其分,不是一味地只追求效果。”
“时常有那种感觉。”
她沉默片刻。“有时还真有点捉摸不透你,”她说,“既像是个相貌堂堂的谦谦君子,又像是个不修边幅的行为艺术者。很前卫的那种。”
“不管怎么说,就当都是我好了。”
“当然。”
“不会不开心吧?”我笑。
“什么?”
““因为我没碰你。”
“那倒不至于,”她说,“不过的确是有点儿失落。嗳,在你眼中,我是不是一点那个都没有?”
“啊?”
“就是性感啦。”
“哪里,”我笑,“就因为没碰你,昨晚我差点流鼻血。其实你当时处于极度危险中,只要我心念稍有差尺,你当即就会被我给‘喀嚓’了。知道什么是秀色可餐吧?”
她一阵朗朗的笑,那声音在电话里依然听着甜美。我正欲问她是否记得昨晚商定外出散心的事,话还没出口,她那边已经挂了电话。也许她昨晚喝多了,讲的全是醉话,我想。
看看表,快九点了。下床去卫生间洗嗽一番,回来后还想睡。但又睡不着,心里有事。还在想邓岚,想她头缠绷带的样子,可怜楚楚地躺在医院里。不知此时伤势是否好转。我起身斜依在床头,给符警官打电话,这回通了,我报了姓名。
“你好。”对方很快想起我是谁了,语气温和。
“很抱歉打扰你了!”我说,“就是想知道邓岚的伤情和案子的进展。”
“啊,关于这些......”他有些犹豫不决。
“当讲则讲,”我说,“属于保密范围的我一句也不要听。总之,不想给你带来麻烦,也不想使你为难。”
“明白。”他说,“先说说受害人,她的病情有些反复,主要是脑部的伤口所致。现在她已转往广州治疗。至于医院嘛,由于案子的性质目前还没搞清,所以不便透露。主要还是考虑到受害人的安全。”
“这我理解。”
“关于案子,”他想了想,说道,“虽然有一定难度,但必破无疑。你知道,我们这里是国际箸名旅游城市,南方航空十佳属于名人,不仅公司方面在催我们尽早破案,就是市领导也多次打电话过问,说此案不破对城市负面影响很大。所以我们这拨人马最近一直扎在此案上。”
“非常感谢!”我说,“今后如需要我提供什么线索时,尽管来找我就是。我一定配合你们。”
“说句题外话,”他说,“这个案子,你有何看法?”
“一定是内部人干的。”我思索着说,“定是有人暗恋她,那晚看到我们一起喝茶聊天很开心,所以就下了毒手。同时买通她的亲戚嫁祸于我,达到其泄愤的目的。”
“还有吗?”
“目前能想到的就是这些。”我说,“不过我是外行,说说自己的看法而已。未必有什么参考价值。让你见笑了。”
“哪里会呢。”他笑,“你的意见至少是一个选项。那好,有空再聊。”
放下电话,心情有些难过。如果案情真如我说的那样,邓岚岂不是为我所害?不管策划者与施暴者为何人,但归根结底是为我所害。关于这点无论如何我都要负起该负的责任。
我躺在床上一边抽烟,一边在心里诅咒这个社会,从内心深处升起一股极端的蔑视。这世界里还有阳光吗?还有温暖吗?似乎都没有。有的是令人不齿的污秽、莫名其妙的卑鄙。每个人都是舞台上的表演者,不断地表演着自己,也不断地表演着他人,或者说为他人使用,甘愿为他人表演而唯独迷失了自我的个性与良知。人人皆无真象真貌,人人皆以反复不止的变脸为乐或是以面具取而代之。我软弱无力地立于这臭气熏天的舞台边缘,身后是断裂寒冷的深渊,眼前是伪善者们的人生画妆舞会。我望着自己的双手,掌心红润,只有这双手还表现着某种诚实,但手掌的边缘同样沾满腐烂的气味,怎么洗也洗不掉。如果切割掉腐烂的组织,是否意味着我将不再失去什么?不再失去心里残存的那点温暖和憧憬?没有答案。四周沉默。一切全靠自己去寻求。或许未来的日子里我不再拥有美丽时刻,那倒也罢,只要周遭的一切能够从善如流我也甘愿。想到这里时,倐然间感到坐立不安,胸口郁闷、心脏窒息,就像一只膨胀到极限的汽球,稍再加力便会砰然而破,巨大的冲击波几欲穿肋而出。
我起床下楼走出小区,来到街上,在苍茫的天空下慢慢行走。也不知走了多久,过了几条街,恍惚中感觉有雨点落下,寒风四起,我将风帽从衣领处拉起罩在头上。虽然此时四肢开始冰冷,雨下得更大,但我一如既往地朝前走着。脑袋依然混乱不堪,耳朵响起重音,不是音乐声不是撒克斯管独奏也不是Artist的演唱会。世界一片喧嚣,杂音庞大,我听到远方尖锐的呼啸声,不是飞机起落,不是火车加速,不是轮船鸣笛,就是呼啸声,像灰云一样游走在天边,像起重机吊塔一般悬浮在半空;它不断变幻形态,不断变幻色彩,就是声音不改,呼啸声犹如墓碑从时间与虚幻的深谷中腾立起来--向我昭示--那是我的记忆,正被不透明的空气包围,粗糙而尖硬,雪一般冰凉。我开始明白,似是而非的明白,那位蒙面女郎为何对我又是跺脚又是摇头,那分明是一种失望,一种任凭时间穿越深渊而麻木不动的深深失望,就像我对这社会、这世界的失望一样。这时眼前街景消失,我看见白骨出现,像森林一样生长;血肉消融,若江河一般流淌;那正是我自己的身体--现实中虚幻的形态,此刻正化作尘埃在风中飞扬。
这时有人对我说,嗨嗨,你去哪?我突然被什么东西禁锢,飘在空中的部分重新落地。我回头,看见一个年轻女子拉住我的手,她的手心很热,仿佛来自地心,我冰凉的全身不久被那热量游走数圈。我渐渐回神。
她拉着我来到一处温暖的餐厅,先叫人给我上了一壶热咖啡和加热鲜牛奶,尔后叫人去隔壁商场卖来全套新衣,几个男服务生拉我进了洗手间,不由分说脱掉我身上湿透的衣服,换上买来的新衣。等我回到座位后,身体渐渐暖和许多。
桌上摆放许多食物,香味诱人。我这才想起,早、午两餐滴米未进。于是稀里糊涂地吃了双份三明治,喝了二杯咖啡,一壶热牛奶,大饱其腹。至此,脚尖与指尖也恢复了常温。意识慢慢正常,头脑渐渐清醒。
年轻女子坐在我对面,伸出一只手在我面前晃晃。
“还能认得出我是谁吗?”她说,“刚才你怎么啦?差点撞到汽车。”
我抬头看了看她,似乎没看清楚。我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又坐了片刻,站起身来就走。
“嗳嗳,怕是太冷淡了吧?”年轻女子追上来挽住我的胳膊,她大概以为我还像刚才那样连站都站不稳。“又不是素不相识,怎么好像不认识似的呢?”
“送我回家。”我低声说,没走几步就感觉双脚发麻,两腿酸软无力,速度慢下来。我看了她一眼,“我没开车。”我说。
“好的,我送你回家就是。”她搀扶着我边走边说。
我一声不响地坐进她那辆红色的莱克赛斯轿车。她一边开车,一边不时从倒车镜里观察我。我扭头看着窗外。雨依然下得很大,海上的雾开始浸入城市,将一幢幢高楼拦腰抱住。天地之间一片迷濛。街灯开始亮了,在雨中显得一片昏黄。
到了家,她扶着我下车。进屋后,王妈惊慌失措地问她:“这孩子怎么啦?”
她摇摇手。“没事。就是淋了点雨。你煮壶热咖啡,里边再加点白兰地。”她对王妈说。
王妈进了厨房后,我望了她一眼。“扶我去书房。”我低声说。
上了二楼,推开书房门,里边照例是一片狼籍。我在沙发上坐下,一声不吭地望着她,同时耸了耸肩膀。
“请给我一个合理地解释。”我说。
她时而双手抱肘,时而背着双手,在书房慢慢踱步。脸上的表情非常镇静,丝毫看不出内心情绪有任何变化,甚至连一丝细微的变化都看不出来,而遇到这种场面,内心深处的那类变化是不可能没有的。只不过她处世老练又老道,掩饰内心的手法高明而已。也就是心理素质尖挺。
“佩服你!”我说,“从认识你的第一天起就佩服你,直到现在更加的佩服你!”
她在我身边坐下来,望着我,神情若有所思。
“关于这个,你都知道些什么?”她反问我。
“我知道有人把我家当游乐场,把我的书房当建筑工地,几进几出,搬过来翻过去的。”我说,“这还不够嘛?”
她嘴里咕哝了一句“这群蠢货!”接着站起身来在房中踱步,片刻之后又停下,回头望着我。
“我要那盘编号为0515的原始录像带。”她说,“就为这个才派人来你家的。”
“你想要,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我会毕恭毕敬地给你老人家送去的。何必用这种极端的方法呢。”我说,“近时期以来,你似乎很热衷使用这类方法,快沉迷其中了吧。”
她没有理会我的话。“我要你就给?你什么时候在我面前这么乖过?”她问。
“你没试过,怎么就判定我不给?”我说,“那盘带子对我已无秘密可言。”
“当然,另一些隐密也是这几天才知道的吧?”她笑。
“那盘带子只有秘密而无隐密。”我说,“秘密也许你我都知道了。但隐密我不知,只有你知道。不然干吗一定非要走极端。”
“这不可能。”她说。
“你太过自信了。”我说,“以为把老Q的图像嫁接到其他人身上就可以瞒过我。结果还不是被我识破。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在我面前演的把戏。我就不明白,以你平时的傲气加自负,何时变得肯为他人做嫁衣裳了。这可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精典故事。”
面对我的冷嘲热讽,她一点也不动怒,反而笑意盈盈,满眼秋水。似乎那些凝聚着许多心血的图像嫁接的失败无损她的一发一毫。她到底想干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这点倒让我如坠五里雾中。
“小朋友,”她笑,“犯不上为这个生气。书房一会就给你整理干净。”说着亲自动起手来。
我没吭声,很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着她的一举一动。王妈这时端着咖啡进来,看见她在干活,赶快把咖啡放在茶几上。
“大小姐,怎么能让你干这个。”王妈说着走过去,“还是我来干。”
“王妈,”我说,“你别管她。这活还非她莫属。”
“瞧你这孩子,”王妈拿眼睛瞪我,“人家是客人,很久不来一次的稀客。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我只好收声。拿起杯子斟满咖啡,边喝边看她们两人忙碌。大约30分钟后,书房整理完毕。
“来,喝点咖啡吧。”
我给她斟了一杯,递过去。她接过杯子,在我身边坐下,神态陡然间显得无精打采。她姿势优美地并拢双腿,亮丽而洞穿力极强的目光落在案头摊开的一本书上,她放下咖啡拿起那本书,随手翻了几页,浑如一幅精典话剧的剧照。窗外依然下着雨,那些雾静止不动地悬浮在空中。室内无风。片刻,她放下书籍重新端起咖啡,微微扬起脸看着我,递出一缕流萤似的微笑,色彩浓淡相间,如空气与迷迷细雨擦肩而过时瞬间的一颤。我与她双目对视,那眸子秋水盈盈,让我暗自惊讶的是,那眼睛里以往绵延不绝的傲慢与自负不翼而飞,代之以楚楚动人的妩媚,犹如洁白的晴雾笼罩其中。这晴雾看似飘忽不定,仿佛一阵风吹便会自行消失,但这终究属于视觉和主观意象,实际上那雾一直依稀存在。她的美与活佛和苏凤儿截然不同,仿佛是季节的两个极端。由于职业与经验的打磨,她的美闪烁着炉火纯青的成熟韵味。她卓有成效地将美融化在自我之中,使美成为她自身的自在象征。成为她的自由王国。与她相比,活佛和苏凤儿的美则犹如北方的雪花,漫山遍野地任意飘洒,纯结清雅的浓度以致连她们自己都为之困惑。我每每目睹她漂亮妩媚的异性风采,每每暗自叹息--可惜了这一朵奇葩仙蕊,偏偏开放在世俗的路边,若是生在深山或是多一点清纯之气,对我而言莫不是三生有幸。
“下午我真得差点给车撞倒?”良久我终于开口。
“当时我正好路过。”她放下咖啡杯,抬起头来望着我,“远远看见你像只落汤鸡似的在雨中乱窜,路上车又多,你突然横穿马路,所到之处都是急刹车的声音,大家对着你怒吼,你一点反应也没有。那情形着实吓坏了我。我当即下车抓住了你。”
我默然。继续喝我的咖啡。
“今天你怎么了?”她问,“从没见过你那个样子,就像灵魂不再附体一般。”
“你说得没错。”我背靠沙发,眼望着天花板,“当时灵魂已经出窍,在天地间翱翔。”
她用指尖在茶几上轻轻敲打几下,想了一会儿。依然不解其意,问道:“这,怎么回事?”
“活在虚幻中的现实,”我望了她一眼说,“颤抖的时间,摇摆的意识,扭曲的道德,语言像坚硬的岩石穿过不透明的空气,在远处变脸。我穿越自我,在血肉横飞里劫持灵魂共同寻找存在的不存在里的自在境界。”
她脸上显出惊讶的神色,定定地望着我:“幻像?疑或是扭曲的现实?”
“或许两者都是。”我说,“这些幻像比真实还要确实,因为真实本身是活动和模糊的,而幻像呢,来自孤寂,具有深刻的特征,表现出有力的固定性。”
她又用刚才那种眼神久久凝望我。“别这样。”她说,“凡事还是要朝好处去想。这个世上,爱你的人,喜欢你的人还是多过仇视你的人。你已经明白许多事,还有许多事想必不久你也会明白。人生在世,有些事难以取舍,好坏对错不能简单评判,就像幸福里有贫瘠,痛苦里有丰富一样。归根到底,理解的深度与角度很重要,否则即便是同一件事,也会失之毫里差之万里。”
“你如果能就此收手,也许大家会比较开心。难道这样不好?”我突然改变话题。
“我已经厌倦啦。”她望着我,叹口气。“听天由命吧。怎么表达好呢--有时我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像被外力操纵,其实那是另一个我。只是我一时无法分清而已。所以只好什么都不去理会,任着性子胡来。这世上,任何一件事只要你做了,终归要有回馈的。我现在如一个知错的孩子,双手抱膝蹲在角落里一动不动。我在等那个回馈的到来。”
“那会是什么?”我问。
“结局,”她望着我灿然一笑,“我的。”
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往昔的一幕,如空气在指尖微微一颤,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出现:那个多年未见的靓丽女孩找到我。如今你长大了,我来请你吃饭,她说。那笑容犹如电视啤酒广告里冰块被抛入黄色液体荡起清凉的泡沫一般。
临出门的时候,我突然问她:“你可有跺右脚的习惯?”
她再次平静地望了望我,什么话也没说,开着车走了。
“也许不是她。”望着逐渐远去的车尾灯,我这样想着。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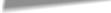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