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稿信 |
约稿信
《新新阅读》杂志隶属深圳市文联《特区文学》,为一本青春活泼,提倡新文学写作新趣味阅读,面对在校生的月刊。稿件要求贴近生活、健康向上、轻松活泼、感情真挚、有故事(此为重点),又不拘泥于故事,也不做说教面孔。本刊特设以下栏目,欢迎各路大虾踊跃投稿,稿件一律要求首发,3000字以内,稿费每千字60—300元,优稿优酬。若有优秀稿件,可直接投递,ylh@szstory.com,多谢支持!
1. 新新制造
此栏目为话题栏目,围绕话题,征集优秀稿件。
2. 那时年轻
回忆性质的文章,用故事形式展开,可回味可追忆可感悟。
3. 手执玫瑰
校园恋爱故事,要求健康惟美。
4. 值得流泪
发自内心深处的事件,要求文笔精炼成熟,切忌无病呻吟。
5. 温柔时光
温情类短文,真善美型的,类似《读者》上的散文。
6. 猫猫狗狗
与宠物有关的故事。
7. 绿绿绿绿
环保类文章,切忌说教型,理论型。
8. 校园啦啦啦
属于自由发挥栏目,要求有趣生动的校园轶事。
9. 八宝粥
类似于校园啦啦啦,区别在于可不是校园故事。
10. 你我不同
关于国外生活经历故事,突出一种与国内生活的对比。
11. 人在天涯
同你我不同,区别在于此栏目属个人感受文章,不突出对比。
12. 有点出格
幽默辛辣型,要求文笔出众,才华四溢,可乱弹,可写人。
13. 时光底片
类似于那时年轻栏目,追忆型散文,通过故事感人悟人,或追思。
另:《特区文学》也需中短篇纯文学小说,10万字以下。
下面贴两个新新阅读的范文:
手执玫瑰
一百斤木炭和一次狭路相逢
(深圳)野麻雀
妈妈说,快去借箩筐!包家有便宜木炭卖,我们去买100斤回来过年。
13岁,是一个可用的劳力了。我很雀跃,木炭来了煤炉子就可以撤走了,从初冬起,屋里就一天到晚弥漫着浓浓的煤气,木炭的气味好闻多了,而每年木炭火一生起就意味着过年;我很气馁,9岁就和妈妈抬粪桶泼菜园,临到13岁,正爱着齐秦的《冬雨》,还要去抬木炭。
我和妈妈走在去包家的路上,我们分得开开的。风吹过来,我看到她的身子缩得很厉害,一点都不凶狠,可是我还是不想靠近,反正靠近也不会温暖。
包家是路尽头一幢白色二层小楼房,有楼房住,真是有钱,还未进门心里就打了个格登。妈妈不,她是小学老师,总认为高人一等,她昂着头进去了。我蹑脚跟进去,妈反过头来瞪了我一眼,我更矮了,为她挣不来面子,我也急。
包家主人与妈相熟,给了一个好价,17块钱100斤,本来是卖18块的。妈说我们两担可以挑完。包家主人宏亮嗓子不知对着哪喊:“必儿——,必儿啊——快来给李老师装炭!”
“喊死啊!——来哒!”
一个小伙子冲进来,14、5岁的样子,骂骂咧咧地冲到堂屋的木炭堆边,春笋一样蓬勃的势头,鼻子眼睛挤在一张窄脸上,仿佛还没来得及长开。挤在一起的还有麻子,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他的外号是“酱油麻子”。那时,我正爱着齐秦,“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这句总惹得我鼻子发酸,心却犹如被什么东西提上去,没有实处可落;那时,我正受着妈妈的欺凌,他冲进来,看也不看我妈一眼就开始铲炭,他不怕我妈妈,我觉得他好厉害;那时,我13岁,正在为许多摸不着的幻想找张摸得着的男性面孔;那时,他的眼睛如火柴一样,“划”地一声,点亮了漫长的黑暗的冰冷的青春。
装满了,我说了一声“谢谢”。对于乡音来说,这声“谢谢”不亚于晴天霹雳;对于乡村来说,这是开天劈地;对于我妈来说,她狐疑了一秒钟后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我听到钉子按在胸口,被锤子砸进去的声音;对于他来说,他直起身,对着我笑了一下,这一笑,堵住了所有来路。嘴不大,两颗门牙暴得很闪烁。
那100斤炭是如何运回去,是担还是抬?我不记得了。堵住了所有来的路。所以不记得了。
狭路相逢,是很不好意思的,因为这其中有我的刻意。
包家那孩子,13岁就辍学在家学开汽车,等15已开得一手好车,总是开着一辆叮叮咣咣的解放车从长江堤坝上去镇里。我家离堤坝不远,但是端着一碗饭跑到堤坝上去吃的话,是很牵强的。跟家人说看长江里的船去,妈妈瞪我,吃个饭还疯那么远。我还是夹了些菜跑了。江是亘古的,日夜盘着村庄,几乎都盘到人们的骨血里去了,看江?疯了。我不知道我端着个饭碗站在堤坝上看江很傻。我站在那儿看,饭快吃完了,要回去了,还没有车来。江水让人烦,一切都让人烦,我的心要沉下去了。
没有饭了,呆太久妈妈的眼神会把我的秘密全揪出来,我想,如果我的秘密被任何人知道了,我就死。我悻悻的回头,下堤。
车来了,一辆绿色的解放车。轰轰地,比心跳还响。它是开过来还是飞过来我不知,等我把眼睛抬起来时,我看到包家的孩子了。显然他也没有预料到我拿着一只空碗一双筷子在江边出现。车停在我身旁,他探出身子说,我觉得他犹疑了一下,我觉得他也是在平复他的心跳,他说:“你在这里搞什么?”
“看江。”
“看江??”
“嗯……”
他笑,不可思议地,惊奇中隐藏了鄙夷地,这一笑,把所有除了死亡的路都给堵住了。
猫猫狗狗
赛班
(深圳)孙冰岩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对赛班的厌恶,说不清什么原因,只是讨厌。
赛班是我们老板养的一条狗,一条不知道是什么血统的外国狗。在我来公司时,它就在了,据说还是老板的父亲做老板时买的。在我的印象里,外国名狗应该或乖巧可爱,或高大威猛,可赛班却和这些,一点儿也挨不上边。
赛班也许是这世上最差的一条进口名狗吧?它的身体很高,却一点也不壮,瘦骨嶙峋的,走路摇摇晃晃,仿佛随时都能倒下。其实它很能吃,一顿吃下的排骨,够我吃一个星期了。公司的食堂并不是总那么慷慨,我也不能保证天天有排骨吃,可赛班却一天两顿,从不间断。这是老板的父亲在公司时,定下的雷打不动的规规矩距。听公司的老人讲,大概是赛班以前救过老板父亲的命吧?可老板的父亲已经去世2年了,具体详情却没人说得清楚。大概又是传说吧?这种狗救主人的故事,我都快读烂了,天知道有几个是真的。
赛班是条母狗,身上披着厚厚的土黄色长毛,总是油腻腻脏兮兮的。好像以前下过崽子,两排斑驳僵硬的乳房,松松垮垮地垂在肚子下面,走起路来,晃荡着像拖在外面的两根大肠,让人感到恶心。
它总是趴在办公室的门前,布满暗黄色眼屎的眼睛,半闭半睁。外来办事的人不知道,总会害怕,其实自从我来公司以后,就不曾听它叫过。它白天不叫,晚上也不叫,即使那天有人翻墙进来偷东西,也不曾听它叫过。我想,它大概是老得叫不动了,快死了吧?
每天早晨,起床后到院子里转,便总会有种想法,就是看看赛班死了没有。可每次看到它,它都还活得好好的。尽管依然那样懒懒地趴在地上,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它今天还死不了。
赛班也好像知道我不是很友好,每当我走近,它总是挣扎着站起来,躲得远远的,眼睛斜视着我,小心戒备的神态表露无遗。越是这样,就越发的感觉它讨厌。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毫无来由的仇视一条狗?其实在所有的动物中,我最喜欢的是狗。也许是赛班和我见过的狗,差距太大的原因吧,我居然盼着它早点死。
它的存在,实在给狗的形象丢脸,也给公司的形象抹黑。在一个早晨,和老板站在办公室门前闲聊,看着趴在台阶下的赛班,我就建议老板,杀了它算了。老板也对赛班没什么感觉,何况它一天还要吃掉几斤的排骨,就皱着眉头说:“好吧,哪天让老吴来看看,勒死吃肉吧。”
老吴是食堂的大师傅,每次老板买狗回来杀了吃,都是老吴动手。我为老板采纳了我的谗言而沾沾自喜,便马上去找老吴,临走前回头看赛班,它也正眯着眼看我。我心说:“你还不知道吧,你就快死了!你这肮脏的家伙,就是真的勒死吃肉,我也决不会动一口。”
老吴来了,围着赛班转了一圈儿,然后对老板说:“现在勒死有些可惜了,赛班带着崽子哩。”
我吃惊地看着老吴:“你不会搞错吧,它都老得快死了,怎么可能会带着崽子呢?”老板也说:“是啊,它好几年都没下过崽子了,你看错了吧?”
老吴摇着头咂着嘴:“不会的,我不会看错,也许这几天就快下了。”
老板饶有兴致地也围着赛班转了一圈,说:“那就等下了崽子再说吧。”
我无奈地看着赛班,它的头转向别处,看也不看我一眼,仿佛在蔑视着我的存在。这可恶的家伙,怀孕怀得可真是时候!
半个月后,赛班真的下崽子了,只有一个,是个胖乎乎的土黄色小家伙儿。公司的人都围着看,老板乐得眼睛直发光,一个劲儿憨憨地傻笑:“真没想到,赛班真下崽子了。这是好兆头,喜事儿,老吴,明天给赛班加半斤牛奶!”
老吴一叠声的地答应着,顺着老板的心意奉承:“这么大年龄的狗,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有下崽子的。你看这小家伙儿,长得多肥实,肯定长大狗!”
老板乐得合不拢嘴,用手摸着下巴说:“给它起个名吧,就叫福来吧。”
我看着赛班,它依然安静地趴在那,眼睛慈爱地望着它的宝宝在吃奶。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忽然发现,其实赛班也并不是很让人讨厌。
“福来”却并没有如它的名字一样,给它带福来。在它二十20多天时,老板在送一个走老客户“老楚”回来后,呆呆地看着“福来”,忽然叹了口气。
我小心地问:“怎么啦?刚才那单生意没谈成?”
老板看着越发长得虎头虎脑的“福来”,摇了摇头,半天才说:“老楚最近喝酒喝得胃疼,也不知谁给了他一个偏方,说是吃刚满月的小狗能治这病,刚才他来看到了……”他不忍再说下去了。
我的心里一阵悲凉,张嘴冲口说:“那给他再买个别的吧?”
老板晃了晃头,说:“他只要这个……唉,等满月,你想着打电话,叫他来取。”说完老板转身回办公室去了。丢下我一个人,看着“福来”无知地拱在赛班的肚子底下,哼唧着吃奶,我的心忽然像被针扎了一下,抽搐着在疼。
我伸出手去,想要抱一抱“福来”,可赛班却警觉地对我裂开大嘴,尖利的牙齿闪着冰冷的光。它居然不再让我抱“福来”了,这是自它产崽后,所从未发生过的。我和老板每天都会抱一抱“福来”,今天,赛班是怎么了?望着赛班狰狞的面孔,我终于放弃了。转身离开时,我在心里哀叹:“可怜的赛班,可怜的福来,这样的结局终究是无法改变的了。为了赚钱,老楚就是要老板的老婆,老板也会答应的,何况只是一条狗……”
第2天一大早,老吴惊慌地闯进我的宿舍,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你快去看看吧,赛班把福来给吃了!”
我的心一震,手里正在刷唰牙的牙刷都拿不住了!怎么可能?赛班疯了么?!
是真的,我赶到院子时,赛班还没吃完,只剩下一条血淋淋的后腿,还叼在它的嘴里。它的眼睛也是血红色的,发出妖冶的光,放肆地望着周围的人,毫不在乎。
老板也闻讯赶来了,他的脸色铁青,只看了一眼,便扭头走开。临转身时却说:“老吴,你把赛班拴起来,明天杀了吧!”语气决然,带着金属的颤音。
我看着赛班旁若无人地踞地大嚼,鲜红的血丝顺着嘴角在向下滴,摔在地上,裂开来,像一朵朵梅花。呵……赛班,你终于要死了,可我现在居然会很伤心!人呐,复杂的人呐,不知你是残酷还是仁慈。
当天晚上,已经快半夜了,老吴又闯进了我的宿舍。他依然像早晨那样惊慌:“赛班跑了!它咬断了绳子……”
我愕然望着他:“赛班还能咬断绳子?不是你故意放的吧?”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居然会这么想。也许,换做是我,我可能会……
老吴的一张脸急得沁泌出汗来:“我怎么会故意放它跑呢?难道我不想干了么?这可让我怎么和老板说呢!”他急得在地上转着圈儿跺脚。
我笑了,拍拍他的肩说:“跑就跑了吧,明天我和老板说,要扣钱,让他扣我的!”
老吴感激地抓住我的手,眼圈儿都红了。“谢谢您,您可千万……”
送走老吴,我心里忽然感到一阵的轻松,沉重了两天的心情蓦然开朗起来。自己给自己冲了杯咖啡,坐在椅子上,呷一口,眯起眼睛。眼前,赛班的身影仿佛正驰骋在黑夜的原野,身姿矫健威武。
忽然一种感觉细若柔丝,在脑海里飘来飘去,竟难以捕捉。
赛班为什么会突然逃走?难道它有什么预感?难道它听得懂我们的说话?那它吃掉“福来”……我的脑子乱极了,在晕眩中,仿佛“福来”那条血淋淋的后腿,仍在不停地在眼前晃动。
一个星期后偶然的一天,我在离公司十几公里的地方,又一次看到了赛班。那是高速公路加油站旁的一个垃圾箱,赛班正埋头在里边寻找着什么。也许它是在找排骨吧?我相信,那里面一定没有。赛班抬起头来,它也看到了我。它只是呆呆地看了我一眼,便漠然地转身走开。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它步履蹒跚地渐渐走远,忽然感觉到眼里,正有什么东西在悄悄滑落,咸咸的,有些苦涩。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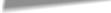 |
|
回帖 |
 |
|
| 回复人: |
竹辉 |
Re:约稿信 |
回复时间: |
2005.04.20 11:00 |
|
欢迎《新新阅读》杂志社来胡杨林约稿。:)
此约稿信我转去传媒征文版区。
|
|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