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走吧 |
我们走吧
(一)
我若告诉身边的同事或者朋友,说我身体的左侧总有一个女人,他们一定会说我有神经病,或者若我一再坚持的话,他们会说我一定是见鬼了。可她不是鬼,她的确是一个女人。她就在我的身边,而且大部分时间她站在我身体的左侧,左侧总是一个人防御能力比较弱的一侧。
从第一次见到她,我就知道她会一直跟着我,一辈子。
那是在那样一间灯光昏暗的屋子里,在我的童年。
那个漆黑的夜里,没有月亮,夜色稠密得让人觉得窒息。我被一个叔叔从老家带回来。叔叔一向不喜欢我,像甩掉一个包袱一样把我放在胡同口就自己回家了。那时我大约5岁或者6岁。我想我的妈妈了,我已经半年没有见到她了,我顺着漆黑的胡同往家里跑,我熟悉这个胡同,这里有我孤单的童年,在这个夜里,她像是被一个魔鬼使了妖术,怎么也跑不到尽头,没有一个人家屋子里的灯是亮着的。
我跑到院子门前,拼命地拍打着那扇破旧的门,拍一下它就会哗啦哗啦地响,我太熟悉这扇门了,青灰色的油漆已经大部分脱落了,露出乌黄的木头的颜色,可是现在它挡着我,我见不到我的妈妈。我一边拍,一边用尽所有的力气喊着妈妈,我听到我的声音那样软弱无力,颤抖着,像一只迷路的小山羊的叫声,我很想哭,可是我忍住了。我那么久没有见到我的妈妈了,现在回家了,我该高兴才对的,不是吗?我怎么能哭呢?
不知过了多久,母亲来开门了,母亲听出我的声音后,慌忙地问着,可子,可子,是你吗?那声音像是一个人由于太激动而没有端稳手里的水杯,水洒在地上的声音。
母亲开了门,迅速地把门关好,拉我进了屋子,然后一把把我抱在怀里,我的脸贴在母亲的耳边,我想我该高兴的,可是眼泪却流了出来,而且没有一点声音,那时我就看到她了,傻傻地憨厚而可爱的样子,站在我和母亲的身旁,她问我,见了妈妈应该高兴的,你为什么要哭呢?而且你哭的时候怎么没有一点声音呢?我说高兴,真的高兴。可是为什么要哭呢?而且哭居然可以不发出任何声音。我全部的思想几乎都在她那充满了迷惑的眼神里,我不认识这个女孩,可是我一定在哪里见过她的,我想。我趴在妈妈的肩上,很长时间不愿意起来,我该全身心地投入到重逢的喜悦中的,可我却在被她吸引着。
她的第一次出现就是在那个晚上,那个时候我决不会想到她最后会成为我的一种疼痛,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也许她是我的记忆。她总是在我猝不及防的时候让我疼痛,那种痛像沙子一样弥满了我存在的空间,我无处可躲,即使我努力地紧闭双眼,或者捂住耳朵,或者天真地想使自己所有对于外界的感觉变得麻木,也无济于事,她有足够的耐心对付我,她说她叫左沙。当然也许她并不是故意做这一切,她的存在就是一种痛,她让我对所有的男人都是一样的感觉,也就是说,如果有两个或更多的男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有人问你哪个更好一些,而你说你哪个都不讨厌,哪个都不讨厌就意味着哪个都不喜欢,她就是这样的,让我对任何男人都爱不起来,一个女人不会爱上一个男人,甚至从来没有爱过一个男人,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
这种疼痛是从一个夏天开始的。
那个夏天我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中等待着背着书包去上学的那一天,我终于够了上学的年龄了。我不睡午觉,每天偷偷地从后门溜出来,钻进屋子后面那些工地上用的大水泥管子里,我和我最好的玩伴冬冬,靠在水泥管子里一起憧憬着走进校园的那种骄傲,日子变得无限甜蜜和美好。
忽然有一天,冬冬兴奋地对我说,她的哥哥为了庆祝她可以上学了,答应让她带我去他的工作室里去参观,她曾无数次地向我炫耀她的哥哥以及他的工作室,眼里总是闪着无数的小星星。她拉着我的手走向那间对于我来说充满了神秘也同样神圣的工作室。穿过一个狭窄而阴暗的走廊,走廊里堆放着一些旧床板,充满了腐木和尘土的气息,两边的门都用金属的锁头锁着,贴着封条。外面的阳光要把人烤化了,而这里却像是被隔离开的一个秋天,我不禁打了个寒噤。走廊的尽头是一个通向地下室的楼梯。她用兴奋异常的声音喊着,哥,哥,我知道那是因为她太激动了,她终于可以向我证明她没有骗我,她不是在说大话,她可以用即将来到我们面前的事实来剿灭我眼里的那些不屑。
地下室的木门吱地一声被拉开了,昏暗的灯光像一个垂死的人的微弱的喘息,在敞开的门里无力地呻吟着,她的哥哥干柴一样地立在门口。
所谓工作室,也不过是一间冲洗胶片用的暗房而已,墙上贴着已经有些发黄了的黑白照片,墙角的两个大盆子里泡着一层一层的相片,屋子里网一样交织的铁丝上也挂着相片,我有些看呆了。冬冬看着我惊奇的眼神得意地说,怎么样?我没有骗你吧?一边讨好地看着她的哥哥。
对我来说,他是个陌生人,虽然我和冬冬一起长大,可是他却是刚来的,他的脸并不像他的身体一样单薄干枯,甚至那双眼睛像一条狡猾的鱼一样饱满灵活,唇角溢出了浅浅的笑,像一只没有关掉的水龙头,无论你怎么去捂住它,还是会有水从指缝里溢出来,他为什么不干脆笑出来,干脆让水流出来或者关掉它?
他关掉它了。突然变得很严肃甚至有些烦躁地对冬冬说,哥渴了,你去给哥买瓶汽水,也给你和可子买两根冰棍儿。说着把两张皱巴巴的五毛的票子塞到她手里。我认为我应该跟她一块儿去,她也正这么看着我。可是她的哥哥却说,你去吧,可子第一次来,让她呆着吧。她眼里闪过一丝的失望,转而却更感激地看了一眼哥哥,一溜烟地钻了出去。
坐吧,他指了指那张看起来很苍老的床,我战战兢兢地坐下了,床发了出一声难听而沉重的叹息。他停下了手里的活,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在干活,盯着我看,他的眼神如一根绳索一样地将我捆住,我一下也不能动,他顺着那绳索来到我的身边,俯下身子在我的耳边说,可子,都长这么大了,喜欢这些相片吗?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像一个巨浪摇荡着一只小船,小船还没有平静,另一个更猛烈的巨浪又打了过来,他以我几乎不能看清的速度从床单底下抽出几张相片来,并紧贴着我坐下来,用一只胳膊紧紧地环着我的肩膀,另一只手把相片挡在我的眼前,那一瞬间我只看见一团花白的肉和一个男人的生殖器,像一条邪恶的虫子一样趴在这小纸片上。
好看吗?在我来不及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轻得像羽毛一样的声音在我的耳边轻轻飘起。
我努力地想挣脱他,骂他流氓,不要脸,可是她制止了我,左沙就是在这时出现的,她的出现使我陷入短暂地呆滞的状态,在这种状态里,我清楚地看到她不知羞耻地盯着那些照片看,好奇而兴奋地睁大了她的眼睛。
左沙对相片上男人的生殖器的好奇和二十年后的一个下午是不同的,在一个被白领丽人点缀得像皇帝的后宫的写字楼里,大约是第六十一层的洗手间里,洗手间的门上写着WOMAN,在刷得如同奶油一样鲜白的墙壁上也用铅笔画着一个男人的生殖器,左沙看到后不屑地在上面啐了一口,在电梯里,左沙总是盯着每一个靓丽的女人问我,你看她是那杰作的作者吗?
左沙看完那些相片后,用可耻地羞涩的眼神盯着冬冬的哥哥。他看起来的确是个英俊的小伙子,她想那相片上也许就是他自己,在这样一间如同老鼠洞一样的暗房里,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我看到她几乎要伸手去摸那些相片,我惊叫着,不!我吓了他一跳,把她也吓得退到一边了。他说,可子,没什么,别对别人说,也别对冬冬说。你喜欢这里吗?以后常来,好吗?我居然点了点头,不,不是我,是她,是左沙。
走廊里传来冬冬的脚步声,很轻,却足以使左沙乖乖地站回到我身体的左侧。
他蹲在那些盆子前,一张一张地把那些相片从水里捞出来。刚才发生的事,似乎只是我的一场幻觉。冬冬的脸被太阳晒过后,更红了,看起来她的得意劲儿一点也没减。冰棍儿已经在不停地滴水了。
他冷冰冰地说,去吧,你们出去吧。
我和冬冬一前一后往门外走去。我几乎不敢多看他一眼,可是左沙却冲他眨着眼睛。
冬冬喋喋不休地唠叨着她哥哥的好,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听进去,我只听到左沙一声小小的幸福的叹息。我瞪着她,恨不得把她踢到山那边去,那时候山那边对我而言就如另一个世界一样遥不可及,可是我知道我只能和她在一个世界共存,她已经像我身体里一个多余的长相怪异的器官,我的一种病。
她无时无刻不站在我身体左侧,像回味着一块好吃的牛奶糖一样回味着那个中午,并对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她惶惑不安的兴奋的感觉,可是她为什么会兴奋,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那个夏天,可以去上学的喜悦的心情,被她赶得无影无踪了。我所有的时间只是用来摆脱她的纠缠和关于那个下午的回忆。我很少和冬冬在一起了。冬冬为此在别的小孩面前说尽了我的坏话,并在一次无意的相遇中丢下一句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开始不与任何人玩耍了。
在这种更加孤独的日子里,她总是拉着我在那个长长的走廊外徘徊,我任由她摆布着。终于有一天,他看见我了,先是一愣,然后就在唇角挂上了那种溢出来的笑。他叫着,可子,来,我带你进去。我几乎要拔腿就跑,可是左沙制止了我,推着我,跟在他的身后。
我又坐在那张床上时,他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一只手解开了自己的腰带。多年后,我和左沙一起回忆起他的这个动作时,都想到了性感这个词,我们一致认为男人的这个动作的确是性感的。我全身颤抖着,看着他在我的面前把玩着他的生殖器,像是在一个急速下降的电梯里,我感到晕眩,甚至开始恶心。可是左沙却伸出了她的小手,她听不到我绝望的呼喊,和他一起在那肮脏的快乐中陶醉着。这下流的一幕如同一块肮脏破旧的抹布,抹去了我所有在那些成长岁月里该有的色彩。我生活在灰色的世界里,深灰,浅灰,灰白 一切都是灰色的。而且我开始不停地做一种梦:
而左沙在那一瞬间战胜了我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和我一起生活在灰色里。那一瞬间带给我的疼痛和恐慌化成的力量使她不能再轻易地左右我。她羡慕漂亮的女生,羡慕他们生活的那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她甚至偷偷地喜欢上了一个很有几分帅气的男生。那男生瘦瘦高高的个子,明亮的大眼睛里总是含着浅浅的笑意。她一遍遍地恳求我去和那个男生说几句话,或者放学偷偷地跟在男生身后,她可以远远地看着他。我不会那么做,我对所有的男生都无法不做出冷漠甚至仇恨的样子,我在抱负她,我把别的男生写给我的纸条一眼也不看就扔掉。我们为此无休止的吵架,在课堂上,在路上,在夜里。我们互相憎恨却无法摆脱彼此。
有时,我想我是可以抱负她的,比如我残疾,我不得不在轮椅上或是床上度过我的后半生,那么她还有什么办法呢?她还能肆意地安排或是捉弄我吗?她面对这样一个人大概只会有同情了吧,我对于她还那样重要吗?也或者还有更直接的办法,就是死亡,这个办法像我偷偷藏起来的一个漂亮的钮扣,不只一次地让我感动。
现在我想我是为左沙才写这些文字的。也只有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那痛虽然离我更近了,却不再那么锋锐难挡,那痛顺着我的指尖流泄在文字里,我把我们揉碎了做成了这些文字,我们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过瘾的快感。我相信还有别人的旁边也站着像左沙这样的人,只是他们没有发现,站在旁边的人也没有像左沙这样张狂,可是我不关心别人,我只关心自己,也只能关心自己。
我的成绩当然不会好,老师想把我当一个破板凳一样扔出去。我没有被扔出去,我主动辍学了。在这期间我的一个女同学怀孕了,比我更早地离开了校园。她是那样的娇小美丽,可是她的一天天隆起的小腹使她看起来苍老而笨重。我看到她下楼的时候,小心地扶着栏杆,左沙对我说她真可怜。他们都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可是我和左沙知道。他们在校园后面的那片小树林里幽会时,我和左沙就在那里,他们没有看到我们。我不会说出这个秘密。
(未完待续)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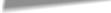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