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杀手独白 |
杀手独白
晚上十一点四十七分,像往常一样,我横坐在四楼窗口的窗台上,侧目俯视着下面的那条路,一条南高北低的路,其实应该说是一条坡。而这条坡上就是这个地方最高的山,我就住在这里。
这个城市的在我出生时天气就永远不会放晴,不,其实在我出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放晴过。现在是十一点四十八分,我已二十七岁零五十四天。
就这么坐着,看着下面发生的一切,从我的眼前闪过,没有漏掉的。早在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就不再抬头仰望天空看或数星星,因为出来星星的位置我都很清楚,就像清楚自己身上有几颗痣,在什么地方一样。就是前面我说过的,这个城市的天空永远再都不会放晴,晚上也是如此。
在这个城市,我从未见过书中或别的什么地方所描述的银河,我所见到的就只是那几个永远都出现在夜空之中的,随着季节才会变换位置,但永远不会改变彼此之间的距离的星。所以,从十七岁起就不再抬头仰望,因为我心里是知道什么样的。
路上来去的人们已经不多了,但可以准确的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是要去干什么。上班的,下了班的,打佯的,无家可归的,酒醉后找不到家的,或醉着还去找醉的......
当然,天是彻底的黑了,但靠着晚上皎洁月光和昏黄路灯以及未关门店铺的灯光,还有我那两个都是5.2的眼睛,这些都是可以让我很清楚的看到下面所发生的一切。
对面的小巷里有一团红飘了过来,缓缓的,用一种慵倦懒散的步调前行着,让人感觉到暧昧。夜晚的红总是不那么的自然,是极力在掩饰自己心里的虚弱,生怕被外界察觉什么,红色,则是遮盖这种情绪的最好装饰色。
那团红出来了,是飘了出来。一个女人,确切的说是一个身穿红色大衣的女人。而这个时候在外走动的女人大多都是去谋生的,是在夜晚里作着满足人类最初原始级最为强烈欲望的的职业。还有她穿着看感觉露出大半且快要蹦出胸部的紧身短衣,还有短的不能再短的小皮裙,这些特征都不可否定的决定着这团红的职业。
十一点五十二分,不知为什么,不由自主的抬头,我一向都不喜欢仰望,认为仰望是隐藏在内心底处很深很深地方,一个声音悲楚向上天祈求的行为,而且是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的一种希望,这种行为只能是空望神分,没有一点的回应。
但在这一刻,我抬头仰望了,处于莫名的动作或奇怪的心理暗示,但我不认为这是什么预示和预感,因为我很平静。
阴历十六,被我现在抬头仰望所见的月亮因为这个时间而处于最大状态,也最圆,也就最为不一般的倾泄着自己从别处折要来得很一般得淡的不是自身所散射的光。
十一点五十四分,阴历十六,月亮最大最圆最光亮的晚上,也是我抬头仰望之时,那团红,不,那个女人,在我的预警感觉之前,在走出巷口的那三秒钟,从背后抽出一支带瞄准镜的点射长枪,口径17毫米的子弹通过扳机抠动后,被撞针顶住弹底,由火药的力量推射,经过厚厚的枪镗,自四十七度的角度从枪口处打出,穿过普通0.4的家庭用玻璃,从我左眉上方偏右处钻进,带着我红色的鲜血与白色脑浆由后脑出来,以每秒四千米的速度钉在我头后的墙壁里。
我还是在仰望着,之所以能够知道的这么清楚,就因为我是一个杀手,一个非常优秀的杀手。而且我这个优秀的杀手即将死去。
我仰望着的头慢慢的靠在了墙上,靠在那口径为17毫米的弹头上。在濒临死亡之前的这段时间我还是清楚着的,虽然血液从弹孔伤处流出,以缓和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接近于慢板的速度流淌着,经过我的左眉,左眼,顺着鼻梁左翼,从左嘴角拐弯,由下巴滴流着,浸湿我的衣服裤子,以零距离紧裹着我的皮肤,然后聚集在窗台上,形成一滩红,但不同与先前的那一团红。
这一滩红是有象征的,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与我共同生存了二十七岁零五十四天,不可缺的一滩红。当这滩红越积越多时,它就会重新寻找再次聚集的地方。于是,这滩红顺着窗台,开始一个一个,一滴滴的向下跳,如同一个个小小的红色精灵;不一会,这些个红色的精灵多了起来,蜂拥着,开始奔跑,形成了一股红流,向下汇合。
虽然以后这些红色精灵会逐渐慢慢的,一步步的变成黑红色,再然后会干裂掉,而最后会被扫除消失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但在这时,在现在,它还是一滩聚集在一起的红色精灵,是象征我生命一部分的一滩红色精灵。
而将我与这滩聚集在一起红色精灵分离的就是那团红,这团红是谁?不知道,但我知道它也是个杀手,也是受雇于人,也是完成一项任务的。所以我的心里现在是释然的,因为我知道我即将死去,知道我是怎么死去的,是为了什么。现在那团红是什么已经变的不重要了,因为在这个世上很多人在死以后都不明白,不清楚自己是怎样死的,是怎么死的,是为了什么而死的。
记起了一本书里,主人公度边对所爱女人直子死时说的话: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死,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
而我说:
“无生亦无死。”
更简单,更直白。
十一点五十七分,我中弹后的第三分钟,不,我不能再相关于生和死的问题了,讨论下去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是在浪费我所剩不多的时间。那么,想什么呢?我已经开始不可以动了,身体已经僵住,只有思绪还可以流淌。这时,我也就只能回忆了,别无作他选择。因为结果马上就会到,而我也很清楚,所以去幻想以后,去想象明天是不实际,也不对的。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忆,也只有回忆可供我选择。
回忆,回忆什么?小时侯,上学时?父亲母亲?少年时?可当我只剩回忆可想时,我竟然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快,我对自己说快,快回忆,快记起自己的过去。从什么时候开始?那就从记事起。
想起记事,我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忘了。那第二件呢?不知道。当然,第三第四也就都不会记得了。那有没有记得很深的事呢?有,当然有,可那件事是最重要的呢?是这件,还是那件?分不出,好象每一件事都很重要,没有差别的。
我的身子慢慢的冷了下来,血也流出了很多,覆盖在先前的那一滩汇集的红色精灵上,底下的不断干涸,龟裂,上面又不断的出现,重复着之前所发生的。
十一点五十八分,我拼命回想,可好象什么也没记起来,又好象又许多的过往在我眼前闪现过,很多很多。
没有一切的一切,只有永远的永远,选择什么,作了什么,经过的,遇到的,碰见的,没有相会的,所有的,在我的时间里,在我的心里,明楚着。
一个漆黑的空间,什么也没有,空无一物,只有我在的感觉里漂浮着,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知。没有疯狂,没有恐惧,在黑暗里我漂浮着。
一切都以结束,什么都完了。
十一点五十九分,我死了。在这个世上我活了二十七岁零五十四天。
回忆之前,忘记之后,都结束了。
继续在的还都在,而走掉的,也就都走了。
就这么了
LY
http://wooway.51.net/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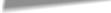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