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雨褛 |
《FAMOUS BLUE RAINCOAT》,按照我这种鸟语水平将其翻译为《经典的蓝色雨衣》,而懂行的朋友说,应该翻译为《蓝雨褛》。这样的叫法,我喜欢。
第一次听GENNIFER WAMES的《FAMOUS BLUE RAINCOAT》,是在朋友的家里。除了厚重的吸音窗帘以外不带任何曲线的家,在一个充满了松香和我们青春的脚丫味道的房间里。为了表达我们的情真意切,我们甚至装腔作势的关了灯,至始至终的保持着和GENNIFER WAMES等边三角形的关系。我得承认,不管怎么的做作,一群才从学校里毕业、还在努力嘶吼着的人,是不可能用摇滚的耳朵去凝听GENNIFER WAMES的。一个30几岁的女人和一群为赋新诗强说愁的人是没什么共通语言的,就象我们想望成熟的女性,而不得其法一样。
曲子从萨克思荡气回肠的一弯弯肠子开始,厚重的倍司让人心旷神怡。
GENNIFER WAMES成熟性感的声音被B&W801音箱演绎得淋漓尽致,一如黑暗里阴红的胆机。可能是受了CD里前两首歌曲的影响,加上半懂不懂的鸟语。恍然中感觉只是一位在曼哈顿临海的摩天大楼里独自凭窗的女人,一面摩挲着手指间的结婚戒指,一面心有旁怠的回忆往日的恋情,其间颇带顾影自怜的哀怨。令我们激动的不是歌曲的本身,更多的在意诸如GENNIFER WAMES口水溅到电容麦克风上的声音或者是几乎不太可能分辨的喉音,分辨重于感受。为了斤斤计较我们失去了更多领悟的可能性。但是,的确很发烧。
这个幸福的拥有B&W和GENNIFER WAMES是我大学里的室友,一起读书,一起玩游戏,一起赌博,一起泡妹妹和被妹妹泡。他是广西人,鼻子长得特别壮族,很帅。走路非常个性,脚下象安了弹簧,一蹦一跳的,象是拼命想浮出水面的鱼。读书的时候一手好吉他,每天都在寝室里弹棉花。喜欢动手动脚,小到手表,收音机,大到彩电,计算机,只有他装不上的,没有他拆不了的。他经常写点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口血的东西,却偏偏说自己喜欢余光中,发情的时候就大呼小叫“我不是长江水,我是雪山的一滴相思泪”。
很喜欢和他走在一起,他的个头和我相近。看起来象我弟弟,事实上他比我小一岁,象个孩子。家里人汇款一到,就是我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时候。兴高采烈之余,我们会出去不停打游戏机,从街头一直打到街尾,一个游戏币打到老板生气。一起去看通宵录象,一起企盼深夜的时候加演大黄。一起去学校舞厅门口看姑娘,虽然我们没一次得手,那时我们腼腆非常。月底挨饿是肯定,一起躺在床上呻吟,可惜一点没高潮。一起唆使对方去借钱。一起守着寝室空荡荡。
进厂了,他发了,想搞艺术的却搞成了技术。HI-FI 不玩了,酒不喝了,人不见了,据说也开始谈朋友了,(大教堂,大独奏)不弹了,全改民谣了。单位的一个小姑娘喜欢死他了,眼睛大大的,个子佼佼的。却被他放逐了。他说他喜欢高挑的,喜欢明艳的了。女孩受伤了,他也外调了。出去搞销售了。两年以后我们又喝酒了,二锅头换成头曲了。紧身的衣服他不爱穿了,脖子上卧一狐狸了。他说他很寂寞,还象读书的时候那样。吉他没有带去,电脑也没有带去,经常守在电话旁哭泣。他说兜里钱是多了,但是挨饿的时候更多了。姐姐去看他,还得去菜市买菜做给他吃,他说他不适合做销售,但是领导很赏识他,他说他想回家,领导说回家你就去待岗吧。他说现在他是经理了,副的。可以管几个业务员和上千万的生意了。他说点上配了面包车了,他差点就学会了。他说他看清销售的门道了,他说把肝和肾都献给了我们的党了……最后他握住了我的手了。
过了段时间,噩耗传来了,他死了,据说他开着面包车跟踪前面一辆比较可疑的大货车,路太拥挤,灯太昏暗,他太想看究竟。凑过去看清楚了原来那货车车尾写着“注意保持车距”。领导也去了,家长也去了,哭得昏天黑地。领导说;该同志是有原则的,牺牲的时候脚也踩着刹车的。眼睛是睁得大大的,就是包里是没有驾驶证的,就是嘴里还有点酒气的,可惜。面包车就不用赔了,借点上的几千块钱是公家的,还是要还的。家长是心痛的,看到我会想起他的,现在对我是不理睬的,态度是变态的,我知道他们是难过的。遗体我是没敢去看的,据说分两段了的。他的未亡人我是见过的,是个业余模特,明艳而高挑的,一身的黑衣。哭没有哭我没看出来,神情是庄严的。那个大眼睛的女孩也去了,手里拿着百合,泪光是闪闪的。
有人说:只有当人经历了死亡,才会变得成熟。但是,这个人没说,朋友的死亡算不算?于是我为我一脸的沧桑找到了发育的旁证。
另一位朋友读书刚毕业就分在银行上班,一个小小的储蓄所里他是唯一的男丁,花团锦簇的他经常向我们炫耀。在我们的圈子里他是一个诗人,其实是他自己喜欢那样评价自己。在外出的汽车里他能写出“车轮呀,让我们欢快的转动起来吧!”愤怒的时候他说:“我向天空吐了一口痰,那是我的愤怒……”当然现在想来那样的词句我憋厕所里一天能搞出无数。
他经常带一个和他脸盘一样大的黑边眼镜,所谓是晋卫分明,高度的近视。很怀疑从那样的眼镜里看出的东西能基本还原到本质,不过我喜欢他叫我帅哥,这时候他的眼睛绝对是雪亮的,我承认。知道他生病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几年没见了,只听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准备结婚,只听说他不再写那些诗歌了,只听说他穿的衣服越来越工整了,不再以穿原件(从买来到穿坏一直不洗在摇滚里叫原件)为荣。只听说他的房子也快分下来了……
再次见他,他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上插满大小的管子,流淌着不属于他的东西,房子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人的味道,床头上摆放着橙黄的橘子,红润的苹果,大小的伪劣的滋补药品,象是祭奠的道具。看见我们去,他还是很高兴的。努力的在床上想摇滚着欢迎我们。可能他满怀诗意,可惜发不出声来。脸象纸一样的蜡黄,这倒是符合他的本性。眼镜没了,看起来一点不象他了。
身边一个女人不断的用哀怨的目光一次一次的把他熨烫得展平。肝腹水,我们谁也不敢去接触他,怕传染。他用目光让我们吃他的水果,他用目光指使女人为我们倒水。他想告诉我们,他还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没有距离。我们手里拿着水果和茶杯(出去的时候就扔了,手洗得快蜕皮)。我们惺惺作态的表示关心,我们不断的鼓励他,我们嬉笑着说以后我们一起出去飘,我们高谈阔论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谁也不敢提曾经。走的时候没有流泪,虽然我们知道那可能是最后一次。
好久以后,个把月了吧。深夜里一个电话说他去了。我想我是镇静的,只是身上都起满了鸡皮疙瘩。(感动的时候我多半如此)。四川有个传说叫“回煞”,说人死以后的一个小时里,他去过的,接触过的东西,他都会再留恋一次。我的心不由自主的收缩了一下,一夜无眠。
再次的聚会已经是参加他的追悼会了,灵堂里挤满了,朋友,同事,亲戚。黑色的大照片挂在堂上,除了他一个人在那里傻笑,我们都在难过。这可能是人类减肥的一个奇迹,一百多斤的人,到几两重只花了十几分钟。我们站在一起,恭鞠得比谁都深沉,脸拉得比谁都烂。下葬的时候,山冈上风非常大,墓穴很小。斩了鸡头,倒了白酒,点上香蜡,一切就绪。埋了,合和一把黄土,世界上没有人再能想起他,除了每年的清明,开始的两年,我们还是去的,买了他最喜欢的白酒,香烟插在橘子上,站在墓碑前和他说话。我们不再谈现在和未来,我们只谈曾经……
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的蹉跎着,想起也纯属不是故意。歌曲就象是记忆里的书签,当音乐想的时候总能想起点什么,不管你愿不愿意.
多年后的一天,朋友送给我一盘CD,随手放进机器里,一面喝着茶,一面是事而非的听着。竟然是《FAMOUS BLUE RAINCOAT》。但歌者已不是GENNIFER WAMES。而是LEONARD COHEN。从一阵尼龙弦轻柔的紧张开始,第一声就道尽了苍凉。吉他颗粒般的叙述和背静下渺曼的女声游吟相纠合消融了LEONARD COHEN追溯的目的,一个已被狼狈不堪的生活折磨得变形的人。这个狂放不羁的二流子在12月末凌晨4点纽约的克林顿大街上的一家小酒店里半梦半醒。低沉略带沙哑的演绎着什么叫颓废。
依稀浮现第一次听《FAMOUS BLUE RAINCOAT》的感觉,想起那群一起听歌的伙伴。但有一些人,一些事情,即便是想起也无力触及。就象手握燃烧的香烟正向酒杯里呵气的LEONARD COHEN。所有的美好和不幸,都只能被一仰而尽,都只能用一种沉稳沙哑的叙述娓娓道来,只是有时候感觉不知道自己是那个曾经想在沙漠里建立小屋的人,还是,凌晨4点还在酒巴里烂醉的人,不知道那种痛更痛?虽然这还是那张经典的《蓝雨褛》。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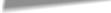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