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与子 |
江国家这段时间看谁都不顺眼,别人和他开句玩笑,他都大光其火,恨不能将人家生吞活剥了。等冷静下来,他又对自己刚才的失态悔恨的咬牙切齿。这管别人什么事呢!他骂着自己,手上还毫不留情的连扇自己几个耳光。他希望自己能深刻地吸取教训。可是等下次又遇到类似的事情时,他又鬼使神差的重蹈覆辙,眼睛喷火似的骂得人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肚子里的气放完了,可恨的理智就紧跟其上的敲响它的钟声,搅扰得他一刻不得安宁。
只有他知道,这怪不得别人,全是他老爸捣得乱。
可是这有什么办法,谁让他摊上这样一个情理不通的老爸呢?天下的事情可以什么都不认,惟有这父母兄弟不能不认。
江国家觉得自己真够委屈的,有理无处说,还弄的别人尽埋怨他。他有时仰头看着天,久久地,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老天,你的眼睛长在哪里了?你为什么不眷顾我一点呢?
不是我为我的主人公说好话,他其实蛮好的。平时脾气很温和,说话前舌头总在嘴里嚼半天,感觉——这“感觉”不是我吹牛,他从小到大没间断过练习,准确率在99%——进了别人耳朵只会产生春天般温暖时,才会细声细语的吐出来。皮肤白皙,清癯高瘦,举止温文尔雅,要是生在古代,标准的白面书生,不知要迷死多少怀春的少女。无奈他偏偏生不逢时,现今的漂亮女孩的审美观念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络腮胡,鹰嘴鼻,身材魁伟,说话如敲锣,身上的肌肉丰厚结实,外加猪八戒的有色心无色胆的甜言蜜语。以上几点他恐怕一点也达不到。不过我这样想,多少有些杞人忧天。傻人有傻福么,到了结婚的年龄,江国家也没在自家的小院当起吃素不吃荤的和尚。媳妇长得娇小玲珑,和江国家有一拼的就是她那张不管走到哪里都不饶人的利嘴。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就有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威慑力,心先自怯了,语调便不免含出几分巴结和客气,距离产生生疏感,产生美,运用到江国家媳妇身上就形成了一种可望而不可既的姿态。亲不亲,远不远,有的人天生就懂得如何站在与人共处的黄金分割点上。他媳妇巧珍毫不客气的属于这一类。
在江国家与他父亲的矛盾上,巧珍完全不放在心上。夫妻都没有隔夜仇,何况父子呢!巧珍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她把问题想简单了。
江国家家是很普通的农村家庭,没有复杂的背景。生活平淡的就象地里种的庄稼,春种夏耕秋收冬藏,一切皆有规律。那他们父子俩的矛盾在哪里呢?这真是一言难尽。
他们父子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敌意的,这连江国家都说不清楚,真是千头万绪。好在我是个局外人,又喜欢说东道西,论人长短是我生平快事。对于他们父子的是非功过,我这俗人也有孔子的毛病,时不时就把他老人家的春秋笔法拿将出来点评一番,至于批评得对错与公正,就只好教给读者中的明眼人来评判了。
小时侯的江国家可活泼了,简直和现在判若两人。跟个猴子似的,整天闲不住,他一般不在家里玩,也不带伙伴去他家,我们也不愿意去。凭着孩子们单纯敏感的直觉,我们都闻到他家的空气不对劲,透着一股子压抑的死气,教人害怕。每家的空气都是不一样的,和睦幸福的家庭的空气是薄荷味,清凉而又迷人,但是在孩子们眼中,家中的空气是五颜六色的,他们把不喜欢的东西都说成黑色。
江国家父亲江海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平庸,不管他说出怎样奇特的理论,人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江海却不这么想,他有一种不知从哪儿得来的信念:我永远是对的。即使在客套的时候,那敷衍的言语背后潜藏的虚伪就会乘机冲入他人的视线。可见他并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却自以为天赋神力不可一世。他悲叹命运,怜悯世人,却不知自己才是可怜的人。如果一百个人在一起照相,你就是拿上放大镜看上七八遍,也未必会发现江海的踪影。你喊他的名字,第一声他肯定不会答应,除非在确信的确是在叫他时,他才会勉勉强强的答应。原来他站在最后一排,个子比谁都低,梨子形的小脸淹没在一片硕大的脑袋的海洋里。神情严肃高傲,一双不大的眼睛眯成细缝,象是在看什么,又象是什么也不看,迷离恍惚的眼神一如刚出校门走进社会的大学生,滑稽中夹杂着呆板。
江国家以为父亲最大的毛病是无法认清自己。这如果是个人毛病到无所谓,问题是每个人都生活在纷纷攘攘的世界,肯定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身上的这个作祟的毛病就会由此引发许多利益上的冲突。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的发明者简直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这句话用到他们父子上也恰当不过。
每个孩子都崇拜过自己的父亲,江国家也是一样。他至今还能依稀记得,在一次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父亲将他紧紧裹在怀里的感觉,温暖,舒适,宁静,体内流淌的血液被这催不及防的幸福点亮。他不说一句话,搂着父亲的脖子,一股汗味象发潮似的从父亲脖颈冲出来,他嗅着,甜蜜的嗅着,他希望到家的时候,自己身上也能有父亲的这股味道。这种亲密的感情对于他们父子已经久违了。后来每想到这些,江国家就失落。如果父亲是个没有人情味的人就好了,我可以毫不愧疚的怨恨他,可是......父亲的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好象把江国家悬浮在痛苦的状态中,既没有落到地面上的踏实感,也没有升到空中的沉醉感。
这是一间奇特的房子,好象是上帝的故意安排,在中间位置不偏不倚插进一堵卡片似的墙壁,留着一个小小的门,仅够一个人通过。朝北屋子的架子上堆着一些草药,一张破旧的长沙发懒懒的靠在门边,还有一张床,对着门口,床单上总有一层抹不干净的灰尘。床上有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在打闹,他们玩的好开心,尽管沙发上坐着三个他们并不熟悉的大人,可这更激发了他们的兴致。他们也许感觉自己象电视上表演节目的小演员,肆无忌惮的笑声感染了身边的大人,使他们也不由得发出会心的微笑。孩子们在争夺一块糖,与其说是在争夺,倒不如说他们在玩糖。他们并不想吃,因为他们获得了比糖更多的快乐。小房南面坐着两个人。江海坐在一把木制靠椅上,正在一本正经的为一位大约五十多岁的男人号脉。手里夹着一支烟,有时问病人几句话。
江国家和弟弟国园玩得忘乎所以,从床上打闹到地下,从那间屋又滚到这间屋。嘻嘻哈哈的声音占领了屋子狭小的空间。快乐的童心为他们围起了属于自己的世界。
“别闹了!”江海说话象刀劈豆腐似的简洁。
可是不知是他的声音低,还是孩子没听见,总之两个孩子没按他的吩咐行事。
江海气冲冲地扔下笔,跳起来,一脚踢到离他最近的孩子身上,“找死!”
一股钻心裂肺的疼痛刺得江国家哇得哭起来,还没等他换过第二口气,江海的下一脚又踢上了,这次是连踢三下,一下比一下重,江国家哭不出来了。他怎么也吸不住第二口气,嘴巴张得老大,死鱼的悸痛神情恐怖得呈现在他那张充满疑惑的嫩脸上。一阵可怕的狂风从他的脑际刮过,好象要拽走他的灵魂。那刻,他变成了一只蝴蝶风筝,父亲的三脚变成了锋利无比的利刃,每刀都割在他稚弱的生命线上。
江海不明白,孩子会为这件事记恨他一辈子。也许他想,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可是他没想过,那时候的江国家只有六岁,瘦弱的身体怎能承受住一个成人在失去理智情况下所踢出的四脚。他更没想到的事,为了这欠考虑的四脚,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失去了一个孩子对父亲所应赋予的爱,江国家体内的生长细胞从此分裂出一种冷漠的器官,他本能的将自己幼小的心潜藏起来,快乐的花只在孤独的心灵里绽放,本该无忧无虑的脸上添上了一层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冰霜,还有那双六岁的清澈的眼睛,忽然蒙上让人看不懂的烟雾,他到底在遮掩什么呢?
当一颗“恨”的种子落进土里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它就开始成长。每种事物的发展都需要诸多因素的全力配合,稍有不慎,就有夭折的可能。“恨”的成长与别种不同,它不需要阳光,水分,养料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一片阴影,一块压抑紧张的空气就可以使它繁殖成密不透风的森林。试想,在这样的环境里,生长的植物会是怎样的苍白。
在江国家成长的过程中,江海似乎不是没有付出过代价。但是他头脑中从来没有过清晰的该将孩子塑造成怎样的人的形象。他教育的方针纯粹是凭自己的心情而定,尤其是在他情绪糟糕的时候,这时候的江国家要是碰上他,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江国家记得在他五年级的寒假期间,一次就碰上了这样倒霉的事。当时学校老师让他们学着写日记,这个爱好语文的孩子,每天晚上躲在西厦屋里,就着一盏昏黄的油灯,写呀写,他有那么多的话想要倾诉,怎么也说不完,怎么也写不完。他好象一下子找到了自己,不再彷徨,不再忧虑,不再提心吊胆。那颗喘不过气的心陡然松活了。因此对于那天的事他还是记忆犹新,想忘记也忘记不了。
西斜的日头快要落坡了,家家户户做饭的炊烟,穿过窄窄的窗户,弥漫了弯曲的街道。一种温暖的疲乏笼罩住这个淳朴的乡村。江国家独自一人从姥姥家往回走。
刚进家门,一瞧父亲的脸色,江国家就闻到了硝烟的味道,他刚才一路上还在回味姥姥家享受的快活眨眼间消失的荡然无存。他缩着脖子,象一只迅疾而无声的蚂蚁向最近的茅房走去。
“站住!”父亲一声令下,
江国家不得不停住了。转过身,惊惧的望着父亲,随即垂下头,再也没有抬起来。手颤颤地捏弄着衣角,小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你给我进来!我有话给你说。”江海说完,气冲斗牛的走进堂屋。
江国家迈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趔趄,跟着父亲也进了堂屋。
江海端坐在沙发上,紧抿着干瘦的嘴,僵硬的面部肌肉好象凝结着一层水泥,好象不这样便不能产生教训人的效果。面前的茶几上放着江国家的那本日记。一瞧见日记本,江国家就知道坏事了。
“这是你写的吧?”江海的语气出奇的淡然,可是江国家分明已感受到父亲咄咄逼人的质问向他袭来。
江国家没说话,一味的默然,他知道自己不管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何不干脆闭紧嘴巴省份力气呢。
果然,江海暴跳如雷了。“你看看你写的都是什么东西!”他指着日记本上的一行字大声念道:“‘我不喜欢我的父亲,他让我紧张和害怕。’我到是要问问你,我是怎么让你害怕紧张了?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读书上学,难道就是让你反过来骂我么?真是不孝子!......”
尽管江国家一句话不说,可是他的心里在一刻不停地同父亲辩驳。“有本事你就别供我吃穿上学了,我才不稀罕!我有手,要饭我也饿不死。这个家有什么好,我早不想呆了。你把我一脚踹出去得了,我还不怨你。”等听到父亲骂他是不孝子时,他险些哼出声来。“不孝子!?多大的帽子,我看你才是不孝子!爷爷奶奶病了,你就是抓上两副药送过去,一分钟也不想多呆。回到家,有时还骂他们是‘老不死的’,真不嫌羞!你口口声声的教导我做人,可是你做人又做成啥样了?......。”
江海骂可一通,嗓子有点渴,喝了杯水,他觉得还有余怒未消,坐在沙发上又继续开骂:“你看看人家王涛,整天在家里做作业,多乖!闲了还帮家里干点活,你问问你自己,你这一天除了玩,还干了些啥?都十二岁了,还象小孩似的不懂事......。”
江国家皱着眉头瞟了父亲一眼,冲到喉咙口的话被他生生的咽了回去。“我还干的少呀,天不亮我就去给牛割草,还拾了一筐柴,难道你眼睛瞎了没看见么?是!王涛整天在家里做作业,可那是他不会做呀。不说王涛还好,一说我就一肚子的气。你也是当父亲的,可是你同王涛父亲比比多差劲呀。人家只不过是打饼子的,可是赚得钱你恐怕三辈子都赚不到。的确,象你说的,钱不是万能的。可是钱却是衡量一个人很重要的标准,如果一个人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他还配称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人么?你真枉称是医生了。连自己都没医好,还敢去医别人,不知羞!”说真的,江国家的这番话,虽然没有说出来,可是够狠毒的。如果在古代,判他个大逆不道之罪,一点也不为过,我们可以不信世间有什么轮回转世,但是因果报应却有它值得信的一面。江国家说出这番话的“因”到底再哪里呢?
那天江海不知吃了什么药,竟然连着讲了两个小时没歇气。江国家可就受不了。十二岁的瘦胳膊瘦腿怎能承受如此长久的站立,更何况心情抑郁着呢。他开始两眼冒金花,可是他又不敢走,摇了摇头,咬牙镇定自己。与这满天金星搏斗了不知多长时间,他忽然感觉眼前黑茫茫一片,好象天塌了一般。扑通一声,他倒在了地上,在他昏迷的刹那,他隐隐约约听到父亲说:“他×的,还给我装睡!”
后来,江国家听弟弟说,当时刚好来了一个人找父亲,要不这件事还不知怎么没完没了呢。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着,父子俩的关系如死海一般没有一点生气。江海忙,忙得一塌糊涂,他奇怪别人为什么老是不听他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和他有矛盾。他不认为自己错,经常地,他独自一人坐在院子里,一支接着一支吸烟,眉头紧缩,神情痛苦万状,好象世界上有天大的苦难令他担忧着,而别人却无法理解他的苦楚。家里人从他身边走过,他不理,别人也来个还以颜色,不闻不问。这就让他更苦恼了,同时又夹杂了无可奈何的失落。这不能怪别人,他的表演实在是太老套了,二十年如一日,大家虽然口上不说,可是心里明白,他只不过是个空壳,内心里其实什么都没有。要是非找出东西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一把自寻烦恼的干草,但是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想去点它,免得惹火烧身。
到了十六岁的江国家,给父亲下了一条评语:自以为比谁都聪明,其实比谁都笨。
这时候的江国家,虽说和父亲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已经基本上没有语言上的交流。除非万不得已,每碰到这种事,江国家就象吃了苍蝇似的恶心。“爸,有人找你。”“爸,吃饭了。”“爸,这是我叔给你的东西。”父子之间就只剩下这无谓的客套了。江国家觉得自己过的好累,十六岁的年龄却分明有了六十岁的沧桑心情。“活着真没意思。”江国家的嘴里竟然时常冒出这种可怕的思想。
十七岁的那年,江国家做了一件事,使江海才开始发觉:这孩子了不得。尽管这句话他一辈子都没有对孩子说。可是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那是秋天的麦收季节。江国家对那个季节的印象是比夏天还热,热得他真想把自己的皮割下来,放在冷水里泡一泡。在握住镰刀的刹那,江国家就明白自己报复的时刻到了。
一人五行麦子,江海带头。在江海割了一二十米的时候,江国家才挽起袖子动手。
他要让江海输得心服口服。
这场仗江国家赢得很艰难。他靠得是一股要爆发的仇恨的力量,可是他缺乏最起码的常识和经验,不知该怎样又快又省力,只顾盲目的挥舞着镰刀。半个小时后,他不仅没有超过江海,相反距离拉得更大了。他急火攻心,手上的镰刀失去了控制,小腿上好几道惨不忍睹的血口子就是他为此付出的代价。身体里象一锅烧开的热水,肆意翻腾,没命的从他的汗孔里往外奔涌,他的眼睛蚀得睁不开了。呼吸艰难,胸部缺氧似的难受。麦子已经割过半了,他和江海的距离好象还是差着一二十米。
江国家直起腰,深深地喘了一口气,“难道我永远超不过他么?......不行,我不能输,我就是死也不能输给他。”这几句话是江国家咬出来的,
如果一个人连死都不怕了,那他是什么事情都干的出来。
他的镰刀挥得更猛了,小腿上的血口子越来越多,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他胡乱的在腿上抹上干土。他感觉心脏停止了跳动,唯一能知觉的是那无边无际的麦田。一刀完了,割下一刀。毒辣的太阳,聒噪的蝉,流动的风,还有身边的世界他统统的忘记了。割麦子对他来说已经不是命令或者行动,而是机械式的运动,他好象成了一架没有灵魂的机器。脑袋只有一个指令:割!
终于他赢了。在他割到地头时,父亲在他屁股后头还有十米远。他什么时候超过父亲的,他一点也不知道。他笑了,笑得很纯粹,很快意。当然他没有让父亲发现他的眼神。他要让江海知道,他只不过是随随便便地就把他赢了。
江国家所要表达的全部含义,江海全都感觉到了。冲入他头脑的第一个意识令他不寒而栗:我真的老了么?......。要知道江海还有许多野心没有实现,他相信自己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而如今都晚了,回想过去,他感觉自己真是一是无成。绝望的遗恨撕扯着他的心,“不,我不能就这么完了。”江海还想抓住他最后的一丝欲望。
对于超过自己的对手,人们往往会想出两种办法,一种是捧,一种就是摔。江国家的沉默,象一座大山压在江海的心头,这比骂他两句还难受。骂人,江海可以将十倍于对手的气势还骂,可以将胸中所有的愤懑发泄干净。但是沉默就不一样了,江国家的沉默不是懦弱,不是服软,而是一种比子弹更可怕的轻蔑。自尊心很强的江海,本能地选择了第二种方式。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千古名言,出不了孝子那是棍棒还不够狠!江海树立的指导方针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和江国家不可逆转的命运。
眨眼进了二十一世纪,江国家又长了几岁,胡子硬楂楂的,个子比江海多出一头。没变的依旧是他寡言少语的脾气。这时候的江国家结婚了。
可以想象,成人后的江国家是多么渴望自立门户。但是事与愿违,不管他做出怎样的决定,父亲都如蜘蛛网一般将他罩在里面,令他动弹不得。如此僵持了几年,江国家终于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他这次是无论如何也要和父亲说清楚的,不然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活得太窝囊。
问题的焦点是江国家想把父亲的中医诊所办回家去,把这间街上的门面房空出来,自己准备做生意。这个决定无疑让江海恼羞成怒,这不是让他打回原形么?
这间门面房既不是江海的,也不是江国家的,而是江国家丈人的。这就有戏看了。
江国家和父亲当面谈了一次,江海一口回绝。原因他没有讲,江国家约略猜出一点。在儿子的眼里,他觉得父亲的理由很可笑,很荒唐。中国人好面子,江海也是如此,不过别人的面子起码还有点底蕴,而他纯粹是花架子,一戳就破。中医好处几乎尽人皆知,既吃不死人,可也医不好病。人们这种观念的形成多半都是庸医造成的,一辈子靠着两三个方子滥竽充数于救死扶伤的队伍里,还自诩为华佗再世,说的好听点这是恬不知耻,不好听就是误人性命。江国家觉得父亲就是这一种庸医。当初父亲想把这中药摊子交给他,他没要。后来父亲把诊所搬到江国家丈人空着的门面房,来看病的人虽然多了,可是额外费用也不低,到了年底也仅能维持。就这还是江国家丈人为了顾全面子,不向他要每年将近两千块钱的房租费,而江海也就这样装糊涂的无赖下去了。而且更要命的是,江海自从把诊所搬到靠近大街的门面房后,才好象真正找到了当医生的感觉。不管怎么说,他也算行医三十年了,何况还有那句形容中医大夫的古话:越老越红。就凭这份资历加上这块处在全乡黄金地段的门面房,他以为自己终于到了宏图大展的时候了。就凭这几点,江海怎么可能回到过去那个犄角旮旯的家里呢?
不少长辈告诉我们,生活的路是崎岖不平,充满坎坷的。这话一点不假。就说路上的那些坑吧,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陷进去。这里面透着运气,透着神秘。如果不幸让你踩着了,你也别怨天怨地,再套一句长辈说的话:这就是你的命。你瞧,长辈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多少丰富的经验。
命是什么?说不清。不过在周围却能经常听到认命这一类的话。
认命吧,你这辈子注定不是生意人,干什么赔什么。
认命吧,要是你离了婚,下次找的肯定比这个还差。
咳,这命可真是个鬼魅。
那天江国家去诊所叫父亲回家吃饭,就在他准备掀门帘进去的当儿。一句话让他不由得痛了,他听出那是父亲的声音。“现在的孩子真是不象话,说他一句顶两句”江国家想:我顶你么?“而且什么事都不知道干,整天懒在家里,都快三十的人了,你说可气不可气?”江国家想:我什么时候懒在家里了,从我结婚到现在,我给你要过一分钱么?这钱是天上掉下的么?“让他接我的摊子,他还不要。心高气傲,他以为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江国家想:哼,你就是给我什么我都不想要,更别说你那摊子了。“老王,你想想,我这一辈子容易么?到如今,落得一身埋怨。我有时候真连死的心都有。”
江国家实在是忍不住了,他一把掀开门帘穿进去,想都没想就把他这几天的闷气发泄出来。“死?!你真的想死么?我成全你。”江国家从门后拿出一把剪刀递给父亲。
江海楞住了,他没想到儿子在门口偷听,没想到他敢向自己顶嘴,更没想到的是,儿子竟然敢拿一把剪刀来威胁他。短暂的沉默之后,江海恢复了常态。他可不能在外人面前失去了自己的尊严,他还想好好地活人呢。
“老王,你看见了么?这就是我养的宝贝儿子!”江海从椅子上跳起来,破口大骂。“他今天竟用剪刀来对付我。”
江国家此时已经疯了,根本不听江海在说什么。
“你不是死么?我把剪刀拿给你,你到是死给我看呀!”
老王是邻村张家坡的人,他不认识江国家,江国家也不认识他。可是面对这种事,再陌生的人也会上前劝两句。“孩子,你怎么能这么跟你爸说话呢?他可是你爸呀!”
“我没这种爸!”江国家一句就把他顶回去了。
老王面露尴尬之色,却又不甘心。“孩子,有话慢慢说,你先坐下来。......”老王亲热的拍着江国家的肩膀,想把他安抚住。
江海还没见过孩子跟他发火,但是看着江国家血红的眼睛,他胆怯了。脚步不由自己地就往门口走。
“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溜呀!”江国家赶紧几步,挡在门口。目光咄咄的逼着他。
“你是不是怕死呀,要是怕死,你就别说那种话。好象我在逼你上吊!”
“谁怕死了!谁怕死了!”江海的声音很高亢,可是脚步一直在往后退。
老王抓住江国家握剪刀的手说:“你这娃娃说话怎么这么吓人呀,你爸要是死了,你还能好!”
“好!?我要什么好,他只要敢死,我就敢偿命!”
“你胡说什么?死那么容易?”
“江海——!”江国家指着父亲骂出他的名字。“死很容易,我今天教你。”
江国家趁老王没注意,右手往上一翻,朝自己的腕动脉就扎了下去,顿时血流如注,喷了老王一脸血。江海吓得面色苍白,倒坐在地上。
江国家把剪刀扔给江海,“看清楚了么?要不要我再示范一下。”
老王按着江国家的手腕,气都快上不来了。“孩子,快走!......。”
“叔,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你让我今天把话说完。”
“说个屁!你快给我走!”老王活了半辈子,还没见过这么犟的孩子,简直犟得让他害怕。
这时候,有几家邻居循声赶了过来,一见这场面,就知道事情闹大了。不由分说,架着江国家就往门外走。(完)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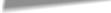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