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据重在实证--《牛石慧即马士英》质疑 |
考据重在实证--《牛石慧即马士英》质疑
萧鸿鸣
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0年4月份的《美术&设计》上,鸿鸣非常有幸地与吴之+先生同时在讨论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牛石慧的问题。
关于牛石慧,鸿鸣因研究八大山人,从而对这位与八大山人同时代且又有交的杰出书画家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是,奈何史料文献极其匮乏,十余年中,仅觅得只鳞片甲而已。而历来对牛石慧的研究,又多有谬误,如郑秉珊•拙庐先生的“牛石慧即八大山人”说;叶德辉•奂彬先生的“牛石慧即八大山人兄弟”说;以及李旦先生的“牛石慧即青云谱二道长朱道明”说。这些误传和谬说,鸿鸣曾先后在拙著《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第14页、26页、103页、125页;拙著《八大山人印款说》233至234页;《南方文物》1999年第一期《也谈八大山人几个问题•九•牛石慧其人》;《美术&设计》总第八十四期《关于牛石慧史实问题的实地调查》中作了尽可能的辨谬和追溯其错误根源的介绍。在这些文章和书籍中,虽因史料的匮乏尚未形成一个研究牛石慧的学科,但却并未亦步亦趋地步人后尘,而是有一点史料,作一点公布,说一点自己的研究,慎之又慎地做着探索。
吴之+先生的大作《牛石慧即马士英》一文刊载于《美术&设计》后,鸿鸣先是兴奋,继而是逐字逐句地拜读文中的“八考”。但是,原以为牛石慧的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定论的文章,却在读完该文后,令人疑惑不解。此文虽举所谓“八考”,但实在只是一个构架在海市蜃楼之上的幻影,无一考令人信服。思之再三,如梗噎喉,不吐不快。故撰此小文,祈教于海内外牛石慧研究的方家大正。
一、 马道常与马士英诸方面之比较
1、此马非彼马,路遥万里、各自不相融
吴之+先生在文中认定“牛石慧必释家衲子而非朱道朗、道明辈丹客羽士。”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在肯定牛石慧非青云谱道士的同时,吴之+先生却紧随着提出了一个违背逻辑、令人十分惊讶和荒唐的观点,言牛石慧“应与青云圃开山祖马士英葛藤纠结,有千丝万缕的浮世因缘。”即:牛石慧虽不是青云谱的开山祖朱道朗,也不是朱道朗之弟、青云谱的二道长朱道明,但却是青云谱的另一“开山祖马士英”。
吴之+先生在文中“牛石慧即青云圃开山祖马士英”的结论所得,不知其所依据的是何方文献和史料,文中未标明出处和来源。鸿鸣只能依据其“青云圃开山祖”的思路和吴之+先生所用引用的有关青云谱开山祖之一的马道常文献中的“涉大江、过越王城”来进行猜测。因为这不仅在吴之+先生的文中,所言明的是:特定的、座落在南昌市南郊十五里的净明派道观青云谱,更因为在该道观创建之初的人员当中,唯一的“马”姓道人,仅有马道常一人。故知吴之+先生在文中所指的“开山祖”当为马道常无疑。
但是,翻开不管是康熙辛酉原刻版的《青云谱志略》,还是1920年延寿居士订正、徐忠庆重刊的《青云谱志略》,这都让我们明白无误地知道:青云谱开山祖之一的马道常,却是一位从年龄、籍贯、姓氏、在青云谱修道的时间上,与明末大奸臣马士英毫不相干、路隔千里的另一人。
在康熙辛酉原刻版《青云谱志略》人物•十二至十三页(见图一)中载曰:“马道人者,道人生于蜀,本姓上官,莫知其名,后易姓法名道常,号常住。亦莫知其易姓出世之故。涉大江,过越王城至南浦,稍言其经历地,朗(朱道朗)遇之省城,同至谱内,年可六十许,肢体雄伟,须眉间另具一色相。书法飞动有生气,然亦不甚书,昔之相识者叩之,辄不应,凡有馈遗悉屏不受,计六载如一日。康熙丙午夏四月七日夜,索茶集众谢曰:吾今且去矣,取片褚书偈而逝。偈曰:非恍非惚,清清白白,解下连环圈,丢去生死窟。咄!清风明月,六年无说补还亏,缺一对聋耳根,三般真药与君诀,我非拙静,裹守红炉,动中添白雪,去来来一笑别,次日焚化,举火烟腾,忽见一鹤盘旋,热焰中时垂朱顶,示人久之,绕谱三匝而去,数百人共观焉。朗(朱道朗)观其偈:已臻无上之诣,而书亦如干日而已,逝之后又如此盖通昼夜之,故忘生死之大,而与天为徒者,其丰干、懒残之流欤。朗(朱道朗)既幸得其人,又窃幸其继。”
马道常的介绍虽不甚详细,但其原籍,俗姓、法名、法号以及与朱道朗的交往,来青云谱的时间和卒年等来龙去脉,却是交待得清清楚楚。
对于马士英,除《明史》卷三百八•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中有长篇的介绍外,许多有关明史及南明史的书籍中,均有详尽的介绍。为不赘文,鸿鸣在此对马士英略作介绍如下:
马士英(约1591-1646)字瑶草,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贵阳人。崇祯时累官右佥都御史。坐事发,复起为兵部侍郎。1644年明亡后,马士英等拥立福王于南京,升东阁大学士,进太保,与阮大铖相勾结,专权昏愦。日事报复,名器猥滥。清兵破南京,饰其母为太后,奔杭州,事露,杭人逐之,窜伏天台寺。其家丁缚献清军,被杀。
吴之+先生所言马士英即马道常,从以上的比较来看,除去二者中马道常易姓后姓“马”与之相同外,余无一处与马士英有瓜葛。二者可谓途殊而异归,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的。
2、马士英“隐青云圃道院”的时间与青云谱的创立时间风马牛不相及
吴之+先生在文中称:“马士英明崇祯中谪居南都,”“隐名换姓屏踪匿迹禅隐青云圃道院”这一结论的得出,鸿鸣不想论证“马士英崇祯中谪居南都”是否一定就是吴之+先生所言的南昌或所属地域范围(“南都”之说,实乃是明末遗民对南京福王弘光小朝廷的称谓)。但是吴之+言之凿凿的“隐青云圃道院”,鸿鸣则必须有所考证。
在考证问题之前,鸿鸣想试问一下吴之+先生:您是否见过康熙刊行的《青云谱志略》?如确曾读过,吴之+先生为什么会在“马士英崇祯中谪居南都”,“隐青云圃”的时间与青云谱的创立时间问题上,犯一个非常要命,但却又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呢?
在《清云谱志略》中,黎元宽于康熙乙卯吕祖诞生日所作的“青云谱志略序”(见图二)中写道:“……青云谱在豫章城南仅十有五里定山桥……朱良月至洪崖顷兴起之,即瓦砾之道,以至金碧之功。”时任“江西按察司副使”的周体观,在“定山桥梅仙道院记”(见图三)中,则对青云谱的创建时间有更加明确的交代:“南昌府东南十五里有定山桥,桥旧,溪也病,涉者枉之,遂不从溪。溪澳、钓迹存焉。盖汉南昌尉梅福会钓于此也,后人因之构祠溪上,曰:梅仙祠。唐贞观中,改名太乙观,久而墟,墟而复构者屡矣。辛丑秋,道人朱良月来游,于溪就祠之基而扩之。起方壶之宫,建绛节之期,以事列仙崇苑,宇置丹灶,以待四方羽客……”入清以后的青云圃,是朱良月自“辛卯秋”即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以后,在梅仙祠废墟上重建的结果。直到康熙六年丁未公元1667年,青云圃作为道观的规模才初步落成。其道观名“青云圃”,则是自创建之初一直沿用到清嘉庆二十年(1815)由戴均元将其“圃”改为“谱”,以示此道观“青云”传谱,有稽文查。
吴之+先生在文中言“崇祯中”。崇祯一朝(1628-1644)凡十七年之“中”,不管如何界定这个时间的上下限度,其距“青云圃”的创立和落成,都将是相隔33至17年的时间。一个子虚乌有的地方,或者说仍是一片瓦砾的场所,何来道观让曾身居高位的马士英隐居?“隐居青云圃”之说当然难以成立。
3、马道常的行踪与马士英“隐青云圃道院”行踪不符
《青云谱志略•人物》中,对于马道常来青云谱有明确的交代:“马道人也……涉大江,过越王城至南浦,稍言其经历地,朗(朱道朗)遇之省城,同至谱内,年可六十许……计六载如一日。康熙丙午夏四月七日夜,索茶集众谢曰:吾今且去矣,取片褚书偈而逝……”
马道常自“年可六十许”在青云谱,“计六载如一日”,于康熙丙午去世,仙逝的年龄约在66岁左右。康熙丙午为1666年,上推六年,为1660年,顺治十七年庚子或1661顺治十八年辛丑。这个时间,正是朱良月“辛丑秋,道人朱良月来游,于溪就祠之基而扩”青云谱的时间,也是马道常“涉大江,过越王城至南浦,稍言其经历地,朗(朱道朗)遇之省城,同至谱内”的时间。
马道常作为青云谱的创建人之一,其行踪如此明确,恐怕与《明史》列传•奸臣中马士英此间详尽的行踪和吴之+先生所谓的“考证”:马士英“崇祯中来南都”“隐青云圃道院”的时间是相隔的太远了。
4、马道常、马士英的生、卒、籍贯
马道常的生年史无记载,但可依据其卒年来推算出较为准确的生年。马道常逝于康熙丙午(1666)夏四月七日夜,在青云谱六年,来青云谱之初是“年可六十许”。这就是说,马道常逝世时约66岁。由康熙丙午(1666)上推66年,马道常约生于公元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庚子,这个时间若有误差,仅会在一年之内。
马士英的生年,公认的是约在1591年,万历十九年辛卯。与其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科进士相合。死于1646年,大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丙午,得年55岁。
按吴之+先生所论,马士英即马道常,马道常逝世时当为75岁,即已死二十年的马士英需要再活二十年,才能来青云谱修道。而按此论,马道常的生年亦要向前推二十年,马道常“辛丑”随朱良月来青云谱时,其谱志中所载便不可能是“年可六十许”,而应当是“年七十余”才对。文献的不可改动性,是马道常与马士英二者决非一人的有力实证。
此外,文献还无情地在告诉后人:马道常“生于蜀,本姓上官,莫知其名,后易姓,法名道常、号常住。”而马士英则为贵阳人,本姓马,字瑶草。史料、文献中并无变姓、改籍的记载。更因其臭名昭著,其姓、名、字、籍贯当源出有本、依之有据,决非混淆。
二、牛石慧与青云谱和马道常、马士英之比较
1、牛石慧与青云谱
在现存公布的所有史料之中,包括后世纂改的《青云谱志略》,均未见有只字片言可证牛石慧与青云谱有任何瓜葛。在有关牛石慧的史料中,牛石慧一直是以释家面目而存世的,从来也没有任何史料涉及牛石慧曾做过道士。而青云谱开山祖之一的马道常,以及二道长朱道明在青云谱修道期间,牛石慧在奉新奉化乡上村牛石庵馥柏寺做和尚,其法名法慧的行踪,史载文献则又是清晰明了的(1)。
不可辩驳的文献存在,强扭三人在一起,如何让人信服?
2、三者年龄、籍贯的差异
按吴之+先生在文中马士英--马道常--牛石慧的逻辑和结果,迫使鸿鸣不得不将这原本完全不相干的三个人物来作一比较。
牛石慧•法慧的生、卒年不详,其作品中见署“七五”、“七四”老人(见图四)。又见有甲戌《富贵烟霞图轴》(1694康熙三十三年)丁亥《松鹿图》(1707康熙四十六年)的署款作品存世(见图五)。因之可知牛石慧•法慧的卒年当在这二年之后。在民国间依据同治九年重修汪浩撰《南昌县志》卷四十二•人物十三•齐鉴条目内,有一款涉及牛石慧的文献,亦可证实牛石慧此间仍然健在。该款曰:“齐鉴,荆山人,工画精墨法;及游京师,画益有声……其画者比之罗饭牛、牛石慧焉。”该款中所涉齐鉴、罗牧•饭牛均为清初康熙间活跃于南昌地区的著名书画家,是包括八大山人、朱容重、澹雪和尚等人在内的“东湖诗画会”的成员(2)。文献中用时人罗饭牛来作为衡量齐鉴的书画水平,显然与罗饭牛同时被提及的牛石慧亦为当时的名士是毫无疑问的。牛石慧或为“东湖诗画会”的成员亦不是没有可能。因此,这条文献便是牛石慧康熙四十六年前后仍然健在的又一佐证。
按照牛石慧康熙四十六年仍然健在的年龄界限,来较之于马道常和马士英:马道常1666年康熙五年逝世时66岁计,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以后,马道常若是牛石慧,当为107岁。
马士英约生于1591年,若马士英是牛石慧,并活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以后,马士英当为116岁。
排比之后,吴之+先生的马士英--马道常--牛石慧的结论,真尤痴人说梦矣。
此外,牛石慧作品中常署“西江牛石慧”(见图五)。“西江”一词,是明清之际专指江西所属地方的特称(3)。牛石慧有此一署,当视为牛石慧对自己籍贯的代称,这与马道常“蜀人”,马士英“贵阳人”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3、牛石慧、马士英二者作品之比较
马道常无作品传世,故只能就牛石慧、马士英二者的作品作一简单的比较。
牛石慧的作品风格(见图七、图八),不管是书法还是绘画,因其与八大山人的交往,其成就虽稍逊于八大山人,但作品中的整体风格,却留有明显的八大山人痕迹。在书法的间架结构和笔划运用上,他象八大山人一样,并不去注重笔划中的点划勾挑有多大的变化,而是利用秃笔中锋,与宣纸纸面磨擦流动所产生的飞白,来达到一种雄浑老辣的气势和笔势。从而形成一种与八大山人晚年众多作品类似的艺术风格的作品。而在绘画风格上,不管是动禽的造型,还是构图的取势,均都带有世人一看便知的八大山人绘画作品的明显风格。
不管是牛石慧的书法还是绘画,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淡墨秃笔,线条粗细均匀的个性特征,还是人们从作品中感受的恣意之中的那种古劲和高秀,你都能够感觉出均匀之下的圆浑和古拙。
马士英的作品(见图九、图十、图十一),书法明显地让人感觉到点划转折明显,线条错落,缀连成行以及跳跃的左右倾伏,犹如醉仙舞剑的节奏风格,这显然是一种师出米芾风格的再造。而绘画作品,则处处体现出作者运笔过程中的侧锋,多皴、点线方仄的风格。其意也多为模仿前代如董北苑等,这种风格的承袭,是与牛石慧作品具有完全不同风格和具有明显区别的。
由于以上鸿鸣对牛石慧与马道常、马士英三者诸根本性的问题已作了明确的质疑,故而吴之+先生在文中所谓“马士英诞日,卒日皆为牛王节”、“其化身牛氏”、“尝于豫章见一头陀拜石”的“考证”,以及所谓公安鉴定画像等荒诞的做法,便成为无任何价值、不需一驳的谬论。
至于吴之+先生文中一会儿说牛石慧不是丹客羽士,一会儿说牛石慧为道教净明派开山祖;一会儿说马士英为“青云谱开山祖”,一会儿说马士英“禅隐”、“头陀”的混乱逻辑思维方式和行文方式,那是吴之+先生在哲学方面修养欠缺的严重表现,亦不是本文所要论及的主题。
考证一个人或一个事件,需要大胆的假想和假设,但要由假想、假设到证实假想和假设,其关键的要素是要有确凿的、直接证据。乾嘉考据学派不管是“吴派”还是“皖派”,遵循的都是这一不可动摇的法则。
浮华之世,我们却在做着这门冷僻、清苦但于后世或许有益的考据工作,故当慎之又慎,不至贻误子孙矣。
注释:
(1)详见拙文《关于牛石慧史实问题的实地调查》。
(2)详见拙文《江西派画家罗牧》。
(3)详见拙文《也谈八大山人的几个问题》。
|
|
|
|
 |
|
回帖 |
 |
|
| 回复人: |
木水 |
Re:考据重在实证--《牛石慧即马士英》质疑 |
回复时间: |
2006.04.21 17:24 |
|
深不可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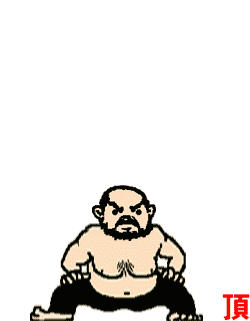
|
|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