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词(二、三) |
张记狗肉铺前。
场景是这样的。挂着油光光“张记狗肉”的店铺面向正南,这是一条这个城市中最著名的食品街与风味街。它具备了一切小街的特征:窨井的盖子开着,成为最方便的垃圾筒,盛装小吃店倒出的污水,剩饭菜,到了夜晚则成为溺物的排泄所。溺物的另一个佳处在每一个墙角,灰黄的墙皮被沤得泛着碱花,散发着臊臭。整条街上布满了新疆羊肉串馆,回民清真饭店与耳朵眼炸糕店,阿拉伯肉饼店,张记狗肉是这里最出名的。出名是因为他的狗肉做的地道,包括他的杀狗技术,那才叫刺激。在张记狗肉的右首有一株大柳树,总会拴着一条狗或吊着一条狗,他的杀狗方法是先把狗收拾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如同待嫁的新娘,然后他举行祭刀仪式,用一口烈酒卟的喷在刀上,一滴滴的落入地下渗进去,再用火一点,刀子呼的一下燃起,瞬间熄灭,蓝瓦瓦的颜色忽而闪现即告消失。这时吊在树上的狗正在死命挣扎荡来荡去。他就会一个箭步上前迅速的拎起狗的后腿,在狗的腹股沟处“刺儿”的一下,麻利的跳开,狗血飞溅。随着狗的痉挛,血喷散在方圆三米的范围内,更多是喷在柳树上。这时张刀把子,也即狗肉店的老板,杀狗的老先生就会咪缝起小肉泡眼拖着肥壮的肩膀站在一旁沉静观望。
总会有人群围观。或似笑非笑的抿着唇角,或惊讶万分的样子。而女人的一般姿态是,用一只手捂住眼睛顺势往身边的男人怀里一靠再叫一声“妈呀,真残忍。”可这并不妨碍他们进店吃狗肉,血腥味刺激着他们的食欲,使他们的胃口大开。
张记狗肉的另一个闻名在于他狗肉的贼味。许多人来这里只是想尝一尝北京叭狗与德国黑贝的肉味与藏獒及普通犬有什么不同。他这里总有一些来路不明的狗,都那么名贵。张刀把子宣称他曾屠过一条大麦田坪犬,纯黑的壮如牛犊。“那东西才叫有血性,血都放干了还扭动了半个多小时,眼睛瞪得出血!”他常在店里张扬。但却总不见有狗的主人前来探询。他可以明目张胆的在他的院下一个肉饵,里面包一个带倒刺的钩子。凡是嘴馋的畜生都会落入他的滚水大锅里刮得刷白十分性感的抛到案板上迎接食客,秀色可餐。
此刻他已动作麻利的褪完了一只昆明犬与本地犬的杂交后代。他的下手正以木杓舀锅里的沸水后倾入窨井,一阵阵热腾腾的蒸汽带着狗毛的不知所以的味道弥散开来。这是个讯号,老饕们自然会逐味前来就象一只馋嘴的猫熟悉每一种海鱼的腥味,情人在夜里也能分辨彼此的气息一样。这种群中的一个就是游民部落的索尔。他是个满人。他来了,并且带上了张秋良。
“刀把子,你妈的又有什么新品种吗?”索尔要高出张刀把子半个头,站在他背后看他操刀游刃有余的解狗,问。
“来啦,最近没有,现在那帮混帐都把他们的畜生看的牢牢的,除非有发情的跑出来但又忙着谈恋爱,理都不理肉骨头。我那块肉都下了四五天招蛆了,现在耗子都不吃。”头也没回,他答道。
“那合着我们白来啦?”转向张秋良,“看起来还真没这福气。那我们改吃别的吧,你点地方咱就去。”
“Son of a bitch!”张秋良骂。“行,反正馋没解决,大饱眼福了,你说狗血要涂到键盘上该怎么样?”
“别扯谈了,快找个地儿喂喂脑袋就得赶回去,Mark在等着呢。说上哪吧。”
“贵宾楼。”
“那他妈得把你卖喽,还没狗肉值钱呢。”索尔推着张秋良出门。并冲刀把子喊:“走啦,”用手挥飞两只嗡嗡的狗蝇。
“等一下,这现宰的你们不吃?”刀把子停下活计,想挽留住他们。
“没意思,要吃这下三滥哪都能找到,泛不上找你个龟儿子。”秋良高声回话。
“那是,那是。”脸上的笑挤成一团,象一多皱的包子。“那把这狗腿带回去吧,黑贝的,前儿逮着的,想给我爹留着呢?”他唤了一个店伙计从冰箱里拿出一枚金红色的狗腿。
“操,不是说没有吗?”索尔停步转身笑问。
“嘿嘿,我爹要从浙江老家来,他还没吃过我做的熏酱狗腿呢,这你们拿去吧,不要钱,回头我再熏一个。”
“灰孙子,我们成你爹了!”索尔接过狗腿,冲张刀把子打了个再见的手势,转问张秋良:“贵宾楼不去吗?”
“这一只狗腿还撑不死你?”
“我怕撑不死你。”
——3——
五个包子只吃了两个。这可不是他赵大卫的饭量。
“今天怎么没跟跟叶谨一块吃饭?”坐在副驾的售票员瞟了眼大卫问。
“啊。”心不在焉的答。这是起点站,客还没满,时间距开车还有三分钟。
“你好象不太高兴?”售票员刘晓莉稍有姿色,这时从票夹子里掏出枚小镜子照着涂口红。并由镜面反射接触大卫的眼光。
“你烦不烦?”赵大卫没好气的答道。
“人家关心吗。”显得委屈,刘晓莉撇了撇嘴。
“妈的!”大卫脱口而出,随又转向惊诧着张大了涂一半口红的娇唇,“没骂你!”
刘晓莉沉默了。一时车内寂然无声。乘客蔫头巴脑的伏在椅靠背上打盹。刚上来的也轻手轻脚的。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或呆呆望着车外,或闭目瞌睡调息养神。这个中午十分郁闷,风不知躲到哪里。火一样的光线直直倾泄下来,在地上完成一个漂亮的反弹折入车内。有一股汗臭味与脚上腋下分泌出的体味混在一处奥妙非凡。
“到点了,走吧。”刘晓莉看了眼头上方的石英钟对赵大卫说。
扭动钥匙,猛踩离合器,大卫象匹烈马样趵着蹶子呼的一下串出去,许多乘客的头撞到了椅背的铁横梁上。开始有人骂。赵大卫充耳不闻。把油门一踩到底,嘴抿的泛青,目光坚定的望着前方惊慌散逸的过横道者。
“干什么呀,开慢点!”刘晓莉喊。
“去你妈的!”赵大卫骂,但刘晓莉似乎没听清楚。
“你说什么?”她站起来冲着赵大卫大声发问。
“去你妈的!”赵大卫转头向她,口水溅了她一脸,有口臭的怪异味道。
无声的坐回去,刘晓莉捂住双眼抽搐着肩膀。车里的人似乎骂够了,或者已习惯了速度。但却都活跃起来,有些兴奋与好奇的盯着前面这两位。
巴士虎虎生风,一站地(这个城市中的所有站点都是等距的,不论闹市区或郊区线路一律0.75公里。)眨眼即到,上客,下客,巴士又疯虎一样咆啸向一站地。
索尔与张秋良在新街口的7路站台候车,狗腿被他们用卫生纸包裹住胫骨部位捏在手里拎着,油光可鉴在阳光照耀下要滴下来,张秋良已把长发用塑筋束成马尾垂在肩后,背上背着双把位键盘。他们都大汗淋漓,敞着印有Slayer字样的对襟黑绸衫,象两各阳光下的刺客或异路侠者坚毅的站在那里骄傲坚毅,而站台的水泥遮阳(遮雨)檐下的长石凳已挤满了或等车或乘凉的人们。
赵大卫的车疾驰过来,嘎然而止。
张秋良和索尔先上去。秋良把键盘挪到胸前,这样就避免碰坏。已经有一把芬达(Fenda)牌的就是在7路车上挤掉了一个把位,调子弹起来古怪的很。那把琴他做L0-FI录音了,使用单轨机,挺粗糙的。而这把是野马牌子的。他不能再把它弄坏。一个人如果两次犯同一种错误,除非他是刻意的,否则他就是白痴。在对待自己心爱的情人的乐器上,张秋良可不想成为白痴。而对于别的事情又另当别论。索尔则依旧拎着狗腿,单手吊在汽车抓环上。谁也不想弄一身狗油。所以鱼贯上来的人都与他保持一个合理的距离。防止污了裙衫西裤。
刘晓莉过来卖票。车上有投币机的,但那只是个摆设。所以有人说机器永取代不了人。因为机器无心。无心则无为,它可干涉不了偷票者依旧乘车。但人不同。所以刘晓莉在沙丁鱼罐头般的人体中挤来挤去,扭动着身体,一些男人不失时机的在她身体上蹭着,脸上一派正经道貌岸然。对这种惯常的骚扰,也已见怪不怪了,只要他们还没有进一步动作,不碰触她的禁区,那不妨两厢无事。大家心知肚明,她暗地里咬牙切齿。
挤到索尔和秋良跟前,对索尔笑笑。老索是7路车的常客了。所以他们已熟识,并有过短暂的对话。比如“忙着哪。”“嗯,过去?”“对”之类的。刘晓莉并不知道索尔是个乐手,但她猜测这个打扮奇特的男人也许是个艺术家,画油画的,想到画油画她就心慌,就仿佛自己成了个裸体模特站在人前。她有些羞涩和耻辱,但均敌不住一刹那液涌的快感。她已二十岁了,正在思春,因此如果哪次售票无人对她骚扰,她就会涌起几许失落。这是一种压抑。她觉得自己怪怪的,有些无耻。但事实上是个正派的女孩子。
“忙着哪?”索尔搭话。
“嗯。你们两个?”她接过一元钱,指着张秋良问索尔。
“是,你怎么知道?”索尔笑问。
“猜的。你们都留长发,又在一块儿,你们的……”她顿一下,把钱装入票夹,撕了两张票根递过来,“气质,对,气质一样!”她似乎因找对一个正确的词而欣喜,兴奋的脸胀的通红。
“喂,良子,听见吗?人说咱有气质呢。”索尔对秋良说。秋良笑着摇头。
“是嘛,就是气质!”齐晓莉肯定的点头。又往车尾走去。他们谈话的声音被车本身的噪声与人声遮掩所以无人注意他们曾进行过一场气质小论辨。
车尾也有一个长发男人。赵大卫见人已上完就把车启动了,速度依旧,这就使得人群都闪了个趔趄。一个小学生扑到在索尔的狗腿上,而后面的那个长发男人却一下子扑倒到刘晓莉身上,双手扣住她刚刚发育完全的乳房,长着短须的上翘的唇则落在她两乳中间,这样恰好有一个绝佳的视角从她的圆口刺绣汗衫看进去,丰腴的一对小东西挤在一起,中间的乳沟成为欲望的刻度尺。那个男人“啊”的叹息了一声,唇吻就落在这块绝佳的风景上。
这些都被索尔看在眼里,因为他一直用视线送她过去,他见她猛的转头闭眼,口型是一个尖叫的样子,却没有声音。他一手拽起身边的男孩子。把狗腿塞进秋良的手里,“我过去一下。”
三步就到车尾,手顺势拨拉开拥挤的乘客,索尔不出声一下子揪起长发男人,左右开弓扇了他几个嘴巴,然后冲他“啐”了一口说“你他妈的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又用右拳一记重锤打在他的下巴上,顿时有血顺着嘴流溢下来。那个家伙的嘴唇被牙齿硌破。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他丝毫没有准备,也许正沉浸在温柔的梦乡里脑淫吧。他懵懵懂懂的抬起头来问:“钱,什么钱?”
索尔继续挥拳,他的大块头已完全把对方震住,“还他妈问我,狗日的你心里不明白?司机,停车,让他下去。”冲赵大卫喊。
赵大卫充耳不闻,大卫依旧跃马由缰。
张秋良把狗腿胡乱扔到地上,护着键盘向前冲过去,人群自动闪出一条通道。使他很轻松的就跃到前车厢,跨过机盖来到赵大卫身侧。
“叫你停车,你听见没有?”他喊大卫不语。车速依然。
“停车!”秋良掏出把匕首顶在大卫的后颈动脉上,那里在蹦蹦的向赵大卫的大脑输送着给养。
“凭什么?”大卫说着,但已踩制动。车剧裂的顿了一下停下来。
“就凭让你停车!”秋良冲他轻蔑的用中指向上竖了竖。返身回到车尾,拎起狗腿,男孩子怯怯的望着他,他摸了摸他的脑袋。跟他温柔一笑说:“没事了。”
索尔扭起那男人的左胳膊背到身后,用手拨拉开车门,一脚蹬在那家伙的屁股上说“你他妈的下去吧。”
那家伙在车下踉跄两步,对索尔咆哮着:“小子,我会永远记住你的,瞧好吧。”
索尔向他屈右臂。
在这短暂的过程中,刘晓莉紧紧拥着票夹子抱在胸前,她听见自己的心脏在“嘣嘣”剧烈跳动,口干舌躁。脸由红转白,又渐渐恢复原来的颜色。她说不清楚刚才那短短的几分钟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男人栽到她身上。那双用力的手,在她胸口的一吻,然后另一个男人过来痛殴了他,把他赶下车去。他欠他的钱吗?他是真的栽倒吗?为什么自己只有一瞬的屈辱而更多的是一种快乐的感觉呢?我在犯贱吗?刘晓莉自问着,手扪前胸,长呼吸。仿佛又听见那人的叹息。为什么是悠长的使她心动呢?她有种痛心感。但旋即又被自己是一个受辱者,应该痛恨那混蛋的念头压下去,代之的是对自己的痛恨。她有些茫然若失。
而索尔的眼里,刘晓莉正惊魂未定。他见她紧紧攥着票夹,因用力指间被挤压的失去血色的苍白,而她还在战栗着。过去拍拍她的肩膀一笑,小声说:“没事了,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刘晓莉点头,艰苦的笑一下,脸上的表情古怪。
“开车吧,到三区A座停一下。”秋良向前面喊:赵大卫重又启动巴士,这一回速度缓慢下来,后面有排队的车龙在不停的按喇叭。而车内的乘客因刚才一番景象都变得缄口,只有马达隆隆,车轮在路面上擦过的沙沙声。
索尔和张秋良在三区A座站车下车了,狗腿已染上尘土。他们拐进A座右侧的窄胡同,走入后面低矮建筑下的一个老车库。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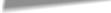 |
|
回帖 |
 |
|
| 回复人: |
hover |
Re:供词(二、三) |
回复时间: |
2005.12.01 15:01 |
|
宝贝啊 什么时候把别的都发出来 我们这里可等着你的呢
你也知道的 我可是个急脾气啊 别让我等的时间太长了啊
哈哈 宝
|
|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