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他写的(老枪) |
割麦穗
2001年06月26日09:50:27 网易报道 cyslm
>
刘洪斌长得挺魁,是个大闲人。入道10来年了,没人敢跟他皮干。
但最近他跟派出所副所长段晓林闹得不好,心里挺烦。
刘洪斌和段晓林半年前在片上合开了个场子----夏威夷洗浴按摩中心,钱是刘洪斌出的,段晓林占了三成的干股。
段晓林能,省厅市局都有人。平时在所里又不张扬,都说以后爬得最快的就是这人了。所里有人都预测了,再在所里混半年,所长肯定是他的,再过两三年,就调分局闹个副局长啥的----娃年轻啊,以后前途无量。传说他背景深得很。他爸是个老中医,以前看病救过一人命,那人现在就是省厅厅长。还有一种说法是那人是省长。
刘洪斌是通过一个兄弟认识段晓林的。两年前东郊的老闲人赵武旗让他拿枪给敲了,市局刑侦那帮当时追得紧得很。在危急关头那兄弟介绍段晓林----那会儿他还只是个警长----给他认识了一下,这下就交上朋友成了兄弟了。刘洪斌后来高兴没白交这个兄弟,知道他确实能,因为段晓林暗地活动了一下,市局那帮就没再追下去了。
刘洪斌当时开这个场子,也没忘了段晓林。他主动提出3成干股给他。有些事儿当然不用挑明。刘洪斌这么做,一是段晓林是他兄弟要报个恩;二是有段晓林罩着,这生意平安。按说副所长这个级别要罩这么大一场子不太可能,但刘洪斌知道段晓林能,所以他也不找别人。还有一条刘洪斌自己心里有底,他得傍着段晓林----不光生意上的事儿,因为他知道段晓林能。
场子生意红火得很,半年功夫,投资大半都收回来了。这年头干这行来钱确实来得快。有段晓林罩着,啥事也没出过。
其实刘洪斌那7成也不都是自己揣腰包里了。他是个义气人----西安的闲人都这样,要不在道上混不下去,也枉称闲人了。刘洪斌自己最多闹3成,其他的都分给跟他一块儿混的兄弟了。刘洪斌挺满足,他不贪财。他知道,只有这样,他才有好名声,有了好名声,他才能一辈子这么混下去。西安道上的人,没有不知道刘洪斌的为人的,都说他是个仁义的人。当然,也都知道他的厉害。
刘洪斌除了段晓林以外,在公安口上也认识不少其他的人----实际上段晓林是他这个级别的闲人认识的最低级别的雷子。市局法制处夏处是他的坚钢。通过夏处,刘洪斌认识的人越来越多,这么多年了,刘洪斌手上一大把雷子。省厅市局同样熟得很,雷子圈里也都认为他是个仁义人。但刘洪斌感觉,最能的人还是段晓林。
刘洪斌跟段晓林闹得不愉快就是因为这场子的事儿。那天刘洪斌喝了点儿酒,正陪夏处安排的一个部里的人在场子里耍呢,段晓林打个电话约他到一个地儿谈个事儿----段晓林从来不到场子去,有事儿最多就是一电话。
刘洪斌当时有点儿不愿意走,一是难得认识部里的雷子,二是当时正耍得高兴,新从哈尔滨来的一个小姐太好了,棉棉的,他有点儿舍不得。
刘洪斌还是开着车赴约了,距离不近,穿了大半个城----段晓林约他从来不在片儿里,地点离片儿都有段距离,刘洪斌明白,段晓林干啥都谨慎,他能嘛。
刘洪斌也是个谨慎的人,不过今天喝得有点儿高。约会地点是个小酒家半楼的一个小包间,楼梯陡啊,刘洪斌踉跄着爬上去,差点儿摔一跟头----酒确实闹多了,不过脑子还清醒。
进了门,就见段晓林一个人叼着根白沙在桌子旁坐着,刘洪斌呼着酒气也坐下来,问道:
“老弟,啥事?”“也没啥事,想兄弟了,不行?”段晓林迷起小眼睛,吐了一口烟。
“赶紧说,北京部上有人在饿那儿坐着呢。”刘洪斌从篼里掏出盒中华来,拆开来用指头挑出一根点上。然后把烟扔给段晓林。
“部上的?嗑,问远的,有用?”段晓林把烟扔回给刘洪斌,“那饿就跟你说吧,场子的事儿。”“嗯,你快说。”刘洪斌掸了下烟灰,抬头看着段晓林。
段晓林慢条斯理地把烟按灭,一字一顿地说:
“饿一个兄弟要到场子里去。”“来嘛,这是个啥事情?”“不是去耍,是要个路儿。”“来嘛!就是这事?”刘洪斌有时候有点儿不理解段晓林,即便这个人再重要,也不至于劳他大半夜跑这么远来商量,不就进个做事儿的人吗?刘洪斌有的时候觉得可气,不由得有点儿不耐烦,认为段晓林有时候象婆姨。
“甭急。俄这个兄弟还要占两成干股。”干股?!刘洪斌心里一激凌。不过他没言传,眼睛眯成一条缝儿,透过烟雾盯着段晓林。老皮了,刘洪斌不会把自己的反应直白地表现出来。他示意段晓林继续把话说下去。
“是这,啊,饿这兄弟你不认识,也是行里的人,以后都是自家兄弟。饿想咧,让他进来是为了个发展。占干股这事情饿是这样想的,你拿一成出来,饿也拿一成出来,这事情就成咧,不可能让你一个人拿嘛。”刘洪斌咽了口唾沫,清了清喉咙,和声细语地说:
“老弟,你把话说透。行里的人都知道规矩,兄弟们都是提着头办事的。你要多少没关系,咱是兄弟。现在你说卧人饿不认识,饿答应你没关系,可饿底下一大堆兄弟饿咋说?你给给饿个说法。”“哥你喝多了。该让你明白的事一定让你明白。饿跟你说了,卧是俺兄弟,饿信的是卧人,就是要个发展。饿现在是跟你商量,你不答应不要紧,饿今天把话搁到这儿。不行,回头就跟饿说不行。要是行,饿把他叫过来见个面,就是自家兄弟。你看咋样?”“兄弟,甭说了。就告诉饿卧是啥人。”刘洪斌没有应承任何事,他要探探底儿。刘洪斌跟段晓林是兄弟不错,也知道他能,可是他仅仅知道段晓林能,其他事情知道得不多。事实上,没人真正了解段晓林,除了刘洪斌身边的几个弟兄,道上的人没几个知道段晓林的。有时候刘洪斌心里想,自己利用段晓林,可人家也许把自己当枪耍呢。他有这感觉。
“嗯,你不认识。卧一直在外跑着呢,10多年了,刚回西安来。东郊的,跟赵武旗原来是一块儿的。但俩从不说话。”“叫个啥?”“白毅。你不认识吧?”“不认识。”“这样吧,这事情就说到这儿。哥你回去想一下,没麻达给饿言传,饿就去把卧叫来见个面。你该干啥干啥。卧不是还有部里的人在你那儿吗?”段晓林说罢立起身,径自出门走了。
刘洪斌回场子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小文,小文原来就是在东郊跟赵武旗一道混的,刘洪斌后来敲了赵武旗的头,小文就透他这儿来了。小文平时胆小,但人机灵,跟各路人都熟,是刘洪斌底下搞侦查的。
“饿跟你打听个人。”刘洪斌把小文叫过来,“你知道原来跟赵武旗一起的有个叫白毅的吗?”“饿不知道。啥事?”“没啥事,饿就是想知道卧是个啥人。”“啥时要知道。这事可能要问东郊位帮老皮。”“饿现在就想知道。你去问,人要问你谁打听,你就说是饿。”刘洪斌又去场子招呼夏处安排的部里人,他吩咐领班,跟小姐说小费全算他头上,爱闹啥闹啥,一定要闹够。他带着狡黠的表情跟领班说“把老皮一定要搞透,最好半个月爬不起来!”过了有俩小时光景,夏处来接北京人来了,老夏笑着跟刘洪斌悄悄说,卧身体是好。
送走了夏处和他的客人,刘洪斌刚回场子不大功夫,小文就回来了。
“刘哥,饿问着了。”小文办事利落,刘洪斌喜欢。
“慢慢说。”“唉,卧怂是个哈锤子,好多年前的老皮了。大概10年前吧,卧杀了个人,一直在外跑着呢。哥你可能听说过,就是割麦穗卧事,头现在还没找着呢。”刘洪斌点了点头,表示知道割麦穗的事情。
“卧怂最近两年都在云南呆着呢,现在倒白粉呢。”“嗯,成。哦知道咧。现在卧人在此地不?”“哎呀,饿也问咧,但都不知道。前年有个怂在云南见过,在咱这儿还没见。”刘洪斌打发小文出去,脑子有些发胀。他已经下决心不能答应段晓林。他隐约有点儿不安,这事情可能有麻达。
真正的闲人都不动白粉。刘洪斌知道这个规矩,倒白粉的事儿都是碎怂干的。刘洪斌跟底下兄弟说过多少次咧,没钱干啥都行,干不成就问他要,但绝不能粘白粉。刘洪斌不敢粘那玩意儿,怕道上人不齿;最重要的,他恨这东西。刘洪斌自己想,他开窑子还不算是做孽,但白粉可算是做大孽。现如今的窑姐有几个跟旧社会似的是生活所迫?所以刘洪斌从来没觉得对不起这些棒,她们愿意呀。真遇上良家出来的女娃,刘洪斌还有不少同情心,知道了往往还送些钱打发走人。
白粉可不一样,这东西害人。撩粘咧要敲头不说----刘洪斌倒不怕死,他这条命死过好几回了----还会危及他所建立起来的摊子。刘洪斌怎么也不能跟这粘上瓜葛。刘洪斌想了老半天段晓林安排白毅进来的意思,基本上心里有了个谱,但是他得确认一下。不过不管是啥原因,他都不能答应。但要是真是那个缘故,刘洪斌他可真要惹麻达咧。
刘洪斌过了两天约了段晓林出来,开门见山地说:“卧事不行。”“咋咧?”“卧怂倒白粉你知道不?”段晓林抬眼皮看了刘洪斌一眼,没有马上回答。两秒钟后,他说:“不知道。”刘洪斌心里清楚这个回答算是俩人系下疙瘩了。段晓林故意顿了一下实际的意思就是他知道白毅是倒白粉的。回答不知道有两层意思,一是白毅倒白粉这事不想让刘洪斌过问,二是明确表明了他不信任你刘洪斌,将来就是有啥事撩粘咧不能把段晓林跟白粉闹一起。
刘洪斌当下心里挺难受,脸上却没流露出任何表情,他无视段晓林的那个故意的停顿,装作关心地说:
“饿叫兄弟去问了,卧怂确实在闹白粉。饿现在告诉你,你是饿兄弟,咱不能跟闹白粉的人粘上。你肯定是不了解卧怂,现在你知道咧,就是干卧事的。你不能跟卧在一起啊。”段晓林迷着眼睛停了有将近半分钟,问道:
“卧怂真是闹白粉的?”“哥啥时办事不牢靠?”刘洪斌心里终于知道段晓林的意思了。他猜得不错,就是那回事情。现在他要失去段晓林这个朋友了,而且,麻达可能也要来了。
刘洪斌从段晓林再明显不过的明知故问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就是他段晓林跟白毅的生意有很深的瓜葛。他安排白毅进来无非有俩原因。一是洗钱。一旦白毅进来,他刘洪斌的场子就是白毅倒白粉的一个工具。二是段晓林和白毅有交易。在洗钱的同时,给白毅一些洗浴中心的干股,来换取倒白粉方面的一定份额。刘洪斌想,倒白粉的份额一定比白毅的两成干股还要大得多。白毅之所以愿意干,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段晓林能。
刘洪斌还知道段晓林心里知晓他心里想的是啥。白粉生意是敲头的买卖,既然他段晓林知晓你刘洪斌知道这事儿,那你刘洪斌就一定有麻达。刘洪斌尚不知道这麻达究竟有多大,他希望息事宁人。兄弟嘛,好聚好散。他那一瞬间有点儿难过,他先前的感觉不错,自己不过是段晓林耍的一杆枪而已。
“是这,你是当哥的有经历,”段晓林平静地言语道,“饿这个当弟的没经历,不管咋说,这事情要不这么办:你甭出干股给白毅了,饿自己出,饿一个人给他。你甭管,饿已经答应人家咧,这事不办不行。兄弟的为人你知道,饿说办的事一定得给人办。哥你甭说话,真的不用你拿份子!”刘洪斌知道段晓林不让他拿干股给白毅是真的,从这儿他知道段晓林在白粉上的份额一定比场子的干股多出好多。他也知道段晓林也有息事宁人的意思,就是你刘洪斌不用管任何事,只要让白毅进去就行,话说到这份上就是你继续维持你的现状,井水不犯河水。但同时也表达段晓林的另一强硬的立场,就是白毅非进去不可。
刘洪斌知道他现在有两条路好走。一是答应段晓林的条件,让白毅进去;二是不答应,这关系就掰啦,而这意味着某种危险。刘洪斌飞快地想了一下,他选择了后者。不管怎么样,只要他刘洪斌不闹白粉,掰是早晚的事儿。
“兄弟,哥不能看着你出啥事。”刘洪斌装成无限忠厚的样子看着段晓林说。
段晓林当下迷起眼睛和刘洪斌对视起来。俩人就这么看着足有一分钟,多少信息就这么通过眼波交流开来。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段晓林说:
“嗯,成。老哥你的好意兄弟心领了。兄弟回头跟卧说一声不干就是。这事到此为止咧,甭再提了。唉,对了,嫂子最近咋样?”刘洪斌又跟段晓林象亲兄弟一般聊了好一会儿别的事,象没事儿似的分手了。刘洪斌坐进车里定了神才开车上路。他得马上开始安排一些事情。他心里挺烦,这事情闹得不好。他知道段晓林现在决心要他的命。他得先去找夏处拉拉关系,市局省厅都得摆平;然后要召集手下的几个坚钢。他懂得一个道理,叫先下手为强。
陕西产麦子。农民种下的麦子到收获的时候自己割不过来就去雇人。慢慢地到秋收的时候就有一类人专门给人受雇去割麦子。种麦子的管这些人叫麦客。麦客通常手里只有一样工具----镰刀。
道上管杀手叫麦客,因为他们用刀杀人。而杀人割脑袋叫割麦穗。
刘洪斌手下有个麦客就叫老麦。老麦有四条人命了,他是刘洪斌最坚钢的兄弟,一直在场子里头呆着混饭。刘洪斌知道现在是用他的时候了。他把其他有关事情安排妥当,就把老麦叫了过来。他要让老麦去割麦穗。而麦子就是段晓林。他给了老麦三天时间。他知道,夜长梦多。时间拖得越长,他自己越危险。
他本不用叮嘱老麦什么,老麦有经历,知道活儿应该怎么办。但他还是跟老麦说了句:
“小心。事一定要办利索。”他知道段晓林能。
到了第四天,也就是刘洪斌给老麦期限的最后一天,老麦托一个小闲人稍话给刘洪斌说晚上就办----刘洪斌安排老麦完了之后就再没跟他照面,也不用电话联系,他是个谨慎的人。他又约了市局刑侦一伙子晚上到场子里耍。这也是一种准备。
快到天亮了,场子里的客人差不多全走了。老麦托的那碎怂来了。刘洪斌心里一阵高兴。但脸上没显出什么,规矩上讲,这碎怂就是个捎话的,他什么也不知道。刘洪斌不能让这碎怂看出什么。
“刘哥,老麦说卧事情办成咧。”“噢。”“但老麦说右后轮跑坏咧,现在车坏半路上咧,让你拿钱去修理厂呢,就是南郊卧修理厂,老麦说你知道。”这话的意思是老麦事儿没办完全利索,自己右腿受伤了!刘洪斌心里有些懊恼。但他知道段晓林能,不好对付。“噢。坏得咋样?厉害不?”“老麦说还行,就是不能跑咧。”老麦伤得不轻,但没生命危险。刘洪斌打发这碎怂走了以后就开车回家了。他把车停好以后回屋换了件衣服又出来,到路边招了辆出租。他得去那秘密的避难处见见老麦。那地方隐蔽得很,南郊的一大片农民房。刘洪斌还不忘途中又换了两辆出租。他确实是个谨慎的人。
到了地方,刘洪斌看了下周围没人,掏出钥匙开了门进去。在厅堂里他没开灯,径直奔里屋去。里屋门边有个开关,他伸手摸到打开了。
里屋只有一张小床,老麦的两只脚穿着蓝球鞋露在外面,被子蒙着上半身。刘洪斌轻声叫老麦,走过去把被子掀开。
刘洪斌长这么大第一次被吓着了,他看不到老麦,老麦的脖子上面没有头,只有一滩污血洒在床单上。
老麦已经被人割了麦穗。
刘洪斌立即站起身,在他倏地转身的一刹那,从背后黑暗的厅堂里冲进一条汉子,用一根细钢丝从后面套住他的脖子。这汉子一用力,刘洪斌的手脚都麻了,他喊不出话来,钢丝已经嵌进肉里面去了。
刘洪斌本能地用手抠脖子上的钢丝,希望能把指头塞进去,但这是徒劳的。他的眼前一片发红,他眼底出血了。他不觉得疼,只觉得头很重。眼前由红变黑,眼球快掉出来了。随后他耳朵开始轰鸣起来。轰鸣中他隐隐约约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说:
“段晓林让饿割你的麦穗。”刘洪斌最后一个念头就是给卧狗日的碎怂骗了。然后,他身子瘫软下来,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刘洪斌和老麦的尸体半年后才被人发现。
夏威夷洗浴中心现在最大的股东是个叫白毅的。道上人说,是他割了刘洪斌的麦穗。
注:
饿,西安方言发音,意:我。
卧,西安方言发音,意:那,那人。
闲人,西安方言读作“寒人”。大闲人指黑道中大哥级人物。小闲人或闲人常指小流氓地痞。
麻达,西安方言。意:麻烦,事儿。
碎怂,西安方言,意:小屁孩子,小闲人。
撩粘,西安方言,意:倒霉,出事,坏事了。
(也是他写的)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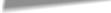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