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天才骑士, 和他的传奇人生 —— 王小波 大哥逝世六周年祭[转 |
| 一个天才骑士, 和他的传奇人生 —— 王小波 大哥逝世六周年祭.
作者 婉约 发表于: 4月11日 2:29
--------------------------------------------------------------------------------
一个崇尚理性、自由的思想启蒙者,一个坚持有趣的文学天才。
一位自由撰稿人,一位行吟诗人,一位自由思想家,
一个笔下调侃, 心中其实优雅的家伙.
一个顽童,也是一位忧郁骑士.
最后的骑士。
生活大抵是脆弱的,
其中的乐趣并不多。
可惜,有个人不能再提供这种乐趣了,他死了。
--------------------------------------------------------------------------------
斯 为 祭 。
--------------------------------------------------------------------------------
小波生平:
1952年5月13日
出生于北京。
1968~1970年
云南农场知青。这段经历成为他最著名的作品《黄金时代》的背景。
1971~1972年
山东牟平插队;后作民办教师。
1972~1973年
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工人。
1974~1978年
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工人。工人生活是他《革命时期的爱情》等小说的写作背景。
1977年
与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相识相恋,后结合。
1978~1982年
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学生。就读于贸易经济商品学专业。
1982~1984年
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教师。开始写作《黄金时代》。
1984~1988年
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生,获硕士学位。开始写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小说,其间得到许倬云先生的指点。
1988~1991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1991~1992年
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讲师。
1992~1997年
自由撰稿人。
1997年4月11日
逝世于北京(因心脏病突发?)。
其后,他的作品盛行于世。
--------------------------------------------------------------------------------
作品集:
http://member.netease.com/~opig/mute/wangtwo.htm
纪念网站:
http://www.wangxiaobo.com/
网上纪念馆:
http://cn.netor.com/a/wangxiaobo/index.asp?boardid=543
--------------------------------------------------------------------------------
以下转载,是几篇我个人喜欢的小波作品。
可惜,我最爱的《红拂夜奔》实在太长了。
——————————————————
这是我一个人的纪念。
不喜欢的人,请您另开新贴。勿在此跟贴。
谢谢 !!!
--------------------------------------------------------------------------------
愿您的思想在自由的天堂里飞翔。
《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
王小波作品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作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份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敲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兑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它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声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作“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全文完)
--------------------------------------------------------------------------------
《沉默的大多数》 之 《序》
王小波
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但这是后话——无论如何,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狂妄之辈,总是一种解毒剂。
萧翁说明辨是非难,是因为这些是非都在伦理的领域之内。俗话说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伦理问题虽难,但却不是不能讨论。罗素先生云,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考虑伦理问题时,想替每个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一得之见,然后说出自己的意见,把是非交付公论。讨论伦理问题时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这是我最近的体会;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动机。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马上我就要说到,这些傻子也不见得是真的傻,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久而久之,对中国人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前些时见到个外国人,他说: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在说“不”?这简直是把我们都当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气地答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认识的中国人都说“不”,但我不认识这样的人。这倒不是唬外国人,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
伦理(尤其是社会伦理)问题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我在这个领域里有话要说,首先就是:我要反对愚蠢。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做愚蠢。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假如乡下一位农妇养了五个傻儿子,既不会讲理,又不懂王法,就会和人打架,这家人就能得点便宜。聪明人也能看到这种便宜,而且装傻谁不会呢——所以装傻就成为一种风气。我也可以写装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写过的——“文革”里谁没写过批判稿呢。但装傻是要不得的,装开了头就不好收拾,只好装到底,最后弄假成真。我知道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某人“文革”里装傻写批判稿,原本是想搞点小好处,谁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了风云人物。到了这一步,我也不知他是真傻假傻了。再以后就被人整成了“三种人”。到了这个地步,就只好装下去了,真傻犯错误处理还能轻些呀。
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的发现,是萧伯纳告诉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个假痴不癫的杜特立尔先生。息教授问:你是恶棍还是傻瓜?这就是问: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两样都有点,先生,凡人两样都得有点呀。在我身上,后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讨厌装傻,渴望变聪明。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
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到,这可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人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在萧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谢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话都编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这话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力,他已经不战而胜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全文完)
--------------------------------------------------------------------------------
《理想国与哲人王》
王小波
罗素先生评价柏拉图的《理想国》时说,这篇作品有一个蓝本,是斯巴达和它的立法者莱库格斯。我以为,对于柏拉图来说,这是一道绝命杀手。假如《理想国》没有蓝本,起码柏拉图的想象力值得佩服。现在我们只好去佩服莱库格斯,但他是个传说人物,真有假有尚存疑问。由此所得的结论是:《理想国》和它的作者都不值得佩服。当然,到底罗素先生有没有这样阴毒,还可以存疑。罗素又说,无数青年读了这类著作,燃烧起雄心,要做一个莱库格斯或者哲人王。只可惜,对权势的爱好,使人一再误入歧途。顺便说一句,在理想国里,是由哲学家来治国的。倘若是巫师来治国,那些青年就要想做巫师王了。我很喜欢这个论点。我哥哥有一位同学,他在“文化革命”里读了几本哲学书,就穿上了一件蓝布大褂,手里掂着红蓝铅笔,在屋里踱来踱去,看着墙上一幅世界地图,考虑起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了。这位兄长大概是想要做世界的哲人王,很显然,他是误入歧途了,因为没听说有哪个中国人做了全世界的哲人王。
自柏拉图以降,即便不提哲人王,起码也有不少西方知识分子想当莱库格斯。这就是说,想要设计一整套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让大家在其中幸福地生活;其中最有名的设计,大概要算摩尔爵士的《乌托邦》。罗素先生对《乌托邦》的评价也很低,主要是讨厌那些繁琐的规定。罗素以为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把什么都规定了就无幸福可言。作为经历了某种“乌托邦”的人,我认为这个罪状太过轻微。因为在乌托邦内,对什么是幸福都有规定,比如:“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在乌托邦里,很难找到感觉自己不幸福的人,大伙只是傻愣愣的,感觉不大自在。以我个人为例,假如在七十年代,我能说出罗素先生那样充满了智慧的话语,那我对自己的智力状况就很满意,不再抱怨什么。实际上,我除了活着怪没劲之外,什么都说不出来。
本文的主旨不是劝人不要做莱库格斯或哲人王。照我看,这是个兴趣问题,劝也是没有用的。有些人喜欢这种角色,比如说,我哥哥的那位同学;有人不喜欢这种角色,比如说,我。这是两种不同的人。这两类人凑在一起时,就会起一种很特别的分歧。据说,人脖子上有一道纹路,旧时刽子手砍人,就从这里下刀,可以干净利索地切下脑袋。出于职业习惯,刽子手遇到不认识的人,就要打量他脖子上的纹,想象这个活怎么来做;而被打量的人总是觉得不舒服。我认为,对于敬业的刽子手,提倡出门时戴个墨镜是恰当的,但这已是题外之语。想象几个刽子手在一起互相打量,虽然是很有趣的图景,但不大可能发生,因为谢天谢地,干这行的人绝不会有这么多。我想用刽子手比喻喜欢、并且想当哲人王的人,用被打量的人比喻不喜欢而且反对哲人王的人。这个例子虽然有点不合适,但我也想不到更好的例子。另外,我是写小说的,我的风格是黑色幽默,所以我不觉得举这个例子很不恰当。举这个例子不是想表示我对哲人王深恶痛绝,而是想说明一下“被打量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众所周知,哲人王降临人世,是要带来一套新的价值观、伦理准则和生活方式。假如他来了的话,我就没有理由想象自己可以置身于事外。这就意味着我要发生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而要变成个什么,自己却一无所知。如果说还有比死更可怕的事,恐怕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原故,知道有人想当哲人王,我就觉得自己被打量着。
我知道,这哲人王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他必须是品格高洁之士,而且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在此我举中国古代的哲人王为例——这只是为了举例方便,毫无影射之意——孔子是圣人,也很有学问。夏礼、周礼他老人家都能言之。但假如他来打量我,我就要抱怨说:甭管您会什么礼,千万别来打量我。再举孟子为例,他老人家善养浩然之气,显然是品行高洁,但我也要抱怨道:您养正气是您的事,打量我干什么?这两位老人家的学养再好,总不能构成侵犯我的理由。特别是,假如学养的目的是要打量人的话,我对这种学养的性质是很有看法的。比方说,朱熹老夫子格物、致知,最后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本人不姓朱,还可以免于被齐,被治和被平总是免不了的。假如这个逻辑可以成立,生活就是很不安全的。很可能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有一位我全然不认识的先生在努力地格、致,只要他功夫到家,不管我乐意不乐意,也不管他打算怎样下手,我都要被治和平,而且根本不知自己会被修理成什么模样。
就我所知,哲人王对人类的打算都在伦理道德方面。倘若他能在物质生活方面替我们打算周到,我倒会更喜欢他。假如能做到,他也不会被称为哲人王,而会被称为科学狂人。实际上,自从有了真正的科学,科学家表现得非常本分。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就是教人本分的学问,所以根本就没出过这种狂人。至于中国的传统学术,我就不敢这么说。起码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叫做“学而优则仕”,当然,若说学了它就会打量人,可能有点过分;但一听说它又出现了新的变种,我就有点紧张。国学主张学以致用,用在谁身上,可以不问自明——当然,这又是题外之语。
至于题内之语,还是我们为什么要怕哲人王的打量。照我看来,此君的可怕之处首先在于他的宏伟志向:人家考虑的问题是人类的未来,而我们只是人类的几十亿分之一,几乎可以说是不存在。《水浒传》的牢头禁子常对管下人犯说:你这厮只是俺手上的一个行货……一想到哲人王,我心中难免有种行货感。顺便说一句,有些话只有哲人才能说得出来,比如尼采说:到女人那里去不要忘了带上鞭子。我要替女人说上一句:我们招谁惹谁了。至于这类疯话气派很大,我倒是承认的。总的来说,哲人王藐视人类,比牢头禁子有过之无不及。主张信任哲人王的人会说:只有藐视人类的人才能给人类带来更大利益。我又要说:只有这种人才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祸害。从常理来说,倘若有人把你当做了nothing,你又怎能信任他们?
哲人王的又一可怕之处,在于他的学问。在现代社会里,人人都有不懂的学问,科学上的结论不足以使人恐惧,因为这种结论是有证据和推导过程的,对于有理性的人,这些说法是你迟早会同意的那一种。而哲学上的结论就大不相同,有的结论你抵死也不会同意,因为既没有证据也没有推导,哲人王本人就是证明,而结论本身又往往非常的严重。举例来说,尼采先生的结论对一切非受虐狂的女性就很严重;就这句话而论,我倒希望他能活过来,说一句“我是开个玩笑”,然后再死掉。当然,我也盼着中国古代的圣人活过来,把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话收回一些。
我说哲人王的学问可怕,丝毫也不意味着对哲学的不敬。哲学不独有趣,还足以启迪智慧,“文化革命”里工农兵学哲学时说:哲学就是聪明学,我以为并不过分。若以为哲学里种种结论可以搬到生活里使用,恐怕就不尽然。下乡时常听老乡抱怨说:学了聪明学反而更笨,连地都不会种了。至于可以使人成王的哲学,我认为它可以使王者更聪明,老百姓更笨。罗素是个哲学家,他说:真正的伦理准则把人人同等看待。很显然,他的哲学不能使人成王。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像这样的哲学就能使人(首先是自己)成王。孔丘先生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子子孙孙都是衍圣公,他老人家果然成了个哲人王。
时值今日,还有人盼着出个哲人王,给他设计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好到其中去生活;因此就有人乐于做哲人王,只可惜这些现代的哲人王多半不是什么好东西,人民圣殿教的故事就是一例。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入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至于我自己,总觉得生活的准则。伦理的基础,都该是些可以自明的东西。假如有未明之处,我也盼望学者贤明的意见,只是这些学者应该像科学上的前辈那样以理服人,或者像苏格拉底那样,和我们进行平等的对话。假如像某些哲人那样讲出些晦涩、偏执的怪理,或者指天划地、口沫飞溅地做出若干武断的规定,那还不如让我自己多想想的好。不管怎么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
(全文完)
--------------------------------------------------------------------------------
以下是一些纪念文章。
--------------------------------------------------------------------------------
死得其所的人
[颜竣]
那天上午谈论的话题是扎伊尔的反政府武装、股金、某个自负而幽闭的诗人、阿香婆辣酱,以及余华的“我感到我写下了高尚的东西’。说笑间接到朋友的电话:“你知不知道?王小波去世了。”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那是一位从肉体到灵魂都高大、健康而且自由、坚定的人,他只有46岁,他的创造力正在一个无限宽广的世界中奔涌,据说他死于脑溢血,死在北京自己的寓所中,其时,正在写作。(此说法有误,见《宛如一曲美丽的歌》——编者注)这是一个太突然的休止符,也是他此生的终结。但我要说王小波是死得其所的人,他说过:“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正如战马死于沙场,落日熄灭于天空而歌声终止于喉咙一样,王小波用以写作的电脑还开着(此说同样有误。——编者注)。那一刻既是惊心动魄的壮烈,也是欣慰和幸运——这个美好事物的追求者在追求中获取幸福,即使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被平庸、愚蠢、病态、专制的事物所伤害。
也许很少有人读过他的小说《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2015》、《红拂夜奔》……但这并不妨碍王小波成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在贾平凹和苏童大红大紫的日子里,没有人想到这个从未介入“文学界”的写作者将会给叙事文学带来生动和智慧的革新,而那种健康、诚实、勇敢的精神在轻风般自在穿行的想象力当中燃烧着、闪耀着,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无法抗拒那样的魅力:唾弃庸常、虚假、病变的生活,转而相信并创造自然而不乏幽默的欢乐。
艾晓明在《羊城晚报》上说:“小波写了真正美好的爱情和性,写了他的人物如何地想要生活在一个可以创造发明,可以爱,可以探讨人的一切自由的可能性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永不到来。”
在花城出版社即将出版的84万字文集《时代三部曲》中,我们会读到许多个王二的不被污染、拘束的人生,哪怕他们被人群否定也决不放弃自己快乐的权力;在几篇奇妙的作品中,他虚构出几十年后的故事,像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但又充满卡尔维诺式的机智和王小波式的戏xue ;在那些古代与现代相互唱和的奇迹般的长篇小说中这位独立的思想者流露出坚定的抒情精神。
王小波对一切既定的虚伪规则、惯性思维和刻板道德的怀疑与蔑视,更广泛地体现在《南方周未》、《读书》、《三联生活周刊》上的许多随笔中。他只是一个满怀工作热情的个人主义者,但却是所有理想主义者的同盟;他敢于也善于解构一切神话:哪怕是戮破所有人都因之骄傲狂热的心理蜃景;他正视一切禁忌,包括同性恋话题和难得的健康的性爱;他是所有自欺欺人的酸腐知识分子、怀旧诗人、高烧的人文精神斗士和官僚和清教徒和中年色鬼的敌人,也是童心和人性的捍卫者。那些连他的随笔都没有读过的人真的是错过了,你们有没有被告知过:生活中有某些更重要的东西值得脱颖而出,被我们体验?
王小波生命的终止,是文字和文字之外的美好世界的又一次损失,然而与海子、骆一禾、胡宽或路遥、邹志安相比,他的死亡更真实,他不会因此被炒作、冠以种种虚妄的标签。这是一个死得其所的人,他相信现有一切美好的事物还可以更多的有,我也相信。那些已经被创造出来的美好事物会生长下去,召唤更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小波没有死于死亡,他只是回到了生命之中,像水回到水中。
1997年5月
--------------------------------------------------------------------------------
《 一块智慧的多米诺骨牌 》
连岳
对我来说,王小波的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在模仿他,他的文风、他的思维,然后到处推销他,就像被鬼上了身。我原来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后来发现,有一群数量众多的人被鬼上了身。他的风格如此易学,如此平易,以致在现在终于泛滥,然后就有人开始不满,开始反思。这当然是对的,但在这里,对于泛滥,我要说一些比他们更对的话。王小波风格的泛滥是件好事,就像米的泛滥一样,像奶酪的泛滥一样;由于有了米的泛滥,我们才有了营养和大便,由于有了奶酪的泛滥,我们才不怕别人动我们的奶酪。
王小波死的那一天,我正在一家地方报的办公室里写一些教育市民的评论,大意是反对不文明行为之类的东西,像绝大多数能写一点字和一点字都不能写的编辑记者一样,心里充满了得意和自豪感,对自己万分怜惜。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王小波死了。我的反应是:王小波是谁?
此后的两个月,我知道了他是谁,他写的东西并不多,但是足够证明我原来生活的形态与脑子是坏的。用王小波的话来说,我这个人是无趣的。用他喜欢的罗素的话来说,我这个人是假的。这种足够卑下的言语,是一种真实的描述,因为原来的生活足够卑下。可以举一个例子,这事几乎是我的耻辱,但我想还是应该在这里说出来。王小波死前大概一年左右,有一本狂热的民族主义著作《中国可以说不》在炒作,我是这种狂热气氛中的一员,我买了三本,一本送人,一本读,一本准备留着。如果当时有人塞给我一枚炸弹,让我去搞自杀式袭击,我一定就去了。我当时就是这样一只蠢猪。当然,是王小波告诉我这种蠢。也许我现在还是一只猪,但是至少不会狂热了,也多少看得出一些骗局了。
王小波说出来的东西,其实很少,也就是要有趣味,行文做人都要如此。他的趣味衡量标准,有一些逻辑实证主义,有一些经验主义,有一些基本的人文主义,但是他说得好,说得有清醒功能,破了很多迷惑和执著。因为这个世界总有很多人靠蛊惑达到目的,破蛊除惑的不二法门,就看看自己的经验能不能证实那些想法,要知道能不能亩产一万斤,最好的办法是自己种一亩田;有人说绝对服从是好的,就看看人类绝对服从的时期,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经验的获得,是要以我为主,以人为本的,一切维护人的本性的经验是好的,而一切违逆人的本性的经验是坏的,我们要以好的经验来指导判断,而拒绝坏的经验在现实中重演;因为人也是会被自己的经验骗的,有时候会形成集体癫狂,认为受虐式的极端体验是好的,这时候要有一点特立独行,相信自己的判断。
这些观念,有人认为,应该在成年礼之前完全掌握,可是我到了27岁才被它们吓一跳,我想,有我懒的原因,有视野不够开阔的原因,但是更说明这些东西曾是稀缺的,不能轻易接触到。幸好,现在它不那么稀少了,在这点上,我觉得有时候人的进步是很快的,人在思想上的幸福程度能迅速提升。王小波说的是常识,这并不能降低他的地位,把常识说得好,反而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启蒙,重要的思想,只有当它成为常识时,才更加重要。
王小波的文风应该是不难学到,他说到的常识拿来当谈资也是容易的,王小波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在实践这些常识。他看到的无趣,许多人当然也看得到,不仅看得到,还感受得到,但只是日复一日地抱怨而已,绝不敢离这无趣半步,种种无趣给了他们些许供养以及若干期权。抱怨和痛苦是希望别人改变,是希望世界一日内整体向好;其实,只是将自己的懦弱与无能合理化而已。而这种举措正是无趣的最大组成部分,像吞噬自己尾巴的蛇,最终只能打成一个死结,没有出路。王小波是从自己远离无趣开始,不惜冒再大的风险,也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自主的人,过自己想过的日子。等待世界的改变,要一万年,自己改变,明天就行了。从王小波后,每晚都有个机会等着我们,只是看自己的智慧够不够,勇气够不够,这当然败坏了我们原来固定不移的生活,使人痛苦不堪地取舍,但毕竟有了思考自己命运的习惯。大多数人想想而已,可也有不少人走出来了。王小波的行为比王小波的文字更具独特性,我想,这点是应该说明的,许多学了王小波文字的人,却完全没有他的行动性,有人像王小波一样行动,却是不写字的,这种沉默行为更具有美感,更王小波。
这几年,我知道许多人爱王小波的人一并接受了王小波喜欢的人,罗素、福柯、杜拉斯、马克·吐温、杜伦马特、卡尔维诺、王道乾、伍迪·艾伦、图尼埃,这些人都比王小波更了不得,更具诱惑力,任何一个都有足够的爆炸力,给坚固的无趣以震撼,至少,能给一个嘲笑。王小波只是最轻的一块多米诺骨牌,但它是第一块推倒的,引起了连串的倒塌,传递和放大了力。
王小波性命的结束,这个惊吓给了许多人慧命。佛家有言,害人性命还可谅,害人慧命不可谅。慧命如此重要,所以,他的死是值得的。
原文2002.4.11发表于 南方周末
--------------------------------------------------------------------------------
《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悼小波
[李银河]
日本人爱把人生喻为樱花,盛开了,很短暂,然后就调谢了。小波的生命就像樱花,盛开了,很短暂,然后就磕然凋谢了。
三岛由纪夫在《天人五衰》中写过一个轮回的生命,每到18岁就死去,投胎到另一个生命里。这样,人就永远活在他最美好的日子里。他不用等到牙齿掉了、头发白了,人变丑了,就悄然逝去。小波就是这样,在他精神之美的巅峰期与世长辞。
在我心目中,小波是一位浪漫骑士,一位行吟诗人,一位自由思想家。
小波这个人非常的浪漫。我认识他之初,他就爱自称为“愁容骑士”,这是堂吉诃德的别号。小波生性相当抑郁,抑郁既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生存方式;而同时,他又非常非常的浪漫。
我是在1977年初与他相识的。在见到他这个人之前,先从朋友那里看到了他手写的小说。小说写在一个很大的本子上。那时他的文笔还很稚嫩,但是一种掩不住的才气已经跳动在字里行间。我当时一读之下,就有一种心弦被拨动的感觉,心想:这个人和我早晚会有点什么关系。我想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缘份吧。
我第一次和他单独见面是在《光明日报》社,那时我大学刚毕业,在那儿当个小编辑。我们聊了没多久,他突然问:“你有朋友没有?”我当时正好没朋友,就如实相告。他单刀直入地问了一句:“你看我怎么样?”我当时的震惊和意外可想而知。他就是这么浪漫,率情率性。
后来我们就开始通信和交往。他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他的第一句活是这样写的:“作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抵挡如此的诗意,如此的纯情。被爱已经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而这种幸福与得到一种浪漫的骑士之爱相比又逊色许多。
我们俩都不是什么美男美女,可是心灵和智力上有种难以言传的吸引力。我起初怀疑,一对不美的人的恋爱能是美的吗?后来的事实证明,两颗相爱的心在一起可以是美的。我们爱得那么深。他说过的一些话我总是忘不了。比如他说:“我和你就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这形像的天真无邪和纯真诗意令我感动不已。再如他有一次说:“我发现有的人是无价之宝。”他这个“无价之宝”让我感动极了。这不是一般的甜言蜜语。如果一个男人真的把你看作是无价之宝,你能不爱他吗?
我有时常常自问,我究竟有何德何能,上帝会给我小波这样一件美好的礼物呢?去年10月10日我去英国,在机场临分别时,我们虽然不敢太放肆,在公众场合接吻,但他用劲搂了我肩膀一下作为道别,那种真情流露是世间任何事都不可比拟的。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他转身向外走时,我看着他高大的背影,在那儿默默流了一会儿泪,没想到这就是他给我留下的最后一个背影。
小波虽然不写诗,只写小说随笔,但是他喜欢把自己称为诗人,行吟诗人。其实他喜欢韵律,有学过诗的人说,他的小说你仔细看,好多地方有韵。我记忆中小波的小说中唯一写过的一行诗是在《三十而立》里:“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我认为写得很不错。这诗原来还有很多行,被他划掉了,只保留了发表的这一句。小波虽然写小说和随笔为主,但在我心中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的身上充满诗意,他的生命就是一首诗。
恋爱时他告诉我,16岁他在云南,常常夜里爬起来,借着月光用蓝墨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呀写,写了涂,涂了写,直到整面镜子变成蓝色。从那时起,那个充满诗意的少年,云南山寨中皎洁的月光和那面涂成蓝色的镜子,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从我的鉴赏力看,小波的小说文学价值很高。他的《黄金时代》和《未来世界》两次获联合报文学大奖,他的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成为1997年嘎纳国际电影节入围作品,使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为中国拿到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如果诺贝尔文学奖将来有中国人能得,小波就是一个有这种潜力的人。我不认为这是溢美之辞。虽然也许其中有我特别偏爱的成分。
小波的文学眼光极高,他很少夸别人的东西。我听他夸过的人有马克·吐温和萧伯纳。这两位都以幽默睿智著称。他喜欢的作家还有法国的新小说派,杜拉斯·图尼埃尔,尤瑟纳尔,卡尔维诺和伯尔。他不喜欢托尔斯泰,大概觉得他的古典现实主义太乏味,尤其受不了他的宗教说教。小波是个完全彻底的异教徒,他喜欢所有有趣的、飞扬的东西,他的文学就是想超越平淡乏味的现实生活。他特别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真即是美”的文学理论,并且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认为真实的不可能是美的,只有创造出来的东西和想像力的世界才可能是美的。他有很多文论都精辟之至,平常聊天时说出来,我一听老要接一句:不行,我得把你这个文论记下来。可是由于懒惰从来没真记下来过,这将是我终身的遗憾。
小波的文字极有特色。就像帕瓦罗蒂一张嘴,不用报名,你就知道这是帕瓦罗蒂,胡里奥一唱你就知道是胡里奥一样,小波的文字也是这样,你一看就知道出自他的手笔。台湾李敖说过,他是中国白话文第一把手,不知道他看了王小波的文字还会不会这么说。真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有人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只出理论家、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和意识形态专家,不出思想家,而在我看来,小波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读过他文章的人可能会发现,他特别爱引证罗素,这就是所谓气味相投吧。他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我对他的思想老有一种意外惊喜的感觉。这就是因为我们长这么大,满耳听的不是些陈词滥调,就是些蠢话傻话,而小波的思路却总是那么清新。这是一个他最让人感到神秘的地方。我分析这和儿时他的家庭受过挫折有关。这一遭遇使他从很小就学着用自己的判断力来找寻真理,他就找到了自由人文主义,并终身保持着对自由和理性的信念。
小波在一篇小说里说:人就像一本书,你要挑一本好看的书来看。我觉得我生命中最大的收获和幸运就是,我挑了小波这本书来看。我从1977年认识他,至1997年与他永别,这20年间我看了一本最美好、最有趣、最好看的书。作为他的妻子,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失去了他,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小波,你太残酷了,你潇洒地走了,把无尽的痛苦留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虽然后面的篇章再也看不到了,但是我还会反反复复地看这20年。这20年永远活在我心里。我相信,小波也会通过他留下的作品活在许多人的心里。
樱花虽然凋谢了,但它毕竟灿烂地盛开过。
我最最亲爱的小波,再见,我们来世再见。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再也不分开了。
1997年4月15日于北京
--------------------------------------------------------------------------------
小波写了真正美好的爱情和性.
写了他的人物如何地想要生活在一个 可以创造发明,可以爱,可以优雅,可以有趣,可以探讨人的一切自由的可能性的时代.
而这个时代,
永不到来。
阿冒 回复于:4月11日 8:44 删除 隐藏IP
--------------------------------------------------------------------------------
王小波先生最大的优点是
他是一个未被这个世界污染的人!
签名档:
葫芦 回复于:4月11日 9:14 删除 隐藏IP
--------------------------------------------------------------------------------
up
也贴一篇偶喜欢的
《欣赏经典》
王小波
有个美国外交官,二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呆了十年。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看过三百遍《天鹅湖》。即使在芭蕾舞剧中《天鹅湖》是无可争辩的经典之作,看三百遍也太多了,但身为外交官,有些应酬是推不掉的,所以这个戏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看,看到后来很有点吃不消。我猜想,头几十次去看《天鹅湖》,这个美国人听到的是柴科夫斯基优美的音乐,看到的是前苏联艺术家优美的表演,此人认真地欣赏着,不时热烈地鼓掌。看到一百遍之后,观感就会有所不同,此时他只能听到一些乐器在响着,看到一些人在舞台上跑动,自己也变成木木痴痴的了。看到二百遍之后,观感又会有所不同。音乐一响,大幕拉开,他眼前是一片白色的虚空——他被这个戏魇住了。此时他两眼发直,脸上挂着呆滞的傻笑,像一条冬眠的鳄鱼——松弛的肌肉支持不住下巴,就像冲上沙滩的登陆艇那样,他的嘴打开了,大滴大滴的哈喇子从嘴角滚落,掉在膝头。就这样如痴如醉,直到全剧演完,演员谢幕已毕,有人把舞台的电闸拉掉,他才觉得眼前一黑。这时他赶紧一个大嘴巴把自己打醒,回家去了。后来他拿到调令离开苏联时,如释重负地说道:这回可好了,可以不看《天鹅湖》了。
如你所知,该外交官看《天鹅湖》的情形都是我的猜测——说实在的,他流了哈喇子也不会写进回忆录里——但我以为,对一部作品不停地欣赏下去,就会遇到这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你听到的是音乐,看到的是舞蹈——简言之,你是在欣赏艺术。在第二个阶段,你听到一些声音,看到一些物体在移动,觉察到了一个熟悉的物理过程。在第三个阶段,你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最终体会到芭蕾舞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不过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而已。从艺术到科学再到哲学,这是个返璞归真的过程。一般人的欣赏总停留在第一阶段,但有些人的欣赏能达到第二阶段。比方说,在电影《霸王别姬》里,葛优扮演的戏霸就是这样责备一位演员:“别人的”霸王出台都走六步,你怎么走了四步?在实验室里,一位物理学家也会这样大惑不解地问一个物体:别的东西在真空里下落,加速度都是一个G,你怎么会是两个G?在实验室里,物理过程要有再现性,否则就不成其为科学,所以不能有以两个G下落的物体。艺术上的经典作品也应有再现性,比方说《天鹅湖》,这个舞剧的内容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为了让后人欣赏到前人创造的最好的东西。它只能照老样子一遍遍地演。
经典作品是好的,但看的次数不可太多。看的次数多了不能欣赏到艺术——就如《红楼梦》说饮茶:一杯为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就是饮驴了。当然,不管是品还是饮驴,都不过是物质存在的方式而已,在这个方面,没有高低之分……
“文化革命”里,我们只能看到八个样板戏。打开收音机是这些东西,看个电影也是这些东西。插队时,只要听到广播里音乐一响,不管轮到了沙奶奶还是李铁梅,我们张嘴就唱;不管是轮到了吴琼花还是洪常青,我们抬腿就跳。路边地头的水牛看到我们有此举动,怀疑对它有所不利,连忙扬起尾巴就逃。假如有人说我唱的跳的不够好,在感情上我还难以接受:这就是我的生活——换言之,是我存在的方式,我不过是嚷了一声,跳了一个高,有什么好不好的?打个比方来说,犁田的水牛在拔足狂奔时,总要把尾巴像面小旗子一样扬起来,从人的角度来看有点不雅,但它只会这种跑法。我在地头要活动一下筋骨,就是一个倒踢紫金冠——我就会这一种踢法,别的踢法我还不会哪。连这都要说不好,岂不是说,我该死掉?根据这种情形,我认为自己对八个样板戏的欣赏早已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欣赏的,但这些戏的艺术成就如何,我确实是不知道。莫斯科歌舞剧院演出的《天鹅湖》的艺术水平如何,那位美国外交官也不会知道。你要是问他这个问题,他只会傻呵呵地笑着,你说好,他也说好,你说不好,他也说不好……
在一生的黄金时代里,我们没有欣赏到别的东西,只看了八个戏。现在有人说,这些戏都是伟大的作品,应该列入经典作品之列,以便流传到千秋万代。这对我倒是种安慰——如前所述,这些戏到底有多好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信,但我也有点怀疑,怎么我碰到的全是经典?就说《红色娘子军》吧,作曲的杜鸣心先生显然是位优秀的作曲家,但他毕竟不是柴可夫斯基……芭蕾和京剧我不懂,但概率论我是懂的。这辈子碰上了八个戏,其中有两个是芭蕾舞剧,居然个个是经典,这种运气好得让人起疑。根据我的人生经验,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这种说法准不对,因为它是编出来自己骗自己的。当然,你要说它们都是经典,我也无法反对,因为对这些戏我早就失去了评判能力。
(全文完)
------------------------
一恨才人无行二恨红颜薄命,三恨江浪不息四恨世态炎冷,五恨月台易漏六恨兰叶多焦,七恨河豚甚毒八恨架花生刺,九恨夏夜有蚊十恨薜萝藏虺,十一恨未食败果十二恨天下无敌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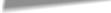 |
|
回帖 |
 |
|
| 回复人: |
亓官 |
Re:一个天才骑士, |
回复时间: |
2003.04.11 12:26 |
|
97年是我刚睁眼看世界的时候,97年先生去了。。。
先生再不会回来,而我却在我的黄金时代。。。。。
似水流年
|
|
|
| 回复人: |
子衿 |
Re:一个天才骑士, |
回复时间: |
2003.04.11 23:38 |
|
他72年开始写《黄金时代》,91年才正式发表,
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他的老婆李银河是位才女,更是他的红颜知己。
是旗士的军旗!
|
|
|
| 回复人: |
孙柳陌 |
Re:一个天才骑士, |
回复时间: |
2003.04.12 12:09 |
|
说不怕兔,不知为何一直就记得这四个字
|
|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