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苇子叶 |
[四]
知道一班长和王洪国谈恋爱的事情已经是两个月后了.
自从名单宣布以后,我和一班长之间好象多了一层什么,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感觉不多自然.
也许,这正应了那句话吧:冤家聚头.其实,对我而言,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因为从小到大,我是在"党气十足"的氛围里长大,妈妈是师部最有名的"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恐怕我没有记住的还有很多,而父亲却是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一身的"学究气",说起话来是"之乎者矣"不离前后,穿衣戴帽却是整整齐齐有眼有板.在我的家里,说了落后的话,要被妈妈批评,说了没有素养的话,要被爸爸斗争,而母亲和父亲,却是从我记事开始,就一直是"一国两治",一个是"永远的马列信徒",一个是"绝对清高自傲的老九",我也可谓是"千锤百炼"啊!因此,在我的眼里,他们就是时代的特殊产品,既典型又可笑.简直就是矛盾的统一!这样环境下,感觉自己看破了一切,所以,最喜欢的歌就是田震的"随其自然",最信仰的话就是"拿得起,放得下"了,平时是什么样子,现在该也是什么样子啊,却总看见一班长愁眉不展的,心里很为她难过.总希望为她做点什么.
"六月雪"这个词,在过去读书时一直以为是文人骚客玩味词眼的伎俩,如今,在五道梁,却真正地感受到了它的存在.我们的宿舍是三排平房,四周围了一圈围墙,有一人多高.围墙上都扎了好多碎玻璃片,从院子里朝外看,只能看见远处的山顶上有大多大多的云,淡有淡无的飘着,山上泛着银色的光,视线所到之处感觉寒意彻骨.站在窗子前的我,忽然感觉身上凉飕飕的,哦,六月的天真像孩子的脸啊,说变就变了,下雪了,不一会儿工夫,雪花漫天飞舞,天色也一下子变得阴暗,我们几个半大丫头,都像看稀罕似的挤到窗前,看这过去只在书上见过的景致.
"哦,副班,原来是真有其事啊."小吴酣态可掬地嚷到.
我转过头去,朝她笑笑,说:"我也是今天才看见呢!"
"多怪撒,在我们四川,现在可已经是穿起超短窑裤,那天气可是热死人啊."川妹子姚军大嗓门一叫,大家都不做声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知道是谁先发出的抽泣声,什么也没有说,几个人都开始哭了,我的眼睛也忍不住含满了泪.想起远在他乡的亲人,想起读书时的伙伴,还想起了那霓虹四射的街道,我的心和大家一样,有着太多的苦涩.生活是时间的延续,更是热爱它的人们的奋斗和创造.来到机务连后,我们由开始的惶恐到现在甘于枯燥寂寞,这中间不知道落了多少泪,不知道熬了多少个不眠夜啊.
天还没有亮,就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我侧耳倾听,只听见"嘁嘁嚓嚓"的声音,起身,穿上军大衣,踏上拖鞋,来到门口,支起耳朵听了听,还是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悄悄拉开门,伸头出去,只见走廊尽头,站着一班长手下的几个女兵,都聚集在机房门口,我略加思考了一下,就轻轻地走了过去,只见她们都向我投来不太善意的眼神,我很诧异,忧郁了片刻,还是没有忍住:
"怎么了?一班长呢?"
"......."没有人回我的话.大家的眼神里流露出说不出的悲哀.
我的心禁不住抽了一下,"说啊,出了什么事?"声音似乎很大.没有控制住自己.
一个个子不高,脸圆圆的女兵走了出来,站在我面前说:
"一班长....她...喝了很多酒....."
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抑制住自己,问道"
"她人呢?快告诉我!"
"在她房间里."
我转身就往二楼跑去.连里是一个班住了一层.男兵全在一楼.女兵被保护在上面两个楼层里.
一班长的房间在二楼的第二间,里面收拾的很整齐,床单是白色的,军草绿的被子叠得很有型,墙上挂了一支长笛,那是她平时吹来玩的,我们常常可以听见她的笛声.刚来这里第一次听见时,我还惊讶在这个旷古异域,还能听见这如此美妙的旋律.每当她吹"流浪歌",总会有老兵小新兵跟着哼哼,总会把大家都吹的心里酸揪揪的.
一班长是个湖南妹子,留海齐齐地挂在额前,双眼皮,凤眼,细高鼻梁,标准的樱桃小口,一笑起来,说心里话,只怕连我们这些女孩子都会有三分嫉意.平时,我们俩在楼上楼下遇见,也不过是点头招呼而已.可能彼此间的感觉相似吧,都对对方感觉比较特别.
我攒足了劲把她抱到床上,她脸色非红,双眼皮叠在一起,感觉像个醉酒的睡美人一样,虽然没有明白她为什么这样做,但,我想她一定有说不出的苦衷,才会如此.给她脱了鞋,脱了袜子,脱了外套,用被子盖住她的身子,让紧随而来的她的兵去找通讯员要了两壶开水,给她把脚轻轻地擦了擦,把被角掖好,又在床头柜上倒了一杯开水,把洗脸毛巾在热水里泡了泡,然后拧得半干,折好铺在她的额上.渐渐地,听见了她均匀地呼吸声.吩咐了一个新兵看护她.起身要离开时,才看见自己还没有穿戴整齐.赶紧赶上三楼
再见到一班长时,已经是四天后了,晚饭后,她约我出去走走.我欣然前往.
[待续]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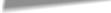 |
|
回帖 |
 |
|
| 回复人: |
苇子叶 |
Re:苇子叶 |
回复时间: |
2004.01.08 01:15 |
|
[五]
如血的晚霞,照着五道梁的四周.我和一班长并排走着,开始的几分钟似乎有点尴尬.大家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或者说该怎么说,北方长大的我受不了这样的场面,率先开口说了话.
"那天怎么喝成那样啊?"我尽量轻声地问着,怕不小心就把她问哭.她在我的心里是那样的神秘.也是那样的娇弱.
话还没有说呢,眼眶却已是泪了."方苇,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和你说这事情的啊."
"和我说?我能帮你吗?"我很诧异,我们之前确实没有过多的接触,怎么会想着对我说呢?
"第二天,我酒醒后,班里人给我说了你照顾我的经过,听后我哭了!我想,长这么大,除了父母,还没有人对我这样好,所以,我想和你说话,想让你和我做好朋友."她那湖南口音,软软嘤嘤,如丝还轻,莫说是我,换了任何一个人,谁又舍得拒绝呢!我边听她说话,边看着她,晚霞浅浅红红地照着她,黑色的睫毛上泛着亮泽,小巧的嘴唇周围有一层细柔的绒毛,眼神中充满了神往.
我笑了,个子比她高一头的我刹那间感觉自己像个勇士,真的,是这样."瞧你说的,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啊!你还是我的领导呢."说完,我狡猾地看着她笑.
她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举起小拳头,朝我身上砸来."哎呀,你怎么这样坏啊?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不是你听见的那样嘛."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是朋友了,你该告诉我啊."
"是他先来找我的,我可没有往那方面想啊."她说的时候,脸上的红晕闪闪的.
"他是谁啊?你说清楚啊."我们俩早已经变成了疯丫头,在沙土里互相追赶着.闹成一团.
机务连和兵站紧紧挨着,泵站和我们相隔还有大概十分种的路程.一里外的公路两边,散散地住着二三十户人家,大多数是唐古拉乡的牧民,也有一部分外地来的做生意的人,真正意义上的"来自五湖四海",有河南的面馆,山东的饺子馆,四川的川菜馆,还有青海甘肃的牛羊肉粉汤馆.最可笑的就是每家馆子都带有住宿,加油还有娱乐等服务项目.用军营里常常戏说的话就是:一条龙服务.我们女兵是很少进这些地方的,一般情况下都是男兵进,本来嘛,每天的三班倒就已经够意思了,谁还愿意出来这样"风吹沙磨"啊.除了值班,我们更多的时间就是细心地伺候自己的手和脸了.
我们俩来到了兵站背后的一个小山坡上,满地石子,沙土,还有土里若隐若现的动物们的遗留物.我们转来转去地寻找大点的石块,总算坐下了,面对山下蜿蜒如龙的青藏公路,心底不由得升腾起一股悲壮.
"苇子,给你说吧,我是很喜欢他,可我也怕他."一班长将头靠在我的肩上,我也顺势把脑袋歪过去,和她的头在一起挤着,我们偎着.
"为什么?"我情不自禁地皱起了眉头.
"和他在一起,是宣布预选名单后的事情了,那是我从格尔木学习回来,和他正好坐一趟班车,上下车都是他帮我提行李,我晕车,也是他照顾我的,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受不得别人的好的,回连后,我去谢他,一起说了很久的话,就这样开始了."她说的很简单,说得很累.我听得出来她的累.
"那为什么又要喝酒想醉呢?"紧跟她的问题我继续话题.
她咬着嘴唇,半天都不开腔,我等了一会,用身子碰了碰她,松开被咬得乌青的嘴唇,她说:
"'他花心!"我的脑子一下子懵了,没有想到.
"怎么啦?你倒是一下子说完啊,别这样折磨人嘛."我感觉自己的血液在升腾.
一班长不紧不慢地说:"那天,我值班,刚好接到一个长途,是个女的打来的,是找王出纳的,我问她是谁,她说她是出纳的妻子,我说你搞错了没有啊?那个女的骄横地说,这话也有开玩笑的吗?倒问得我哑口无言.我要她稍微等一下,等我去叫.让班里人叫来了他,大家都让到了隔壁,我很注意地听值班室的动静,一会儿就听见大声吵闹的声音.当时,心里的滋味你该想得到,我想到了死......"她的手上紧紧地握着一块山石.手指上的骨节凹凸毕显,我心理有说不出的难受.
"后来,他找我,说要给我解释,我已经没有勇气再见他了,可毕竟,这是我喜欢的第一个人啊,我没有地方说,也不能给人说,我就打发班里的兵去买了一瓶沱曲,我独自在房间喝了还没有一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面的事情你都看见了."她出了一口长长的气,好象积攒了若干年一样.
"你倒是说话呀!我是不是不配做你的朋友啊?"一班长急切地推我的胳膊.
"这个败类!我早就看出来他不是个好东西."我眼神定定地看着远方.
一班长一脸狐疑,"啊?你早就发现了?说啊,你是怎么发现的?告诉我呀."
"这还不简单啊:你瞧他看人那眼睛,那表情,那哈腰的动作,第一眼看见他,我就讨厌他.可在咱们部队里,这样的人是最吃香的,所以,我对很多事情看得很淡.你呢?"
"你说具体点,我不明白.他说,他可以帮助我解决党票问题."
"这就对了,他就是这样给你放了饵啊!"我将一块半大的石头使劲地向山下扔去.
"以后我该怎么办?苇子!"她看着我,把我迷惑得以为自己是个仙儿似的.
我把她额前的头发捋了捋,让那些飘在前面的发丝齐齐地藏在耳后."别理他!记住,你是一个女兵!"
高原的天气,是多变的,是预料不及的.特别是夏季.每天几乎都有一个多层次的景致:雪花一阵,雷声一阵,冰雹一阵,尘风一阵......此时的晚霞,早已像捉迷藏似的,时而露出脑袋,时而躲进苍穹,已经没有了刚才出来时的暖意,更多得感觉是凄寂,是酷寒.是一望无际的苍凉!
我们准备下山,因为半山下连里院子里已经开始亮灯.
数着一根根散杆,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不自觉地把衣领竖起,想得到一丝温暖,俩人的手情不自禁地紧握着,山路上高低不一,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朝营房走去.
路过兵站大门时,看门的藏工格图告诉我们,连里来人了,是兵站部文工队来联欢的.三站同欢.
哦,我们这才想起,"七一"快到了!摸了摸围着我们直嗅的藏狗的脑袋,给格图再见后,我们回到了连队.
[未完待续]
|
|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