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呼吸,向前看 |
深呼吸,向前看
一,
我住的这间楼房在二楼的最西边,山墙开了一个一平米多一点的窗户。涂了一层厚厚蓝色油漆的窗台后面是一张桌子,我在桌子的后面,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坐着的,坐在一台轮椅上面。我能够看见的窗外景物是这样的:一个很规矩的长方形院子。北边是一幢四层楼,估计原来的墙体应该是白色的。现在二层以上长了牛皮癣,墙皮掉的挺热闹,如果你有自以为足够的艺术细胞和多得用手捋的时间,你会在那墙体之上发现超现实主义或抽象主义什么的作品,比如我,总是在里面发现惊喜。二层以下的墙体成了童话世界那些夸张人物粉墨登场的地方,打了补丁的红裙子脸上长者雀斑的白雪公主怎么看都透着一股凄惨。东面的墙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和我的窗户隔了一条胡同,胡同里面除了上下班的时候塞满了自行车的铃声其余的时间大都和我一样沉默不语。西面的那堵墙我最喜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经常一眼不眨,一看就是半天。我喜欢这堵墙表面原因是因为它的上面爬满了绿色植物,整整一面墙的绿,一个夏天总不会让你失望的热热闹闹地开满了紫色蓝色黄色的小喇叭。当然这是表面原因,我说了。至于深层原因之一是由于在我透过窗口目力所及的范围它是距离我最远的景物。距离总是起到发酵粉的作用,给你一个虚腾腾的白面馒头。至于深层的原因之二,我会在下文介绍,当然前提是你幸运地能够读下去。下面我该说说院子中间了。院子当间最高的是脱了油漆的木制滑梯,被小屁股磨得锃亮锃亮的。两个跷跷板,三个旋转木马在白雪公主的裙子边上。如果我估计没错的话,在东墙这边应该还有一排秋千,我这么有把握的估计是因为:我会在每天的固定时间比如早晨比如傍晚看到起起落落的小脚丫子和大拇指粗细的铁链子。我想你已经知道了,这个院子是个幼儿园。没错,是个我窗户里面的幼儿园。托领导们的福,我住的这幢破楼还轮不到它动迁,所以我二十多年来除了睡觉的时候以外可以时时刻刻地看着她。打个肉麻点的比喻,我跟我的亲密情人热乎了二十多年了。
接到女朋友信的时候我正在跟我的幼儿园情人热乎,现在正是夏天,她最温柔的时候。满院子的童声小合唱,每天早晨八点之前。我没有读过幼儿园,猜不出在那栋长满了牛皮癣的楼房里面有什么吓人的怪物,可以让那些粉红的小脸蛋在看见大门之后花容失色。我津津有味地看着一个剃光头的小小子坠着小屁股在楼门前打阵地战,死活不肯前进一步。旁边那位一脑门子的汗,估计是小光头他爹,但是他没剃光头戴眼镜不知道我猜得准不准。白色的信封放在桌子上一点都不像不祥之兆,女人真是猜不透,两个人天天见面写什么信嘛。我没拆信封,心里头正惦记着给眼镜两条建议:一条建议去做亲子鉴定,听说鉴定一把也不太贵。一条建议给小光头两巴掌,估计那肉敦敦的小屁股打过去手感应该不赖。不过我已经顾不上给眼镜出主意了,滑梯那边惊天动地的哭声着实吸引我,一天小小的离别可以让一个孩子哭得尿了裤子真让我琢磨不透,也许是孩子还没有学会习惯忍受,但是对他们而言反抗的武器可能只有哭声。我一直对进化论持有反动的怀疑态度,证据一,胡子一大把反抗的那点精气神都活没了。比如我。等院子里消停了,好像有点反应过来:这封信非比寻常。
我的女朋友文笔还是不赖的,比较容易地让我明白了信的中心思想,她说:我们在一起不合适,为了两个人都好,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刀两断。当然,她说的要比我叙述的委婉曲折得多,最后还一往情深地断言,我会找到更优秀的女人做我的女朋友。这话我信。算算书桌抽屉里的含泪告别这已经是我收到的第十九次衷心祝福。
把信装回信封,外面的院子里又开始热闹了。十来个东倒西歪的小不点拉着一根白绳上的塑料环,咿咿呀呀站着排,像极了一条花花绿绿的大蜈蚣,在院子里悠哉游哉。刚才嗓门最大的小光头看来忘了刚才那出戏,笑嘻嘻揪着前面娃娃的小辫子,情绪相当不错。人的某些东西很顽固地终其一生,比如健忘,无论是大人还是小人。有人说欢乐和痛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琢磨这句话快半辈子了,也许那枚硬币根本就不存在,也许硬币的两面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只有孩子们心里面一清二楚。人大了是越活越糊涂。
二,
院子里静悄悄的,看看天色还早,我拽过那个白色信封,打算写一篇和爱情无关的小说。主人公的名字一时还没想好,暂且就叫张三吧。
张三醒来的时候是夜里。
张三彻底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辆火车的硬板座椅上,三个人的座位张三要想躺下必须蜷着腿,所以腿麻麻的不很爽,并且窝了一身的臭汗。火车咣当咣当在黑漆漆的夜色里面很费力地突围,偶尔一闪而过的零星灯火让人感到有点风驰电掣的意思。张三坐起来敲敲腿,看看车厢头顶摇着脑袋的电扇色迷迷的昏黄灯光觉得很不对劲,或者说非常不正常。张三彻底被自己吓着了,一哆嗦光着脚丫子站到地上。半夜2点,科学家说,是人最困倦的时候,列车员同志都在打盹,所以满车厢的人没有人发觉张三在猛拍脑袋,一副精神不正常的样子。张三遇到天大的问题了,他想不起自己姓氏名谁,家住何方,或者没有家?为何跑到火车上睡大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张三忘了。用比较严肃的说法就是,张三得了失忆症。
一般来讲失忆症是由于精神或者头部,受到严重刺激或重击引起暂时或永久的失忆。张三是在火车上也就是旅行途中睡了一觉就把过去都忘光了,一干二净,什么都不记得。
张三拍自己的脑袋瓜子像拍块木头,没什么反应。张三拍累了就不再哆嗦,开始慢慢适应不知道自己是谁的这样一种现实。坐下来一扭头,看见座椅上一个黑色旅行包,被压得瘪瘪的哭丧着脸。张三得了失忆症但还比没变成白痴,稍微思考了那么几分钟就断定自己在失忆以前一定是枕着这个包睡着的。能让自己枕着睡觉的包一定是自己的,也许打开这个包就找着自己是谁了。张三这么想着一把拽过来打开。
张三很快知道什么是大失所望。从包里面翻出如下物品:白色睡袍一件,旧内衣一套(没闻到汗味),袜子两双(新的),毛巾一条,电动剃须刀一个(刀外面的网罩上有胡茬,肉眼观察和张三两腮的胡须质地相似),钥匙一串,水果刀一把,手纸一卷。后来张三又主动对自己进行搜身,缴获的物品有:香烟,打火机,钱包,火车票各一。张三满怀希望打开钱包,人民币若干,没发现任何人的照片,人民币上也没有一个手写汉字。张三口袋里的车票正面印有如下内容:起点到终点;k555次;座位号5车55座;2000年8月9日17:38开;全价299元;硬座特快;限乘当日当次车在2日内到有效。车票的背面是一句人人耳熟能详的只有天才才能心领神会的口号:人民铁路为人民。张三把自己折腾个够,有了重大发现:上车城市:起点市(或者镇),下车的地方叫:终点。张三的重大发现要是叫真的话和没发现也差不多,张三还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从起点上车不等于张三就是起点的人,到终点下车同样也不表示张三和那个叫终点的地方有什么亲密关系。张三抱着他的包真的傻了眼。
在张三努力寻找证据,证明自己是谁的的时候,车窗外黑色夜幕正慢慢退去。滚动着露珠的田野在烟雾里打蔫的小镇逐一闯进车窗又被迅急抛下,远处地平线冒出一个头的太阳忽隐忽现,在窗外一路跟随。车厢里慢慢变得喧闹。人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肯住嘴,只要清醒着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就要不停的讲话,这种观点我和张三是一致的,但我现在心情明显比他要好得多。张三现在很紧张。屏住了气留心前后左右,张三希望着自己的肩头被用力一拍,然后有一张笑脸或者哪怕一声不耐烦的吆喝:张三,醒了!然后,张三就可以找到被他忘记的过去时光。也就是说,张三正张着全身的毛孔等着有熟人朋友同事或者仇人都行能把自己认出来。
张三眯着眼装睡。
一阵全国人民都熟悉的音乐压倒了车厢里所有的声音,紧接着播音员高亢的声音不由分说的闯进每个人的耳膜。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播的都是大好形势鼓舞升平,播音员亢奋的语气让张三感到被喷了一脸的唾沫星子,张三的觉没法睡下去了。等了半个小时也没人来认领,张三觉得还是大大方方睁开眼睛算了。
三,
这时候的车厢就像一碟冬天的蚕茧,端到炉子边上,就是这样相似的情景,蠢蠢在动。坐着睡了一夜身体都乏得很,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像我一样中了大奖----一夜之间把过去忘个一干二净吧?张三一眼不眨地看着车厢里的人,其实在心里还是非常希望大家和他一样都中个大奖。张三的眼神很快就变得暗淡,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表明人家也中了奖。人家们都很有胃口在吃早饭,张三没有胃口,发现自己和人家不一样是多么应该郁郁寡欢的一件事。
“小伙子怎么不吃饭阿?觉睡多了吧,上车就开始睡”。和张三讲话的是坐在斜对面一个中年女人,手里一袋天津辣酱一根黄瓜。食欲旺盛看来人家也没中奖。张三在黄瓜的清香里经历着一喜一悲。喜的是终于有人和自己说话并且没有发现张三得了失忆症。悲的是听话头人家不认识他,想知道自己是谁还是个难题。张三拍拍肚子表示不饿,同时有些讨好地挂上一张笑脸打量着这个女人,张三希望女人继续说点什么,当然说的越多也好。让张三失望的是中年女人不肯再讲话,吃光了黄瓜又开始忙碌着泡方便面。张三咽了一口口水,如何搭话才能不让对方发觉自己的与众不同,要知道并不是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有机会中上这样的大奖,同样,让别人理解失忆症,也是一件要花上千言万语也不一定能解释明白的事。短发40多岁?皮肤暗淡没化妆,眼神看不出是坚定还是执拗,下嘴唇很性感,但总不能夸一个陌生女人说你的嘴唇很性感吧?张三的目光在中年女人身上转了一圈,最后放弃找话头和她搭讪的念头。张三把视线收回来自自然然地落到对面,然后再也不愿把眼睛挪开。于是对面座位上那个姑娘的身上就有一只鲜活乱爬的八脚虫子。
到这里,连我都猜到张三看上人家了。问题是人家能不能看上他呢?根据我的经验,感情是这个不大的世界里最最复杂麻烦的一件事。在我看来,世界上的所谓男人基本概括为两类: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呆在笼子里的兔子。两类的唯一区别在于对食物的动作取向。老虎是饿虎扑食,扑向它的美味。兔子是红着眼睛捧着它的大餐。我就是一只红眼睛的兔子。我的眼睛是这样红的:每一个经过我笼子的妙龄少女半老徐娘风烛老妪都让我眼膜充血,久而久之,我成了红眼睛的兔子。目前,截止到今天,已经有19位勇敢的姑娘送了我19把青草,我打心眼里感谢她们。
对了我得说说我是个干什么的。体面地讲我靠写字为生。但是明白人都知道在这个社会靠写字是无以为生的。写字没能给我带来白花花的经济效益,但也不是一点用处没有,比如19个可爱的姑娘。到目前为止,来到我笼子前面的都是可爱的女人。众所周知,兔子不会骗人,我对每一个送来青草的姑娘都说,我说我是个贫穷的瘫子。聪明点的“呀”的一声扭头就跑,脸上的表情就像刚刚踩了一堆狗屎。有一个傻姑娘,和我通了一年多的信我说我是个贫民瘫子,她说我真幽默。这个姑娘八成是言情小说看多了,脑子有点问题,听说过有人拿自己是瘫子开涮的么?见我诅咒发誓的,傻姑娘非要见面,我讲明白我的住址说你来自己开门吧。傻姑娘在开门的瞬间可能还在想象一个戏剧性的浪漫开头。不幸的是那天没能出现奇迹,她被屋子里的寒酸吓坏了。还不错到底是一个知道柏拉图的女人,尽管小脸蛋被吓的惨白,还是和我一起共进了午餐。可爱的傻姑娘吃饱了饭送给我一个美丽的祝福,然后像蒸汽一样消失了。
迄今为止给我最大一捆草的是我昨天的女朋友,她说她要嫁给我。她说的时候我正在看那面墙,那面墙上有什么好看的一会再讲。女朋友说我们结婚吧,我被吓坏了,吓得眼泪一个劲的流。看见我无比沉痛地摇头女朋友急了,逼问我爱不爱她。我又慌张点头。就这样我把自己弄到了一个死胡同。她的的逻辑是:如果我爱她就必须娶她。如果不娶她就是不爱她。我结结巴巴地告诉她,我是一只兔子,和我结婚只能成为兔子,不能再变成别的什么了,在我心里,我还是希望她能变成只老虎什么的。女朋友很明显没听懂,摔门就跑了,我们家房门到现在还缺块木板,由此可见此女有成为老虎的素质。这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摔门之后又发生了这样一幕,有一天她跑了来,告诉我她的思考成果:你是个虚伪的没用的卑鄙的兔子。后来我发觉我这个女朋友实在是具有老虎级的智商,她的这几个组合在一起形容词:虚伪的:没用的:卑鄙的,着实把我弄到一个迷宫里去了。以我的理解力,这几个词组单独在一起站着我很清楚它们的意思意义内涵外延,但是,麻烦在于,它们站在一起就成了一个难住我的迷宫。说实话,这九个汉字让我半年来几乎愁白了头发。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事实,让我的女朋友终于发现我真实的智商水平实在和她不是一个等级,于是我就收到了这封信。当然事实是怎样的我可能永远不清楚,唯一可以值得安慰的是清楚与否对结局无关紧要。我已经决定放弃这座迷宫,继续写我的小说。
四,
张三对面的姑娘还没醒。圆脸长发,有一绺头发垂下来盖住半边脸,那一只眼睛随着火车的摇晃好像故意撩人似的忽隐忽现,浓密的眼睫毛像一把小扇子,长裙,素花紧身上衣,丰满的胸部好像随时都可能挤出围栏露出无限春光,不盈一握的小腿此时无力的随着车厢摇晃。姑娘半倚半坐,上身和头部几乎全部靠在身边的那个男人身上,那个男人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脸上的小胡子很滑稽,稀疏和苞米须子一模一样的颜色。小胡子看样子好像也没醒,闭着眼睛靠着车窗。但是小胡子不时上下的喉节出卖了他。张三很快发觉小胡子在装睡并且在吃那个姑娘的豆腐。这个发现让张三很气愤,但是张三还拿不准姑娘和小胡子是什么关系,所以尽管心里和下边都胀胀的,也只能暗暗运气。那只八脚虫子上上下下在姑娘的身上爬了个遍也没把姑娘爬醒,当然那个小胡子也就一直那么僵硬地睡着。
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车厢里开始闷热,从早晨开始一直在喧哗的广播终于闭嘴。安静下来的闷热空气让人昏昏欲睡,张三不敢睡,他没指望能够睡一觉之后再把什么都想起来。张三忧虑的是,睡着了不一定还有什么特奖等着自己呢。张三很害怕睡觉,又没事可干,于是越来越发觉对面的姑娘好看。越看越觉得这个漂亮姑娘看着熟悉,张三就在心里期望着姑娘大梦醒来之后说自己是张三的女朋友。张三慢慢发觉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个发觉让他很愉快。
火车一声长鸣,开始减速,窗外的树木变得清晰。广播在娓娓告诉大家某某站到了,张三听清楚了不是他的“终点站”放下心来。随着火车猛地一顿对面姑娘的头用力一点醒了。广播里面那个声音还在喋喋不休,这时差不多车厢里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姑娘的惊叫,她到站了。张三目送着漂亮姑娘婀娜的身影被火车无情甩在后面,一时不知道该干什么好。这时候小胡子已经不再装睡,张三想起漂亮姑娘直到下车也没有看自己一眼,顿时觉得颇受打击,很想出去吸支烟。张三在口袋里发现一盒打开的香烟,想自己应该是会吸烟的,但是失忆这个大奖的获得,已经让张三变得小心谨慎,他害怕还会有什么奖突如其来砸到自己的脑袋上。出于谨慎的考虑,张三决定等一会新买一盒烟。
车厢里新上来几个乘客,顿时让一股陌生的气息在闷热的车厢里流动开来。大哥,有人么?一个姑娘指着张三身边的空座问张三。小胡子旁边也有空位,但是姑娘问的是张三,这个发现让张三觉得自己又中了奖,这个奖张三准备毫不推辞地接受。
姑娘坐下了,车厢里短暂的骚动像水面上被风搅起的涟漪很快平复。张三和所有的人都以为,这是一趟枯燥乏味的旅程。
五,
我已经被我的文字弄得快睁不开眼睛了,要休息一会。幼儿园的那面绿油油的墙是最好的休养生息之地,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我说了,我喜欢那面墙。到了夏天变得水灵灵的,这对一面墙来讲可不容易。这面墙的真正神奇之处不在于它的水灵灵,而是一直以来,这个一直可以延伸到我记事之初,从我第一次发现它上面可以出现变化不同的彩色图案,已经过去了20多年。只要你深吸一口气,这面墙就是一个可以随时随地放映的彩色宽银幕,上面有千变万化的花花世界。我一直以为这个宽银幕电影所有人都能看得见来着,就像每个视力正常的人可以看到月亮太阳。直到有一天,我发觉不是那么一回事。
那一天,我七八岁的样子,没心没肺地指着墙跟妈妈嚷嚷,看,楼下小红她爸和丹丹姐姐在光屁股亲嘴。我妈妈看看墙又看看我,然后一点没犹豫,她的带有葱花味道的大手就招呼了我的左边脸蛋子。捂着火辣辣的脸蛋我不知道自己又犯了什么错误,妈妈的一顿训斥让我终于开了窍。原来那面墙上演出的精彩画面他们看不到,所以她断定我是听了大人的什么议论也跟着乱嚼舌头。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讲别人的闲话是大人们的事业,我们小孩子才没有那个闲工夫。在我看来,那面墙又好看又有趣,比议论别人家的事好玩多了。事实表明,大人常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推己及人。比如现在我也长大了,用我现在的观点来推导,小光头为什么不愿意上幼儿园肯定是,一定是这孩子贪玩不爱学习。事实上小光头每天早晨和那个眼镜哭哭啼啼,仅仅是这个小家伙在和他喜欢的一个人玩他喜欢玩的一个游戏,而已,没有那么复杂。事实也表明大大人非常热衷于嚼舌头。在我挨了一个耳光之后不久,我在我们家不严实的门后听到妈妈和邻居马大娘神神秘秘地低语,没费什么力气我就听到了,丹丹姐姐去医院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结果丹丹姐姐的妈妈气得生了病。其实她们不需要那么神秘,我在那面绿墙上都看到了。我还看到其他一些画面:小红她爸爸坐在荒凉的铁轨上,在我的眼里,在落日下面只有他一个人的画面只能用荒凉来形容。后来又来了一大帮人,跟打架似的一哄而上,小红她爸被架走之后,一辆大火车很神气地喷着白烟飞驰而去。至于我看到的关于丹丹姐姐的画面,至今让我想起来心里还是酸酸的:那个地方是我从来没有见到的陌生环境,街道两边排列着我不认识的树,树上开着夸张的粉红色的花,树后面的房屋在一片水气里湿漉漉的,青砖青瓦看起来阴森森的吓人。丹丹姐姐跟着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男人走进了一幢青砖房子。
我说了关于这面墙的神奇,说给我的女朋友听,她皱着眉说我一肚子的男盗女娼。我很失望也很冤枉。看来这面墙只是我一个人的电影院,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我不能撒谎,很显然我的女朋友断言错了一个事实,我看到的不都是她嘴里的男盗女娼。比如现在,我看到下面的和离奇很近的画面,关于那趟让张三感到厌倦的列车,此时,这趟列车正奔驰在太阳耀眼的光芒之下,金光万道。
六,
张三旁边的姑娘很健谈,但是由于年轻不难看,所以张三并没有觉得她是让人讨厌的碎嘴子。身边有个爱讲话的漂亮姑娘,张三和姑娘已经变的很熟悉,这样的旅行也不是糟糕透顶,张三几乎忘了中了大奖这档子事,决定请姑娘吃午饭。午饭时间乘客似乎格外放松,为了配合气氛,广播里面悠扬的音乐适时的响起,卖食品的小推车在各个车厢穿梭,吆喝声此起彼伏很是热烈。列车行使在万道金光里面,一切都很美好平和,甚至一切都似乎在按部就班懒洋洋地进行着。一些出乎意料的变故常常没有预兆地降临,无常的大手此刻正不为人所觉地操纵着一切。
恐怖是突然降临的。
开始有非同寻常的声音从前面的车厢传过来,张三并没有注意,他的全部精神都在姑娘的身上,张三觉得姑娘吃饭的姿势真是优雅。随着乱哄哄的脚步声大量惊慌的人群开始拼命涌过来,个别人身上淌着平时难得一见的鲜血。出事了,所有人的本能是逃命,随着大多数人,到认为安全的地方去。可怜的是在一列火车之上,人们所认为安全的地方在前方,没有左右可选。张三意识到危险的时候整个车厢已经空空荡荡,过道里静悄悄地陈列着没有来得及穿上的鞋子开着口的旅行包,一片不可收拾的退败。张三试图跑到后一节车厢去,可是他在车厢连接处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在那里惊恐万状的人群已经挤满了整个过道,没有人可以再前进一步。
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也正也来越近,无疑那是恐怖的源头。
张三在洗手盆边上看到一双恐惧的眼睛,那个吃饭优雅的姑娘正在发抖。没有时间考虑张三拉过姑娘一起钻到了座位下面。绕过地上的一派狼籍张三看到一双熟悉的眼睛,是斜对面那个中年妇女。每个人伏在地上笑起来都能挺好看的吧?看见中年女人还能和自己笑,张三发觉自己的胳膊腿有点发软,挺没出息,张三想可不能让姑娘知道。
我想让一切都到此结束,可是出于对事实的尊重,我不得不继续,深呼吸,向前看。
突然,一阵孩子的哭声像一根火柴,点燃了就要爆炸的紧张空气,揪紧了所有人的心。一个摇摇晃晃的身影,野兽样的嚎叫,手里的刀在正午的阳光下面狰狞跋扈。
孩子的腿被一辆翻倒的食品手推车压住。刀锋已经迷乱,所有人闭上眼睛。
一个身体从座位下面冲了出来,阻挡住刀锋必然的去路。血,笼罩了所有人的眼睛。车厢在阳光的万道金光下面变得暗淡无比。
人民乘警终于英勇地冲了过来,像所有电视剧表演的那样,歹徒被制服了,我们胜利了。张三艰难地爬了出来,躺在座椅上中年女人脸色不再暗淡。阳光透过车窗上她的鲜血照在脸上,润泽透明。乘警有一部分押走了歹徒,一部分去找医生,一部分和张三一起围在英雄的周围。张三和所有人惊奇地看到女人苍白的额头慢慢出现红晕,红晕越来越大,整个头部笼罩在一片晚霞般的瑰丽之中。女人被鲜血浸透的衣服神奇地变成了一件长裙,整个身体不断冒出各种颜色的雾气,开始是蓝色,绿色,粉色,红色,然后是让太阳光黯然失色的金色。各种颜色的气体围绕着女人渐渐凝成一朵七彩祥云,女人的身体缓缓升了起来,在众人的目光中飞出了车窗。与天空越近,女人的身体越大,终于融合在一片蔚蓝之中,分不清哪个是天那块是女人的身体。女人躺过的地方散发着一股奇异的香气,超过世间最高级的香水。那个地方空着,被救孩子的妈妈用纱巾做成一朵花放在那里,张三就坐在花的对面。张三想,我是谁这个问题已经无关紧要了。张三这么想的时候,刚刚一只在车窗外盘旋的白鸽展开了翅膀,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飞得没了踪影。
七,
老实讲,在这面墙上,我不是第一次看到死亡。每次看到它,都是不同的样子,但是我得承认,这是最美的一次。在这面墙上我已经目睹过很多次各种颜色的死亡,是的,在我看来,死亡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最可怕的是一种黑色的堕落。对此我不想发表任何看法,对死亡,任何人都无话可说,当然我也不可能例外。
张三可是第一次面对死亡,受了不小的惊吓。一般来讲,人有了压力总是急于找到出口和安慰。张三自觉自愿把姑娘当成了他的安慰。姑娘自从被张三一把拉到座位底下以后,对张三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姑娘已经不管张三叫大哥了,就喊张三。张三现在觉得最信任的人就是姑娘了,张三就说了。张三说,我得了失忆症,不敢睡觉,害怕一睁开眼睛连你也不认识了。姑娘听了,出乎张三的意料一点也没有惊讶,好像失忆症就和感冒一样平常,这个反应让张三比较忐忑。姑娘看了一眼张三,笑了说,你放心睡吧,我没得失忆症,你忘了,我还记得你。张三听了就咧着嘴睡觉了,姑娘这句话就等于说,张三你这辈子别想跑我嫁定你了。
张三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车厢里大部分的面孔都变得陌生,姑娘正跟他笑,问他中奖没有。张三揉了揉眼睛,说,没中上,但是以前的还是没想起来。姑娘就说,忘了就忘了,快哄哄你儿子。
张三这才注意到姑娘手里面抱个孩子,姑娘说,这孩子是张三的儿子。
现在,张三有了媳妇也有了儿子。火车还在咣当咣当不准备停下来的样子,好像在和黑夜赌气。后来终于累了,喘了一口粗气,停了下来。
这是一个灯火暗淡的小站,没有几个人下车,,站台上空只有寂寞的蚊虫在徒劳地撞着窗玻璃。这时姑娘怀里的孩子开始放声大哭,姑娘说,孩子饿了,张三你下车买袋奶粉。
张三慌慌张张就往站台跳,没有卖奶粉的,就喊,没有奶粉,咋办?姑娘打手势,上车呗,笨蛋。笨蛋张三上不去车了。张三看到了站台的站牌:终点站。张三想起来口袋里那张车票,他应该在这里下车。张三想,车票上说,我应该在这里下车,那么命里面我应该和这里有我忘记了的紧密联系,如果找到这种联系,我也许就找到我是谁了。张三转过身,招呼姑娘和孩子下车。可是,让我着急的是,姑娘和儿子被灯火通明的火车带走了。留给张三一个昏暗不清的火车尾巴。
火车开走了,站台一下子变得昏暗,车站工作人员也一同隐没在没有尽头的夜色里面。长长的铁轨泛着清冷的光,站台上除了张三再无他人。
张三站在站牌下面,再一次地张开了嘴巴,星光之下,白色的站牌三个黑色大字:起点站。
天色开始发暗,那面墙上的颜色在慢慢变淡,我知道在太阳落山之前,这场电影散场了。现在,正是下班时间,胡同里面塞满了自行车的铃声,忙碌的一天结束了。
院子的大门打开之后,早已等候的家长像一群失去了蜂王的工蜂,涌进院子飞进各个房间。一会儿,我知道,就会是满院子的欢声笑语,东墙这边就会起起落落很多双解放了的小脚丫子,试图飞到天上去。在落日温柔的俯照下,孩子们的笑声成了人们唯一的安慰。
我身后的门响了,妈妈用她一贯的语气喊:张三,腿又没毛病,就喜欢在轮椅上坐着,真是的。自己把眼睛放药水里去,别什么都等着我伺候。
我忘了说了,在窗户后面的这个桌子上,有一个茶缸,里面放着特制药水,每天天黑之后,我的两个假眼要放到那里面泡着。
于是,我慢慢摘下我的两个眼睛。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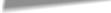 |
|
回帖 |
 |
|
| 回复人: |
意外的内伤 |
Re:深呼吸,向前看 |
回复时间: |
2003.09.12 20:21 |
|
看来又是一个精典大砖头。
我现在眼花。留着晚点再看哈
|
|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