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终对话(六)白夜 |
病房在三楼,15平米左右,一对沙发,两张床,有独立的卫生间。窗台上摆着一盆叫不上名字的紫叶花。由于花土干裂,叶子有些枯萎。窗子正对着铁路俱乐部的操场,每天清晨六点,天还没亮,那里就会传出悠扬的健身舞曲,三三两两的老人们鬼魅一样扭动着身子,停在空中的手臂像枯枝一般抖动不已。舞曲给人的感觉像屋子里的鲜花,呈现欢快又忧伤的意味,康乃馨、百合、满天星……这使我联想到梵高的画,松树、鸢尾或向日葵,就像释放明黄色激情的焚烧,又暗示着终成灰烬的蓝紫色的死亡!这老人舞蹈,这垂着头的鲜花,还有母亲安祥入睡的样子,浑然绽放着凄凉的美。
母亲是在早晨注射了杜冷丁后入睡的,时而神态安祥,时而长吁短叹,间或没了声音,还会突然睁开眼,四下里望,然后又沉沉睡去。她仿佛多少年没有这样放松过了,从上午一直睡到晚上。一直到妹妹也来了,才又一次醒来,起了身坚持下床小解,坐在便器上,慢慢又闭上了眼,没了一点声音,我们顿时又屏住了呼吸,姐姐急去扒她的眼皮。
“没死。”母亲用慢悠悠的声音宣告。大家笑,她也抿嘴无声地笑了。妹妹把头贴在母亲脸上,“脸真光溜。”母亲说。
“这是头发。”妹妹叫,大家又笑。
“起床吃点儿饭吧?”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也是母亲最不情愿做的事。为了给大家点安慰,她强打精神坐起来,倚在床上,姐姐用一只小勺喂她,她应付性地吃了几口。妹妹抢过来喂,母亲又吃了几口,就说不吃了。这时姐姐拿过一个纸杯对我俩说:
“最后一口总是吐出来。”
母亲听了,说:“那不一定。”咀嚼了一会儿,喝了口水,皱着眉头忍了一会儿,还是吐了,看来她真的无法下咽。
“今晚我在这儿,天黑了,你们走吧。”我对她俩说。
母亲也这样说,两人才嘱咐了半天,在清冷的夜幕中坐人力车回家了。
夜晚来临了,母亲又开始昏睡。到了晚上十点多,疼痛又发作了,我披了衣服叫护士来打针,母亲忍耐的呻吟才渐渐平息。我在黑暗中痴望了一会儿母亲,感到大脑有些灼痛,在万籁寂静的苍白里默默躺下,我的耳朵却竖着,捕捉母亲那边的细微声响。
我辗转反侧,又几次坐起来注视着黑暗中的母亲,那几乎只剩了一层皮的坚硬躯体,听着她鼻腔发出的微弱呼吸,一阵寒噤袭来,孤寂像铁钳紧紧扣住了我的心。
我披了衣服来到走廊,静静的白色气氛中,幽深与腐朽的气味在长长的廊道里弥漫,使我产生异样虚空的感觉,似乎走在通往冥府的路上……
困意海潮一样袭来时,我重新回到床边,轻轻躺下,这时我听到一阵响动,母亲已经坐了起来,我急忙爬过去,在她的腰部垫上枕头和被子,再把我的被子拖过来,罩在她的身子上。
母亲最怕的是坐着,因为她的尾椎骨把皮肤撑破了,很难坐得住。这时她努力要坐住,并用一种含蓄的眼神望着我,我知道她希望我陪她坐一会儿。我想起小时候钻进她温暖丰满的怀里的情景,于是向她慢慢靠拢。不过与其说是偎着她,不如说是她偎在我的怀里。就这样,在又青又白的病房里,在狭小又阔大的黑夜中,我们的心又紧紧跳在了一起。
黑夜漫长又凄清,泛着紫色的壁灯下,原本空荡雪白屋子充满了神秘的鬼气,一种细微的不间断的鸣声在空间里飘动,如夜晚高压线传来的电流声,仔细去听,又似有似无。这是大象无形,大音稀声的境界吗?我静静地注视她木塑一样的脸,她时而望望我,微笑一下,并发出轻微的叹息,又一阵阵的瞌睡,然后忽然下意识地睁开眼,再望望我,再瞌睡起来。
“能坐住吗?”我几次担心地问。
她总是点点头,希望就这样坐下去。
“这样会太累,我们躺下吧!”
她不回答,也不反对,依旧时而微笑,时而望我,时而瞌睡。
就这样,从凌晨一点坐到两点,她似乎还不愿躺下。
“你累了吧?”后来她竟然这样问我。
我点点头,我非常矛盾,但我不能允许她继续这种忍受肉体疼痛的心灵慰籍。
她果然同意躺下。
“我们明天再坐。”我安慰她。这同时,一个声音却说:还会有这样的时刻吗?
我于是可以安然入睡了,梦到了在一个向上的通道里,通道愈来愈窄,最后顶部的天空收缩成一个圆圆的小点。一个响动使我睁开眼,看看表,三点十分,母亲已经爬下床,在黑暗里定定看着我,我吓了一跳,我起身去扶住她,她幽幽地说:
“我想走一走。”然后居然爬下床。
我扶着她在黑暗里走了两圈,不住劝她可以了,十分钟后她才重新躺下。
确认她睡着后,我准备重新入眠,但大脑昏沉沉地,一阵阵灼热,一侧耳朵开始鸣叫,我的灵魂到哪里栖息呀,心有撕裂的感觉。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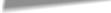 |
|
回帖 |
 |
|
| 回复人: |
安多雅·桑夏 |
Re:临终对话(六)白夜 |
回复时间: |
2006.06.21 18:02 |
|
没死!
她真的没有死!
还在心中!还在梦中!还在我们的身体的血液中!
|
|
|
| 回复人: |
美灵 |
Re:临终对话(六)白夜 |
回复时间: |
2006.06.21 21:51 |
|
灵魂游动 白夜长长
|
|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