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佳期 |
一直惦记着这寒假。回家。放烟花。
何况我学了一学期的吉他,已会弹几个简单和弦。就我而言,这已是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容我回家卖弄一番。
期末考了七门功课,挣扎之余只有闲暇发发牢骚。
说什么,高搂独倚兮,风卷云走。温书迎考兮,人不如狗。
回家赶上春运高峰,拖了行李在车站的人堆里翻滚,身后背着吉他。虽不甚重,感觉却很是累赘,像个落拓的流浪歌手不是,过时。这天气阴阴地冷,空气滞涩,微微带着潮气。
没人来接站,只得拖了行李打的回去。自车窗内看见街道上卖年货的摊子喜气洋洋地摆出来,春联,灯笼,中国结,都是大红。当然也有顶着禁令出售烟花爆竹的小摊,生意极好。
前一日妈告诉我雇的小阿姨回乡过年,家里无人打扫,让我回去自己收拾一下。等开门一看,呵,地板积了一层灰,桌上橘子剥开了皮放着,橘瓣干硬,容色寂寥地躺着。没人去吃,橘子也会自怜的。
开了音乐趴在地上抹灰的时候。阿倾的电话追过来,说死女子回来了也不打声招呼?我瞅一眼来电号码大奇,说你几时回的国?她说三天前。晚上我们去哪里混。我说酒池肉林。
一聊聊了四十多分钟。爸妈回来,对牢我左看右看,说又瘦了,然后欢欢喜喜地进厨房给我炖乌鸡汤吃。我对阿倾说好不好明天出去,我弹吉他给你听。她说她在加拿大的男友就成日价弹唱鲍伯迪伦,这年头是不是是个人就得弹吉他。
狠睡了一天。自己又大又软的床,入了眠就人事不知。与阿倾相约在一家麦当劳。去时她正坐在窗边吃冰淇淋,看了只觉得眼前一亮。这个小城市温情脉脉,这样锋芒毕露的漂亮姑娘和它错了调。
倾从包里掏出一管睫毛膏一盒胭脂,都是兰蔻。她说你眼睛大涂了睫毛膏更好看这款胭脂衬你肤色我就给你带回来了。顿了顿又说加拿大买的便宜许多,那儿一桶哈根达斯不过三十人民币。说完拽我到洗手间上妆。我看镜子里的脸居然好似亚洲版芭比。漂亮是漂亮的,扑朔迷离。
春节前有个初中同学聚会,在网上发了帖子。问她去不去。倾说都是不相干的人,去了作甚。
不相干的人。呵,相干的,又有什么人。
那晚吃饱了汉堡薯条,出来发现落了雨,街道干干净净。积水映出霓虹灯热热闹闹的暖。与阿倾转战酒吧,一人两瓶科罗娜。说的都是陈年旧事,把以前说得那么好,叹息着回不去了。阿倾抽了两支薄荷烟。她学会抽烟。王菲唱的花非花的情调雾非雾的线条。
都有点醺醺然。恍惚里看彼此都事表情怪异两眼迷朦。反正都只是二十出头的人,怎么醉也醉不出沧桑来,只像是某个新鲜的戏码,最后还要各回各家。
在床上辗转,窗檐滴下雨后的积水。滴答滴答。有如更漏。把我衬托成古时深闺里的不眠女子。时时准备感花溅泪对月伤心。
径曲梦回人杳,闺深佩冷魂消。
《牡丹亭》里的唱词,你是否余香满口。看到柳杜在梦里交欢。看看看,即使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也得在牡丹亭畔裸程相见。呵,遂成好事。
凌晨三点。
我遇上了陆恒。
周一晚上酒吧没有乐队演出,台上空落落。生意也冷清,只有几个人喝闷酒。店员大概也意冷心灰,音乐停了也不去续上。又是下雨天,听到雨声了。
阿倾正和旧欢一起,佳期如梦。我形单影只。
于是坐到演出台的高脚凳子上去,抱了一旁的吉他自弹自唱。唱王菲的怀念。音响设备未开启,唱给自己听。酒吧里的人看见这样一个自娱自乐的姑娘,分明精神一振,哗啦啦鼓起掌来,十分捧场。
有人喊我名字,阿错阿错。抬头看阁楼上某英俊男生朝我挥手,眯了眼看清他的脸,原来是陆恒。
陆恒是我初中时手都没牵过的小恋人。好些年,没见过了。
初恋呵,惆怅旧欢如梦。
我们像陌生人一样寒暄一阵,交换各自近况,手机号码,QQ。之后一直喝酒微笑。气氛僵冷,却心满意足。
我问他知道么阿倾回来了。他说知道,她在QQ上说起过。
原来倾和陆恒一直有联系,只有我这样的倒霉蛋,才要靠缘分这个东西来一线牵。
又说几时一起出来玩吧。他说好,为你们设宴接风。
你们?凭空多了一个人出来,难怪空气稀薄。
隔着一张桌子看陆恒的表情始终微笑,眼睛看住我却不敢和我对视。桌上照例有蜡烛摇摇,火光明灭地制造暧昧氛围,让许多人能得偿所愿。
陆恒抽三五烟,用银色ZIPPO打火机,起身到室外接听电话时发现他身高足有一米八二,手机是诺基亚7610。哈,这样的一个人,十足该写进言情小说。何况他头发长长,相貌俊好。
此后陆恒说夜深不好让我一人回家,便陪我往寄车场寄好自行车。他载着我,呼啸来去。
到家时针只在十一十二之间,一天尚未过去。迷糊里想起谁说的,酒会越喝越暖。
……越喝,越暖。
这个寒假叫我意外,阿倾回来了,陆恒出现了。于是自己时常飘飘飘,飘到初中三年那些旧时光里去。像场过家家,晚饭时间到了,家里人唤着吃饭了,于是一群小童便杯盘狼藉地散了。
阿倾问我是不是还喜欢陆恒。我摇头摇头,动情,怎么会。
经常窝在她或我的房间里说话。在她那儿喝的是百事,在我这儿偏喜泡上两大玻璃杯的蜜水。加片柠檬,滋味真好。
问这个寒假我们做什么呢。她问过后我问。一天一天,什么都没有做。
一起上街买过年的衣服,天气晴雨不定。偷偷买了一袋子烟花爆竹,回来路上两人傻笑不止。当然也去小摊上买炸萝卜糕吃,踩这自行车从中山路南端骑到北端。就像我们十四五岁做过的那样。腊月二十八,突然想到按规矩过了年就算二十三岁的人了。哗,物是人非。
陆恒说请客,我说不妨去街边吃大排档,入了夜人声喧杂,我等小市民淹没其中,其乐也融融。他又叫来了大路。大路亦是初中同学,在西安读书兼搞摇滚。吃吧喝吧,油烟一阵阵熏上来,一起灰头土脸。
之后唱K。陆恒要了大包厢,电话不断地约来一帮人。仿佛他必须与人堆混成一色方有安全感。阿倾心不在焉,头靠在沙发上和我絮絮地说她的君。
是啊是啊,她回一趟家,也不过是为了见她的君。君。怪名字。君主亦或君子?日日思君不见君?
那年他俩不过是在路上邂逅。第二日放学时,那个好看至极的君靠着教室外的走廊栏杆看着倾。倾出去,他把一条灰色围巾缠在她脖子上。由此一锤定音。
我只在一旁看着,不可否认地心生嫉妒。英俊的,清洁的,一笑就是满室阳光的脸。说话尤其好听,温暖厚实,一床晒好的棉被一样,叫人卸掉所有防备
阿倾不再和我一样简简单单地喜欢班上的某甲某乙,她和君恋爱,站在一起就是一出言情偶像剧。每天孩子气地分合吵闹。那时倾披着墨色长发,脸上有那样一点甜美的脆弱。那时倾很像个精致的瓷娃娃。
现在她像一颗钻了。骄傲的夺目的。光芒冷硬,划伤玻璃。
君比我们高一级,同校。阿倾的一场恋爱就反反复复谈到现在,与别人合了散了罢了,只有对他念念不忘,不肯忘。
也见过倾哭,山崩地裂要把自己折腾死的哭。君有别的漂亮女友。北京的上海的。呀,枝头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哭过了继续,我劝不了她,此人泥足深陷,劝她不过令这只扑火飞蛾自以为姿态更加决绝辉煌而已。
我从未像她那样伤过心。蜗牛一样碰了壁就安静倒回,不肯让人看头破血流的狼狈相。
倾又抽烟,直接抽陆恒的三五烟。陆恒看得有些呆掉,说我不劝她?
劝有什么用,一劝就能戒的东西早就绝迹了。你还不是,夜夜笙歌,你戒一个我看?
陆恒低下头暗笑。我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
阿倾接了个短信又急匆匆赶出去。她回头对我一笑,抽了一半的烟丢在烟灰缸里,走了。陆恒把烟头捻死,对我说抽烟的女人总让人感觉蕴着毒。
我笑,说是,粗蠢的女人抽烟是死猪肉地沟油的毒,漂亮聪明的女人抽烟就是罂粟花曼佗罗的毒了。
陆恒笑,他最常有的表情就时笑。他摇摇头喝掉杯中啤酒,这下才说,你说得对阿错,我们一起唱个歌吧。
过年。一直在帮家里张罗东西。大扫除。大年三十让我自己买年货去,从大卖场出来自行车丢了,剩的钱不够打的。手提着两大袋东西,一柄新扫帚横在腰间,真不知道是什么扮相。更绝的是手机欠费了,简直要哭。
走了一会儿后遇上大路,让他载我回去。路上他说,陆恒说他一直是喜欢我的。我只扯些不相干的话打岔。过去了,不要想,不要去想。
夜里吃火锅,看晚会。十二点过后和爸偷偷下楼放鞭炮,点了或撒丫子就跑。到处是违禁放鞭炮的人。听着噼里啪啦一通乱响,心里偷着乐。再然后电话短信QQ大拜年,忙得七荤八素。凌晨两点恹恹爬上床,和阿倾发段信。
小时候过的年总比现在醇厚的多,八九岁的小人,小红裙子小红鞋子小红蝴蝶结,还喜欢在眉间点一点胭脂,乡气的可爱不是么。大年初一出门去,说恭喜恭喜换取红包。想要的不过是一个气球一包糖果或一个布娃娃。
阿倾忽然打来电话,接听到的是鞭炮声。她在另一端喊着阿错阿错听到没有,我和君在郊外放鞭炮,还有很多很多烟花,冻死我了不过真够hight的。新年快乐啊薛阿错。
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她就挂了电话。
只是想她跑到空荡荡的市郊火树银花一阵后,会不会越发的冷清。
大年初一。睡。下午出门拜年。晚上在家不停给来客泡茶沏茶。、
大年初二。街上店铺大都还关着门。大超市买了两大袋零食。晚上和十岁的堂妹满街满巷窜着放烟花,裙子烧出一个洞。回家吃饭时客人看着我一脸错愕的僵笑,对我爹妈说你们家阿错还是很……天真的嘛。
大年初三。我帅气非凡的表弟载来他的小女朋友问我老姐不如一起去唱K。与此同时收到陆恒的短信说出来一聚?当然选择后者。
是陆恒几个无事忙的朋友要拍DV短片,找我给写剧本。我说你们找个什么人什么事跟着拍就是了何苦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剧情片。陆恒告诉我说是朋友中的某甲某乙在追一漂亮姑娘,借口找她当女一号来着。良苦用心。我说行,把阿倾叫上她鬼点子多。
有意思。
隔了一天见到那女一号。的确是精致漂亮的一张脸,说话细声细气,一副不胜娇怯的样子。坐下前先抽张纸巾细细擦椅子桌子,吃饭时从粉红包包里掏出一对天蓝色印有Hello Kitty的袖套。我和倾骇极而笑,这种泡在酒精里的花朵儿。
饭桌上分配了任务,与漂亮姑娘演对手戏的是她的追求者某甲,其余演员全凭客串。导演摄像是某乙,大路搞配乐,我和阿倾做编剧。因为在学校学过一点,所以我跟着做后期剪辑。叮一声干了杯算是开机仪式。女主角一直斯文有礼地吃着饭,只是看他那两只袖套,我老觉的她是一副随时准备洗盘子的架势。
对了,陆恒做什么。他说我只负责接送你们。
阿倾一向爱搞鬼,她让那漂亮姑娘挨球砸。篮球。咻地飞过来撞上女一号的脑袋。然后倒地或是晕眩。男一号于是飞奔过来说对不起。扶美人上医务室。这般这般,恋爱开始。
别人说她,阿倾一斜眼说这可是校园言情的经典桥段,不然改成被车撞?
结尾呢?哗这个简单,最后一场车祸随便他们谁死掉,剩下一个此恨绵绵无绝期。
大路在一旁叉着手,他说我最烦你们这些编剧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前后拍了一个多星期,期间去过一次海边。陆恒借了辆吉普拉这票人去。我挤在副驾的位置上,看着他有片刻的失神。天气晴朗暖和,男女主角在沙滩上两情脉脉。所有镜头都似曾相识。我看这言情片更倾向于搞笑。
腻腻歪歪后开始烧烤。
假期遇上陆恒到现在有半个多月,一起聊天说话不超过二十分钟。大部分都在相顾无言装高深。当我们会叙旧?都好像记不起过往,种种琐事。十五六岁呵,那时又比现在的孩子幼稚许多。他只爱打打闹闹,比如从楼上窗口甩下灌了水的气球,砸在我车篮里溅我一身湿。比如放了学在我车上多加一把锁。比如在身后拨散我的头发。似乎看我跳脚他就心满意足。
阿倾在中间帮着传情达意。当然她和谁闹别扭时我也曾凶神恶煞地跳出去骂人。倾是玫瑰花,我还要帮她多添一根小刺,真无谓。
好好的阿倾接了个电话又要走。死女子。我恨恨地骂。每次都义无返顾地要去扑火,不如此就会堕入黑暗万劫不复,连矜持都扔得干净彻底。她说阿错同志,我这假期不长,我不要矜持,只要欢喜。你也是,不要总是脉脉不得语的样子,何必自苦。
她又看出来了。不好辩驳。她郑重拍拍我肩膀说行乐须及春啊,宝贝儿。
走了,这人真是戏剧化。
又回来,说打不到的回城。我噎住,打的回去怕要两百块,阿倾还真是一刻值千金。
于是陆恒让我们先玩,他驾车送倾回去。
……怅然若失。大路来帮我往玉米上抹黄油包锡纸。海风吹得我鼻涕长流,大路问要不要加件外套。我们漂亮的女主角也凑过来坐着,问大路西安怎么样做的摇滚何种流派这次配乐如何准备鸡腿是否烤熟等等。我头痛不已,又是一个烂摊子。
阿倾又消失了一星期,不知如何抵死缠绵来着。我在别人家里剪片子,成日坐在对编机前安排男女主角背欢离合,一遍一遍。晕死。毫无意义。最后配好音乐,大路做得挺地道。男主角面如死灰,因为那漂亮姑娘分明看上了大路。为人作嫁。看这DV片多讽刺,戏而已,如露如电,事不关己。
寒假也快结束了。
晚上陆恒或大路会送我回家,路上一起吃消夜。几次被来家里玩的姐姐窥到,总要扯着我胳膊大叫好帅啊好高啊等等蠢话,引得我虚荣心发作,沾沾自喜。到家后照例吃鸭汤鸡汤王八汤,直怀疑自己已脑满肠肥,照镜子看却是比来时瘦了许多。
夜里睡不着,辗转着胡思乱想。阿倾手机干脆关掉。她不知天上人间,我却找不到人说话好生难耐。
悄悄到厅里看刚刻好的光盘,看我们一帮人炮制出来的爱情故事。爸妈听到动静出来观望,一看又来了精神,站在一边评头论足。
说,那个女孩子也算不得十分好看,哪里比得上咱们阿错。
说,是是是,阿错演肯定比她好。
我骇笑,是,你们女儿最了不起。把自己当宝,不害臊的。
两人理直气壮,说我女儿当然了不起。如此总结陈词后才回屋去睡。
我兀自对屏幕傻笑不已。
约了陆恒到市郊小山上放烟花。你看,过两天便是元宵,新年过完了。颜色旧了。烟花还剩一大把。
这次他终于没有再叫一大帮子人作他的保护色,只是对牢了我,举止尴尬。
我自顾自拿了他的打火机去点引线,对一束束红光蓝光大呼小叫。小时候从不敢去点一个炮仗的,大了开始找补偿。陆恒在一边看着提醒我小心,亮光映着他的脸。嘴角向上的弧度,笑成没理由的纵容。我也笑。出门前用了阿倾送的睫毛膏和胭脂,不知道是怎样的一张脸。
去吃东西。小山上并不冷僻,望下去是热闹的城,上边牵了一溜灯泡搞排挡。夏夜市民驱车上来纳凉消夜,冬夜一个个躲到帐篷里吃火锅。风刀霜剑,都不相干。
我往锅里捞肉片吃。陆恒拿起手机问我要不要叫大路他们过来。我说好啊我去多叫点火锅料来。
等人来时聊起阿倾,说她这样任性。陆恒笑,她初中时就是那样子。
鬼使神差地我问起,那时,你,有没有,喜欢过她。
他顿了顿,笑说喜欢她不是太累了。
答非所问。
呵我知道。是不敢。
他说下去,一开始有点,后来就是你了。
更糟糕,退而求其次。他和我一样怕自己头破血流,喜欢安静无虞的状态,真是同道中人。我没敢问他现在呢,倾总是高我一丈光芒,我是帮忙帮闲的小角色。
正暗自感叹呢陆恒手机响,他们说下雨了不来了。
居然下雨了,心灰灰的时候连天气都来帮衬。
一直喝水,一杯一杯一杯。没来由的渴。也许因为天气干燥?食物太咸?
正月十五了,阿倾回来。和我上街买花灯。扁扁叠成的纸片儿,拉开就是小小的圆柱体纸灯,那样缤纷的,叫人欢喜。
阿倾只随意穿了长毛衣牛仔裤,头发打理成咖啡色波浪,银制大耳环。浓密睫毛,玫瑰色嘴唇。经过的男生都要回头看一眼,再看一眼。这样简单地也透出一股波西米亚风情来。
热闹的街,来往的人都提着小小纸灯,亮了一条街,真是温暖。广场上烟花在空中轰然盛开。最后的盛大狂欢。农历年过完了,不知有谁热衷于过年鸡零狗碎的欢愉。我和阿倾犹自恋恋。
在路边碳上吃汤圆。
阿倾说在加拿大中餐馆打工,一月三百加币。学会做春卷豹子馄沌,老了老了倒可以回来开个小馆子。我说到是帮你和面端盘子如何。她说当然好。只是俩老太太开店太没吸引力,生意清淡怕只能自做自吃。哎你说我们老了会是什么样子。
我笑她,说你是修炼得道的妖精,怎么会老。
不自觉地都笑得有点凄怆。
该准备回校了。行李打点好。车票。对吉他失去兴趣,转送他人。最后出门逛了一趟街,下决心在街边小店打了耳洞。银耳钉。亮晶晶。
阿倾也要飞去加国,我找不到什么东西送她。
去香火最盛的寺庙里为她求了张平安符。廉价的,只得十块八块的小木片,上有菩萨宝相庄严。
阿倾接过时笑我,说即使佛法广大菩萨怜我,护法金刚也得将我这样的人一掌击毙。
我瞪她,胡扯,你又不曾杀人放火。
她又摇头,说你简直不知道我生活多混乱。呵,何况到了那边是圣母基督的地盘,菩萨也鞭长莫及。
只好转移话题,晚上吃饭唱K。陆恒请客,算是饯行。
我费了半天工夫用吹风机弄出一头玻浪来。我对着镜子打理自己的脸。我连指甲都修剪得圆润光滑。我套上短短的牛仔裙,裙沿展开像一把含蓄的伞。也许室外气温颇低,但没有关系。
看看看,假期的最后一天。不舍得不挥霍。
饭桌上已喝了酒,唱K时继续。
李老先生说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我看正相反。
只要微醺,边有了借口恣意而为。
歌唱得荒腔走板。几支烟便满室雾腾腾,叫人看不清眉眼。陆恒与人拼酒却毫无醉意。他是喝惯了的人。
他们让阿倾把君也叫来,看他笑容温煦打扮得体,疯起来却和倾挪开了桌子跳劲舞,端的是个中高手。其他人酒也不喝了歌也不吼了,挤上去一起癫狂。不知道的人会以为是嗑了药。
我陷在沙发里看陆恒在另一端朝我举杯示意。干杯,干杯。将进酒,杯莫停。
轻飘飘到洗手间吐了终于。
用水泼泼脸出来,陆恒在门外等着。他说你喝太多了,我送你回去。
不清楚醉了没有,脑子里荒芜得像洪水过后。似乎是末世了,倾城了。陆恒脱了风衣披在我身上,扣好扣子。坐上他摩托后座。我抓着他的衣服,还是清醒地不去搂他的腰,却把脸埋在他后背上。
陆恒把车骑得前所未有的慢,他怕我这只醉猫掉下去。时间并不晚。街上许多人。
一直闭着眼,无端地觉得他呼吸深重。
快到家时我认为我应当不失时机地借酒装疯。我叫他在小区的小公园停下,我下来笑眯眯地让他先回去吧,我要在这呆一会儿。
这个老实人,手足无措,只能停好车跟住我。
吹了风,又吐。我小心地不溅到他的风衣上。胃一阵翻腾,见鬼。
他拍着我的背,从我包里找出纸巾。偶尔远处穿着睡衣下楼丢垃圾的主妇看我们一眼,陆恒表情又无辜又惶然。
我知道自己仍是笑得恍恍惚惚。我说我走了,我明天就走了。你还不回去吗,对了风衣还给你。
冬夜真是静,只有风声。
他站在我面前沉默了一会儿,轻轻轻轻地,抱了我。
呵,天。
我的心不肯跳了。他依旧轻抚我的背,像安抚一个哭闹的顽童。
三秒钟之后不着痕迹地分开。
他送我到家门口,两个人都若无其事。相信我在酒精的掩护下颇为自然天真。
我到阳台上看他离开。看他迟疑地回头看一眼两人站过的地方。
过去了。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阴雨天气。像来时一样,自己拖着行李去车站。
一晚失了眠。在车上昏睡。
都是喜欢把心思深藏不露的人,谁爱谁猜。网上遇见了,还是言语淡淡。说早。早上好。午安。晚上好。晚安。时间过了一月,无迹可寻。
只是,不自觉的,经过店铺里的三五烟,手机店里的诺基亚7610,专柜里的银色ZIPPO,都要多看一眼。我无法可想。
阿倾说那晚和君分了手。冷暖自知。她说最近吃肉都没胃口,我说无肉令人瘦,宝贝儿。
夜里上网看片子,陆恒上线。例行的晚上好之后陆恒忽然说阿错你丢了条银手链在我这儿。
我问几时?他说你回校前夜,链子落在我风衣口袋里。回来记得找我拿,晚安。
忘记了。大概那时也真的有些迷糊。
陆恒见了也会想起,他也曾轻轻轻轻地,抱过我吧。总是要有遗失的物件做凭证,灰姑娘一消失,王子就拿水晶鞋做一场凭吊。呵我又想多了。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吧。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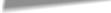 |
|
回帖 |
 |
|
| 回复人: |
夜半桃花 |
Re:佳期 |
回复时间: |
2006.06.11 23:06 |
|
事隔一年多突然想回坛子看看
许久前写的一篇小说
且在此落脚吧
|
|
|
| 回复人: |
漫步长天 |
Re:佳期 |
回复时间: |
2006.06.12 09:22 |
|
辛苦了,请喝水!
有时间请你来一杯,不知酒量如何?
鼓励,并欢迎常有佳作共大家欣赏!
|
|
|
| 回复人: |
减字白水 |
Re:佳期 |
回复时间: |
2006.06.21 01:41 |
|
东邪西毒里说的,酒会越喝越浓,水会越喝越凉。这是二者的区别。
|
|
|
回复 |
 |
|
|
|

